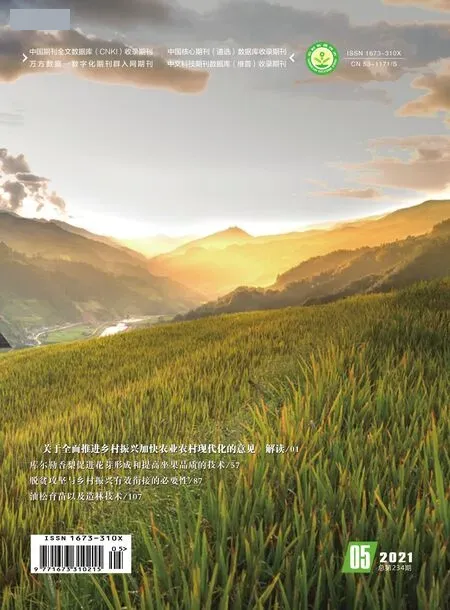農業推廣服務模式新的發展趨勢
劉淑麗 孟志梨 王金鑫 張瑞波
(1.扎賚特旗音德爾鎮綜合保障和技術推廣中心,內蒙古 興安盟 137600;2.達拉特旗種子與經濟作物工作站,內蒙古 鄂爾多斯 014300;3.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農牧業產業化發展中心,內蒙古 呼倫貝爾 162850;4.翁牛特旗紫城街道黨群服務中心,內蒙古 赤峰 024000)
基于此,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如何更好的適應時代發展需求,順應農業現代化的大趨勢就成了不得不討論的一個話題。在此大背景下,本文選取了農業推廣服務模式新的發展趨勢作為研究主題,首先對相關概念進行簡述,接著分析了目前比較普遍存在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最后論述了農業推廣服務模式的幾種新的發展趨勢。希望以此,有助于農業推廣服務新模式的發展和推廣,為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獻上綿薄之力。
1 相關概念簡述
主要是對農業推廣和農業推廣服務模式的相關概念進行簡單的論述,為后續論文的鋪開奠定基礎。
1.1 農業推廣
發展至今農業推廣已經由俠義的學術領域定義拓寬了很多,廣義上的農業推廣指的是以農村社會為服務范圍,將農民們作為服務的對象、以農場或者農戶為中心開展的推廣服務,常常以農民的實際需求為推廣內容,以提升農民生活水平為最終的推廣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所開展的社會教育。其特點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開展,是一種社會性活動,并且更多的強調活動過程。
1.2 農業推廣服務的主要模式
農業推廣服務的主要模式是指在某些特定條件下農業推廣的主體、客體、機制等要素存在的方式以及運轉的過程,整體要素所表現出來的具體內容被稱為農業推廣服務的主要模式。包括政府主導型、高校和科研機構主導型、農業合作經濟組織主導型等類型都是比較常見的一些農業推廣服務模式。
2 對農業推廣服務模式新的發展趨勢進行探究之意義
2.1 是實現統籌城鄉發展的時代需求
對農業推廣服務模式新的發展趨勢進行探究,可以推動農業推廣信息服務模式的發展,從而提升農村地區的信息化服務水平,縮小農村地區與城市地區之間的信息化差距,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2.2 是促進農民增收的實際需求
加強農業推廣服務模式新發展趨勢的探究能夠有效解決三農工作中的一些突出問題,使更多的現代化技術、信息化技術與傳統農業相互融合,對農業生產組織的集約化都十分有幫助,尤其是在提升農業資源利用效率、提高農業經營管理效益、提升農業服務生產活動效益等方面更是成效顯著,而這些都將極大促進農民增收。
2.3 是構建服務型政府的執政需求
對農業推廣服務模式的新發展趨勢展開探討,一方面也是政府對農業實施行政化管理、創新管理的有效體現,另一方面在農業推廣服務工作的開展和創新過程中各級政府部門還能更好的完成職能轉換工作,提升農業經營生產活動的管理效能,積極推動政府主導性服務模式的壯大,進而構建服務型社會。
3 目前存在比較普遍的幾種農業推廣服務模式
對當前我國存在比較普遍的幾種農業推廣服務模式進行論述,有助于更好的了解線性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并為下文探討農業推廣服務的新發展模式奠定理論基礎。
現在存在比較普遍的幾種農業推廣服務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導型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高校和科研機構合作主導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企業主導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主導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
3.1 政府主導型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
這種農業推廣服務模式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環境之下,農業推廣服務模式的主體為政府農業部門,比如涉農單位等,使用制定政策等一些宏觀的方式,將農業推廣服務與政策相結合,再通過開展實際工作帶來農業技術教育、農業示范推廣等內容,并且再開展實際工作的過程中將農業科技的研究成果推廣應用到農業生產活動當中去,促進農業活動的發展。可以分為中央、省級、市州、縣級、鎮級等級次,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推廣模式。
3.2 高校與科研機構合作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
這也是當前存在比較多的一種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它也是以政府指導推動為背景,充分的將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科研資源優勢利用起來,開展農業推廣等服務,向農民示范并推廣農業技術,將科研技術成果直接利用于實踐。
3.3 企業主導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
這一種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側重點在于企業,企業通過自身的農業技術研發力量,對農業推廣服務業務網絡進行搭建,從而將自己或者外來的技術成果、農業產生生產技術等進行推廣,達到生產農產品、收獲農產品、加工農產品等一系列的目標。在講農業科技成果轉變為農業生產實踐的過程中,提升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
4 農業推廣服務模式新的發展趨勢
4.1 政府公益性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將會逐步完善
當前,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已經建立起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農業推廣服務體系,這其中政府公益性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占據了主導地位。在將來新的發展趨勢中,政府公益性農業推廣服務模式也不會退出歷史舞臺,而是會逐步完善。上文有簡要論述過當前政府公益性農業推廣服務模式的基本定義和特征,這種農業推廣服務模式主要依托以各級相對應的政府職能部門,并且負責日常公共管理和服務工作。包括植物檢驗檢疫、品種審定、農業產品的質量監督等,還有一些在生產前為農民直接提供的公益性質服務,比如新種子、果苗的引入,或者是農用技術的引入及推廣等。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公益性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將會對進行了這么多年暴露出來的問題有所改善,并且拓展更多的推廣服務方式。比如說,通過播放科教興農的電視片或者是小視頻,讓農戶簡單易懂的明白農業技術;開展現場咨詢和實地指導活動, 并且開展一系列的高產量競爭等活動,通過更為完善的激勵措施,來達到吸引新農戶、宣傳新技術的目的。
4.2 高校與科研機構合作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覆蓋范圍將會更廣
傳統農業的發展和改進關鍵還是在于技術的進步,只有技術真正進步了傳統農業才有進步和發展的可能,但是進步的技術也需要實踐,只有將新技術充分運用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才能達到農業進步的效果。而高校與科研機構相互合作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就能夠很好的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在將來這種服務模式的覆蓋范圍將會更加廣闊。這主要是因為,高校和科研機構在農業推廣服務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擁有更多的專業型人才、科研及農業技術信息等方面的優勢,能夠為農業科技轉化和農業推廣服務帶來極為重要的支撐,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這種服務推廣模式主要可以問分服務推廣、技術推廣,未來的發展能否順暢重點在于政府的扶持力度以及資金的投入。
4.3 農村社區互助組織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將會增多
農村社區互助組織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主要是在當前農村農業經濟迅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公益性的政府傳統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已經不夠完全滿足生產者、購買者的需求,在這種大背景下之下,農村社區互助組織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將會增多。這種組織有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村專業輔助協會等,這種模式在將來也會成為一種重要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它通過農村之間的社區互助組織為服務平臺,主要是解決農業生產中遇到的實際技術問題并且開展技術推廣和引進工作,讓農戶們直接便利的獲取新的技術、實現信息傳遞和共享。它和政府公益性推廣模式相比較,優勢在于農村社區互助組織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將會效率更高。因為它一般是由農戶們自發組織形成的,即使不是自發形成的往常工作范圍也是在農村當地,會更多的與農戶產生直接聯系,并且更容易取得農戶們的信任。
4.4 農業推廣服務模式信息化程度將會顯著增強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不斷推進,農業信息化進程的迅速邁進,傳統媒體的渠道功能也已經發揮到了頂端,農業推廣服務模式信息化的程度會在將來不斷提升。一方面,農戶們對信息化的呼聲越來越高,有這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農業信息門戶網站也在迅速發展。因此,在將來的發展趨勢中,農業推廣服務模式將會越來越信息化,包括宣傳傳播途徑信息化、方式信息化等
5 結語
總而言之,無論是對于農業推廣服務從業者還是對于農業從業者來說新的發展趨勢都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尤其是對于農業從業者來說更是如此。在新的農業推廣服務模式下,農業從業者獲取信息的途徑增多、獲取信息的時效性增強、信息可靠性也得到了提升,并且獲取信息之后掌握技能的可能性也大大提升。基于此,我們更應當重視新環境下農業推廣服務的新模式和發展趨勢,爭取為更多的農業從業提供更有價值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