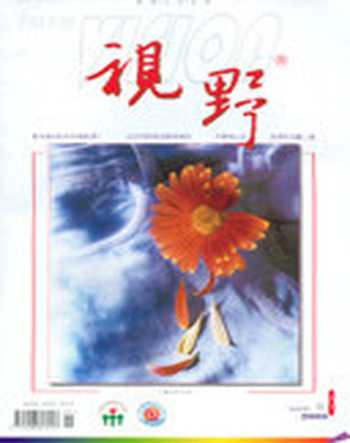以公民的姿態挺身而出
閔家橋
編者按:
孫志剛的悲慘遭遇引發了人們的強烈憤慨和極大關注。真相總會大白于天下,這是我們對社會進步的堅定信念。但是,在真相呈現的過程中,我們總該做些什么。因為,我們是公民,每一個人都是;因為,每個人也都有成為孫志剛的可能。
本期視點《以公民的姿態挺身而出》,讓我們看到了對公民權利的珍視,看到了對推動憲法政治的努力;我們會逐步領悟到這種努力的珍貴和意義。
要抓緊研究和健全憲法監督機制,進一步明確憲法監督程序,使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能及時得到糾正。
——胡錦濤同志在紀念現行憲法實施2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背景鏈接:
27歲的孫志剛2001年在武漢科技學院藝術設計專業結業,今年2月24日受聘于廣州達奇服裝有限公司。3月17日晚10時許,孫志剛因未攜帶任何證件上街,被執行清查任務的天河區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帶回詢問,隨后被作為“三無”人員送至天河區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后轉送至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3月18日晚,孫志剛稱有病被送往收容人員救治站診治。20日凌晨1時13分至30分期間,孫志剛遭人毆打,于當日上午因“腦血管意外猝死”(救治站稱)。
在民眾為被收容者孫志剛的默哀和憤怒即將淡去的時候,有三人以獨特的、公民的姿態挺身而出。 2003年5月14日,他們依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建議書,建議對收容遣送制度進行審查。
他們是三位法學博士,但他們更樂意以“公民”自稱。
他們都選擇了教書:許志永,北京郵電大學;滕彪,中國政法大學;俞江,華中科技大學。
他們是同窗好友:北京大學2002屆博士畢業生。
“我更關注農民和城市邊緣群體”
許志永是發起人,也是建議書的起草者。在整個事件里,他還負責外聯工作。滕彪和俞江更多退居幕后。這是他們商量好的分工,也是性情使然。但顯然,在孫志剛悲劇引發的“建議行動”中,他倆都沒有忍住。
許志永的研究偏向法社會學,社會調查是他生活的常態。他的“農民朋友們”甚至知道他的手機號。
“我更關注農民和城市邊緣群體。”在北京,許志永有一些談不上“高雅”的朋友:那些進京務工的農民。在和這些農民工的調查交往中,他知道了他們中間的很多人都有過被收容的經歷。“他們和我講在里面的遭遇。”許志永眼神痛苦,顯然不愿說得太細。
在接觸了太多收容遣送的事情后,許志永曾經想過行政訴訟。但沒有一個被收容過的人愿意站出來起訴和作證。那些人說:“我們不想這樣,我們還要在這個城市里干活。”
“我們無法忽略這個問題”
那些進過收容站的人,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被侮辱一番后走了出來。城市依然在運轉它的每一天,看不出異樣。
孫志剛沒那么幸運,他死在收容站。這一個案對許志永觸動很大,即便他知道太多類似這樣的故事。這一次,令他意外的是,社會輿論竟然有這么大的空間對此事作出反應。他覺得“這是個特別好的事情”。
許志永有點理想主義。他說,對于每一個案,他都不敢有過多的樂觀,但對于整體中國這個時代的進步,他非常樂觀。他認為,現實的很多制度都是靠個案去推動的。這是他以孫案為由頭做這件事的原因。
對于現實,滕彪和俞江便表現出了一種極為復雜的心情:想要疏離卻又難以疏離。騰彪說:“我更看重個案背后的制度建設。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孫志剛,我們無法忽略這個問題。”
4月份的最后幾天,沒有任何異議,許志永提出寫個東西的建議后,三人就心照不宣地開始了。如何找到突破口,這是個難題。一天,遠在武漢的俞江發來郵件,說《立法法》中規定公民認為行政法規同憲法或法律相抵觸的,有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的建議權。俞江說,我們能不能從這條路上試一試?
這是個重大發現。許志永和滕彪很興奮,許說此前他還總是寄希望于行政訴訟。許志永坦言:“連我們學法律的人都不清楚公民有這樣一個權利,還怎么希望更多的人去用它呢?”三人一致的態度是,要用這樣的方式,“試圖啟動中國違憲審查機制”。
5月14日,1000多字的“關于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書”終于完成了。
“這不是一份普通的公民來信,它的格式具有意義。它更像是一份起訴書,闡述了需要審查的事實和理由。”
他們的落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并寫下了三人各自的身份證號。“在《立法法》上并沒有規定我們應該具體向哪個機構提出建議,他們有沒有義務必須回答我們,以怎樣的程序回答我們,在什么時間以內回答我們,這些都沒有規定。我們通過這樣一種類似起訴書的格式,有它的涵義在里面。”“我們的目的在于從法律技術的角度關注收容遣送制度,我們不希望把它泛政治化。”
5月14日,他們經過詢問后將建議書傳真給相關部門,然后又跑到郵局寄了一份。至此,醞釀了半個多月的建議行動完成。
“即使杳無音信也無所謂傷害”
滕彪說,這件事,他們追求兩個目的。一個是實體上的,最樂觀的估計是,經過審查之后認為這個《收容遣送辦法》違憲,然后廢除。“但這也是最不可能的一種結局。”
程序上的意義是他們更現實的、可以期望的目的。“收容遣送制度可能依然生效,但在程序上我們希望能推動違憲審查機制。如果有一個反饋,甚至因此建立了一個正常的渠道來對公民提出的建議有一個回復,那么在程序上我們就算達到了目的”,即便得到一個簡單的答復——“收容遣送沒有違背憲法和法律”,俞江說,“這也沒有關系,至少大家知道了有這樣一種程序,大家可以反復地用這個程序,總有一天,這個程序的意義會顯示出來。”
許志永說,這件事本身如果能夠引發全社會的討論,就已經很有意義。這一次沒有成功,還會有下一次,一次一次社會的不斷嘗試,形成合力相信會帶來改變。
滕彪說,用知識本身推進社會改良,這是知識分子的本分。即使這事不了了之,對他個人也沒任何影響,他還是會關注中國的現實問題,還會關注收容遣送制度。
俞江說,如果被駁回或無回應,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又會陷入一種僵局。即使我們想再做,在法律上我們已經找不到辦法了。這樣的結局,會很遺憾,但當想到有些遺憾是必然的,他釋然了。
所謂“憲政”其精神核心即在于:限制公共權力于合法范圍之內,保護公民權利。所謂“違憲審查制度”,重點解決的是政府的違憲行為,包括政府的法規規章、抽象的行政行為和具體的行政行為。在上述意義上,三位公民提出建議書的行為,被媒體稱為“中國違憲審查第一懸案”。而這份建議書,也值得再三細讀。——編者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