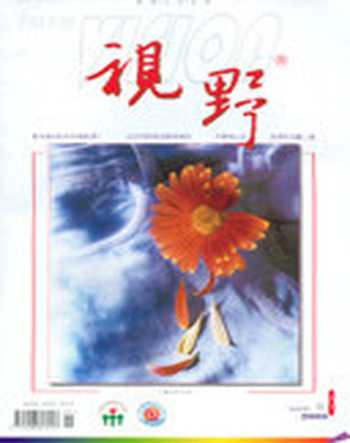后饑鋨年代
秋 高
每每憶起當年那段高中生活就忍不住鼻子一陣陣發酸。
我是1993年上的高中。那所中學雖然在一個小縣城,卻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被列為了省級重點。
學生都是下面各個鄉鎮考上來的尖子生,大多住校。
食堂離宿舍和教室都很遠,得斜穿整個校園,出校門,過一條馬路,沿著居民區里的一條巷子往里走六七分鐘才能到。食堂大廳里有兩排大圓桌,也沒椅凳,吃飯時都得站著。有一個打掃衛生的老大爺會在每次開飯前掃地時順便用那把大掃帚掃一下桌子,就算做了清潔,所以桌子臟得很難辨出原來是什么顏色。
飯菜比桌子要干凈,只是里面經常能吃出一些有機或無機的雜物,蟲子蒼蠅還好,權當補充蛋白質了,有時遇上鐵絲玻璃片就不免會有些后怕。校體訓隊的受不了,經常跟窗口里的人打架,還領導過幾次“罷飯”,但都因為沒有太多人響應,也就不了了之了。
食堂不賣早點,多數人的早點就是前一天打的一個冷饅頭加一杯白開水。我也一樣。雖然如此,宿舍里的幾個弟兄都是第三節課開始才勒緊腰帶,我卻第二節課還沒下課就餓得兩眼冒花了(我始終都懷疑他們有小動作,雖然他們一直不承認)。第四節課上到一半時大家的手就都放到了桌洞里的飯盒上,鈴聲響起時的場景有點像中長跑比賽的發令槍響起,幾乎是一路跑著穿過校園、馬路,穿過那條小巷,然后在食堂大廳那兩扇掉光了漆的木門前擠作一團。隔著玻璃看老大爺打掃衛生收拾桌子,一邊不耐煩地敲著飯盒,一邊把門上那把大鏈鎖搖得嘩嘩作響。門終于開了,便又在打菜窗口前擠作一團。雖然窗口里擺著的只是幾盆白菜、土豆、茄子,可每次如果動作慢點兒是會打不著的,所以只能這么擠。很多人用的都是我用的那種長方形鋁飯盒,很薄,有時從人堆里鉆出來時飯盒已經變了形,像一只破皮鞋。在電視里看到的非洲難民領救濟糧的情景,比我們當初,他們要顯得從容得多。
女生是不敢參與這些“暴力”活動的,一般都從家里帶些咸菜,開飯半小時后才到主食窗口打幾個饅頭,帶回宿舍姐妹們一人一個就解決問題了。饅頭總是充足供應的。
走入社會之后大小餐館進過無數,南北菜肴也嘗過不少,但至今都認為最香的食品還是那時食堂賣的機制饅頭。
為了省錢,那時很多同學都是兩人合打一份菜,填飽肚子全靠饅頭。和我合伙的兄弟很仗義,我們從來都是讓著吃菜,他一頓兩個饅頭,我一頓最少三個。那種饅頭好像太不瓷實,虛得跟面包似的,所以有時候吃四五個也不覺得撐肚子。
每年的運動會是班主任們最頭疼的一件事,上體育課跑幾圈都會暈倒,誰還有力氣為爭個暖瓶鋼筆之類的獎品拼命。最后只好趕鴨子上架,拽幾個眼皮耷拉得不太厲害的上去撐撐場面。為了制造氣氛,看臺上也不準空著,班長每天都要點名。
記得高二那年的運動會我在看臺上讀的是路遙的中短篇小說集,讀完了《人生》還只是心里有點難受,當讀到《在困難的日子里》主人公偷偷跑到學校附近收過的田里撿土豆躲到破窯里燒著吃,為了減少能量消耗趴在課堂上一動不敢動這些情節時,我都忍不住偷偷抹眼淚,我傷心,為那小主人公,也為我和我周圍的兄弟姐妹們。
我吃飯一直慢不下來,同時吃一碗拉面,別人加了醋,放點辣油,攪和一下,挑起來吹吹,剛嚼兩口說出一聲“不錯”,我已經在喝湯了。回家吃飯為這經常挨老母親罵,就是慢不下來。和朋友出去吃飯,誰愛點什么點什么,沒有我不吃的,只要沒有什么重要人物,從始至終我都筷不離手,最后還不忘打掃戰場。這些全都是站著吃那三年落下的后遺癥。
父母親從小就給我們講他們在60年代那三年吃什么,感嘆我們生在了面缸里,可他們不知道我那面缸里的生活也有三年是勒著腰帶過來的。那些我從來沒跟他們說過,當然,也永遠不會跟他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