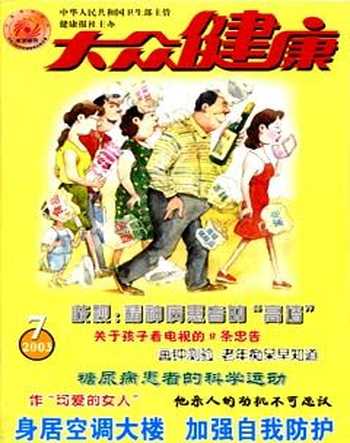英雄有淚
袁 源
他們只是抗擊非典戰場上一支普通的隊伍——北京大學第一醫院(以下簡稱北大醫院)。但是,當我和他們一些人交談之后,真的震動了。遠離生死現物的人,是想象不到真正直面病魔,以身相拼的人的情感。對于一般人難以承受的疲憊、感染、倒下以及遠離親人、推遲婚期等等,在他們的臉上不過是一抹淡淡的微笑。我真的沒想到,這些連生命都豁出去的人,卻有著那么多的放不下。
世界,是因為他們而美麗;生命,是因為他們而珍貴。
難得的防范意識
在他們用生命拉起的安全屏障之下,春光依舊撫摸著北京的每一個角落。
2003年4月3日,北大醫院發現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當時北京的醫生對于這種肆虐廣東并初露猙獰
其實,還在羊年鬧花燈的時候,這所學風樸實的醫院,已經開始抗擊非典的戰前總動員。有關培訓斗天4撥。300人的課堂,撥撥座無虛席。包括醫院的行政、后勤、保安、護工,無一例外都在培訓之內。
于是,便有了后來的保衛處處長王斌,沖上馬路守護電話亭的事。當時他看到一位確診的非典病人,竟然在醫院大門外的電話亭,抱著公用電話不撒手。這意味著小小空間,已經沒有了安全,而且很可能成為傳播病毒的禍源。真的,王斌當時像發現已經點燃的炸藥包,在一時無法消毒的情況下,他只有用死守的辦法,冒著個人被感染的可能,阻止后面無辜的人誤入危險。
在我國,傳染病的防治,不要說老百姓,就是某些專業人員也有些淡漠。那些塵封了幾十年的疾病在人們的意識里,幾乎蕩然無存。自從中國宣布基本消滅麻疹、傷寒、脊髓灰質炎等傳染性疾病之后,北京市綜合醫院幾乎關閉了傳染病科。全市僅有的兩所傳染病專科醫院,也在某種程度上缺乏防治呼吸道傳染病的必備條件和設施。
這是非典最可恨的一點——它抓住了我們最薄弱的環節。
于是,當病魔向我們突然襲來的時候,我們窘迫,慌亂,措手不及。但是,從良心上講,它給了北京人相應的準備期。
事后很多專家都看到這一點——對于突發疫情的暴發流行,我們缺乏快速反應的機制和條件。而北大醫院是北京惟一保留了傳染科的綜合醫院。特別是在會戰疫情的非常時期,他們“嘩”地甩出“三駕馬車”。除了前面說到的“傳染科”,醫院另外的兩支隊伍是“感染管理科”和“呼吸科”。這“三駕馬車”,從“防”到“治”,即從切斷傳染源——降低感染率,到治療效果——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應該說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用知識筑起防護的長城(醫護人員感染率2.2%)
感染管理科是北大醫院的強項。在和平時期,在以搶占尖端的科技為榮的競爭時代,這所醫院始終沒有對基礎管理稍稍放松。“感染”是自打有醫院以來最古老的話題,但是感染管理又是醫院永恒的主題。它是體現一個醫院實施醫療服務的內在真功。
醫院感染科主任李六億,1995年引進的人才。這是一位非常可愛且年輕的女學者。從4月10日醫院搶建臨時非典病房開始,她再沒有回過家。有時愛人抓著電話筒不放,“不能見面,還不能讓我多聽聽你的聲音么?”沒有辦法,現在她的每一分鐘不屬于自己。她的吐字,從嗓子里出來,帶著勞損而撕裂的血絲,可以讓每一個聽到的人心里顫栗。你能看得出來么,這么一位儒雅女子,在這場與非典抗爭的戰役中,竟是先頭部隊的總指揮。隔離——第一道最重要的防線是由她這樣的專家拉出來的。她就像臨戰的將軍,一時間院內大牌的教授、專家都望著她,“六億,你怎么說,我們怎么做。”
3天時間,她參與完成了醫院的非典病房臨時改造任務。之后,她又沖到北京市胸科醫院,參與第二輪的改建工程。之后;北京中日友好定點醫院的改建工地,依然有她的身影。她的種種設計方案和防護理念很快被大家認可。此前,各路有各路的高招,有些醫院防護服可以套到五層六層之多。趕上高溫天氣,一天熱暈過去的醫護人員就有好幾名。
“三層防護服是有道理的”,李六億這樣解釋,它是與三個不同的空間流程相配套:貼身服對應清潔區;防水服對應半清潔區;隔離服對應污染區。多一層則“贅”,少一層則“險”。號稱“多國部隊”的胸科醫院及其他幾家,覺得此說精當而且安全,于是紛紛效仿。
除此而外,在安裝排風扇的位置上,她也有特別創意——把排風扇安在房間的下部。理由是起塵的層面要放得比較低,這樣有助于呼吸層空氣質量。同時,她別出心裁,將低臭氧紫外線燈,調個個兒反向安裝。這算得上是急中生智。打破常規的做法;擴大了消毒燈的有效使用價值,使空氣消毒可以不間斷地持續。
她設立的監督員制度,也備受推崇。監督員會提請醫護人員,在哪個區,該怎么做;死亡病人該怎么處理;被針刺傷怎么應對……如此可以避免因為防護程序繁雜而亂了規章。對于一線人員大大增加了安全感。
李六億是中華醫學會醫院感染管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她參與過國家醫院感染管理標準的制定工作,并親手起草一系列規章、條例。美國1996年修訂的“標準預防”法案,它的翻譯并引進工作也是由她完成。
一份沉甸甸的責任(病死率1.0%)
在這次非典戰役中,可謂英雄輩出。細心的人可能發現,在諸家醫院頻頻亮相的時候,北大醫院卻絕少露臉。記者在5月1日《北京日報》登載的《首都勞動獎狀獎章獲得者名單》上,才找到了他們的名字。
在這場生死較量中,無論是救治的人數,承擔的重癥程度;還是投人一線的人員數量,在大型綜合醫院中他們均是名列前茅。
他們擔負著北京地區醫護人員感染的救治任務。因此,呼吸科主任王廣發壓力非常大。至少,在他的手上“一個不能少”。
“早用無創通氣”(即呼吸機)盡管效果明顯,但是他說,現在下任何結論都為時尚早。他承認自己有機會比較大量地接觸了非典病人,也因此獲得了一些對比經驗。早用,可以避免切開氣管感染的危險,更重要的是,臨床表明;等到出現呼吸窘迫癥,搶救起來就比較麻煩。他把使用呼吸機的指征,定在出現明顯的低氧血癥時。
在激素的使用上,他主張“適時用,及時減”。激素有一定的適應癥、禁忌癥。但是這不意味著因噎廢食。他反對干脆不用,也反對劑量過大。總之,非典的治療對于人類還沒有到說“是”或“不是”的時候。但是,科學需要前赴后繼。
在抗生素的使用上,他不主張一味地排斥。按照他的理論,不需要一來就上廣譜抗生素。早期,可以針對“社會獲得性感染”的病源,配合使用“左旋氧氟沙星”類藥物。兩周后,可以使用針對“醫院獲得性感染”的病源,投放“頭孢?類藥物。
近日,北京的疫情有所遏制。但是,王廣發他們的探索一刻沒有放松。
呼吸支持技術在這次控制疫情中極為重要。這方面出色的人才又是出在北大醫院。闕呈立,一位白凈文雅的女性。曾是加拿大魁北克省、世界著名的麥吉爾大
學博士后,主攻業務是呼吸生理。作為呼吸機使用方面的專門人才,她最先請戰支援北京佑安醫院。一個月后,北京市要求上報“五四獎章”人選。臨界40歲的王廣發被認定是對付非典的一號人物。但是作為科室主任,只有他知道,論付出,論事跡的感人,應該把闕呈立推上去。情急之下,他顧不得曾經的承諾,公開了一個秘密。
王廣發的“秘密”剛一脫口,舉座震驚,竟然有這等事——
闕呈立到佑安醫院的當天,正是她新婚的日子。不知道她和他是怎樣度過的那一夜。只知道一家人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匆匆吃了一頓便飯。愛難,別更難。而一別幾十天了,這位內向的姑娘竟能把嘴唇咬得那么緊。
院長章友康當時“忽”地拍案而起,“這個婚禮我們辦定了”。院長助理黃萬忠自告奮勇:“婚禮的主持我來。”很快,醫院管理層做出決定,明天一定要把人換回來,無論如何不能讓新娘子再上前線。
其實,在特大疫情面前,闕呈立這樣的緊缺人才,所有的明天,都只屬于病人。第二天,還沒踏進醫院的門,她又作為衛生部督導組專家,奔赴內蒙古疫區。至今尚未回來。記者只和她母親通了電話。對方聲音很柔弱,但是沒有抱怨:“我支持她。”作為301醫院老一代的醫務工作者,她對女兒有充分的信心。
4月3日,北大醫院發現第一例非典病人。護士長柴潔(抗擊非典,“首都勞動獎狀獎章獲得者”),平日在有著2800多員工的醫院里,安靜得像一滴水。但是,就在恐懼終于由耳聞變成現實的關鍵時刻,她用非常柔弱的聲音說:第一個夜班,我來。
自此,這家醫院無人言“不”。
綜合作戰,是北大醫院這次遏制非典的又一個秘密武器。除了“三駕馬車”之外,他們還有內科、中醫科以及心理衛生科等等。醫院黨委副書記、婦產科主任廖秦平說,這次許多病人的病毒血癥都非常厲害,這說明隨時可能出現心肌損害、肝臟病變或者腎功能衰竭……因此必須是各個器官功能的檢測、保護性治療一起上。
醫院傳染科副主任徐小元(抗擊非典,“首都勞動獎狀獎章獲得者”)認為,病人的生死全系醫務人員平日的功力和素質。對非典病人,醫生至少要做到“勤”。你經常出現在病人身邊,會從,b理上有很好的暗示治療作用。對于危重病人,他們專門配備有ICU室,全天監護,那真是連眨眼睛都非常小心。
在北京胸科醫院,北大醫院的病床數占到124張,再加上院內收治床位69張。總之,發病高峰的緊急關頭,他們承擔救治病人的份額相當于北京地區總量的十分之一。
1個多月來,經他們診斷、治療的病人已達300多例,死亡5例。其中早期急診室猝死2人。病房死亡3人。3人中一名85歲老人,一名癌癥手術后正在化療的病人,還有一位68歲的老人(非典已經痊愈,最終死于心臟病)。由此,醫院病房非典病死率僅為1.0%。難怪,緩解的病人被通知轉院時,都很不情愿。要知道,信任和信心,對于經歷過死亡考驗的人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在北京考察期間,重點看了北大醫院病區。他們認為:防護是一流的;治療是世界一流的;病人情緒是穩定的。
這是事實。他們是在向“最好”努力。“最好”被他們視為特殊的責任。
醫院黨辦主任孫揚說,對我們來說責任有--:一是作為醫護人員,神圣的職業責任;一是作為“國家隊”,我們不能推卸,我們沒有理由說“不”。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次一次地提出——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嚴格地說,這是沖著我們發出最急切、最神圣的囑托。
挺過最艱難的時刻
進入4月中旬,非典開始瘋狂。像是潘多拉魔盒突然被打開,一種高傳染性、高死亡性的災難從天而降。隔離,成為特定時期頭等的大事。而北京大規模的隔離設施那會兒還不知道在哪里。
疫情初期,北大醫院收留的非典病人多達百例。這是最危險的時刻,也是最悲壯的一幕。醫護人員是這一幕中最動人的角色。
必須盡快解決隔離病房,而且是戰地解決。醫院將一棟已經報廢的舊樓,重新接通水路、電路,加設空氣負壓裝置、氧氣管道。從設計施工到起用,后勤人員被逼上了建筑現場。
這是極特殊的工程,時間當以小時計算。因為每一分鐘的拖延,都意味著將有一撥健康的人成為病毒吞噬的宿主。但是,人的意志力終究不是神話。70多刊、時的連軸轉;終于有人倒在了水泥地上,不顧一切地打起了呼嚕。
13日,臨時隔離病房34張床位開出來,而當即人住病人超過50個。怎么辦?椅子搭椅子。只要能夠盡量收攏感染源,簡易床位一直搭到隔離區門口。整個病房就像一個快要撐破的紙盒子。那情景與泰坦尼克的悲慘是相似的,因為小小的救生艇是永遠無法承載突發的肆虐和巨大的災難。但是,盒子不能破!泰坦尼克的悲劇不能重演!
哪邊,新增病人還在不斷地往外冒。每天以十六七的數量擴增。醫院不得已又把急診科也辟成臨時病房。再開出35張床,同樣是應接不暇。幾天的工夫,院子里,大廳里,走廊里;平車上躺著,椅子上坐著,甚至還有自己提著藥瓶的患者……整座醫院籠罩在非典的陰霾里。
醫院的管理者們必須用他們的脊梁扛起突然坍塌的屋頂。病人—個不能往外推;醫護人員一個不能犧牲。所有的“不能”無限擴張地擠壓在一個容器罐里,隨時都會有爆炸的危險。出口,盡陜尋找病人的出口。
那是難以量化的壓力。
院長章友康感覺到血管突突地膨脹:我們是居民集中區,毗鄰北京四中,又緊挨著中南海。如果有病人流散出去,那將是歷史的罪人。
廖秦平氣促心急:累,我們不怕;病人多,我們不怕。但是,非典的惡性傳染力和殺傷力,決定了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保護健康人群。她說,就是把我們全院幾千顆心,揉碎了,掰開了,也想不出辦法呀。“醫院不封,我們就得瘋”。
李六億的“標準預防”立即變得蒼白無力。因為如果連最基本的隔離病房都解決不了,一切都是廢話。
4月23日,大家最擔心的事終于發生了,13名醫護人員一起感染。這是非正常情況下的院內感染。它是向所有的人發出獻身的信號。對于在醫院工作的每一個人來說,明顯地感覺到殘酷已經在撕扯自己的衣服。但是,就在這個時刻,北大醫院有1800人主動請纓。這是一個多么偉大的數字。、李六億多少次在電話里聽到兒子“想媽媽”的叫聲,她沒有掉淚。因為媽媽做的是有意義的事,做的是對得起兒子的事。但是那一天,她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鬼使神差地把電話撥到了衛生部。聽著對方“喂,喂”,她好像是有很多話要說,卻哽咽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終于,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小湯山等大覷模收治非典的專科醫院奇跡般的快速建成。24日,在付出沉重代價的第二天,病人出口疏通。程蘇華說,從下午開始轉移病人,一直轉到歡日凌晨4點多。終于,轉出病人80多名。
北大醫院經受住了非典的考驗。
危難已經是昨天。在特殊的日子里,他們還默默地收治了由北京地壇醫院轉出的艾滋病、梳行性腦膜炎傳染病病人;還是他們接納了指定為非典醫院的兄弟單位原有的透析病人;他們的婦科、產科手術沒有因為疫情而停止;他們的日門診量仍在上千人次;5月10日,他們開拍實施腎臟移植手術;12日,器官移植手術仍在繼續……
平日無虛夸,遇難敢承擔!北大醫院,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