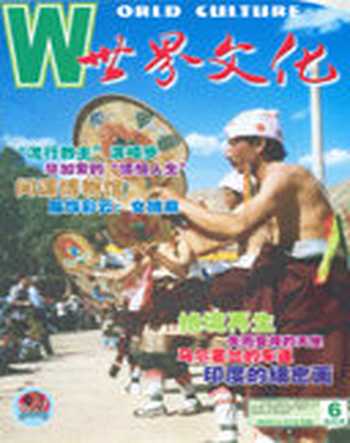玫瑰的名字
劉于嘉
1986年,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Jean-Jacques Annaud)執導了電影《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這部由法、意、德三國合拍的影片講述了發生在中世紀的一個故事: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本尼迪克特修道院中,接連發生了幾樁血案,引起了人們的恐慌和種種猜測。多數修道士認為這是上帝按照《圣經·啟示錄》中七個喇叭天使的預言在進行懲罰。睿智的修士威廉與弟子阿德索在調查中發現這連串悲劇與修道院里收藏的一本書有關。這本由亞里士多德所著的書從自然的角度解釋了人,其論點與當時教會宣揚的宗教理論截然相悖。修道院院長約杰瘋狂而愚昧地熱愛著他所信仰的宗教理論,惟恐人們在讀到此書時會重新認識真理,而使天主教數百年傳下的教義被推翻。因此,他把劇毒涂在書上,致使每一個看過它的人都離奇死亡,并假稱是上帝的懲罰。這一罪行最終被威廉與阿德索所揭穿。約杰在陰謀失敗后,放火焚燒藏有人類精神財富的圖書室,正義的修士威廉冒死搶救了一批書籍,而屹立百年的修道院卻在大火中化為灰燼。
影片在敘事上采用了好萊塢慣用的懸疑片結構,讓觀眾和劇中人物一同尋找答案。但我們得到的答案并不只是好萊塢式的“誰是兇手”這么簡單,而是一場啟示錄般的洗禮和深刻的思考。莎士比亞曾經說過:“玫瑰的含義是什么?那被我們叫做玫瑰花的東西,改稱別的名字,聞起來也同樣芳香。”如果用莎翁的話來解釋片名,那么影片中的“玫瑰”是什么呢?
在中世紀教會組織的黑暗勢力下,一切有關自然的理性的思考都有可能被冠以“異端學說”的罪名。但是,是否名為“異端”實亦“異端”呢?影片中那本亞里士多德所著的書即是真理和人類精神財富的象征。真理的光芒是掩蓋不了的,就像在影片高潮處,修道院院長妄圖用火燒毀古代哲人們的偉大著作,卻反而毀掉了象征宗教勢力堡壘的修道院。整部片子始終以灰藍色作為色彩主調,表現出中世紀所特有的一種陰冷氣氛,那場熊熊烈火在灰暗中燒出了一片光亮,暗示了真理的力量,蘊含著反抗的激情。大量象征符號的運用,使我們不能將影片內容簡單地理解為一場中世紀時教會與古希臘哲學的爭斗。導演阿諾站在人文主義者的立場,設置了衛道士、陰謀家、隨波逐流者、消極避世者、真理捍衛者這些產生于特定的矛盾斗爭旋渦的人物,代表了處于新舊事物沖突之際的不同心態。主人公威廉由英國著名演員肖恩康納利扮演。作為影片中真理的捍衛者,他敢于突破黑暗社會造成的樊籬,保護人類文明史上的精神財富;追求理想,卻不至于淪為極端信仰的奴隸,是一個理性的概括性形象。
影片中另有一對矛盾更加引人思索。威廉修士的徒弟———16歲的阿德索邂逅了一位美麗的山村少女,兩人一見鐘情并不可遏抑地發生了關系。導演在表現這段激情時運用了自然主義的手法,讓人的本性在原始的號召下自然地迸發。阿德索平靜的修士生活被攪亂了,如果選擇繼續從師學習知識,就不得不放棄愛情;如果選擇與心愛的姑娘生活,就失去了平靜清修、追求理想的機會。這對矛盾不斷地、激烈地沖擊著他年輕的心。修士不能享受世俗生活,平民無力接受教育。最后,在理想與愛情之間,他選擇了前者。當阿德索騎著馬,漸漸消失在少女淚眼模糊的視線中時,觀眾似乎得到了來自于編導的答案。但是,在影片結尾處,年老的阿德索卻留下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語:“……我從老師那里學到了很多知識,并且成為了一個博學的人,我也從未后悔過當初的選擇。但每晚出現在我夢中的,卻是那個不知道名字的姑娘。”
這種典型的歐洲式的開放性結尾又一次讓我們陷入沉思。在虛偽和真理之間,毫無疑問真理是“玫瑰”,而在理想與愛情之間,又該如何作出選擇呢?影片利用中世紀的氛圍,反映出來的仍是與當今社會相關的思考。即使環境變了,社會規范變了,人類面對的矛盾卻沒有變。影片中,威廉修士告訴阿德索:“沒有愛情的人生,是平和的、安全的、單調的、乏味的。”怎樣選擇,就要看個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