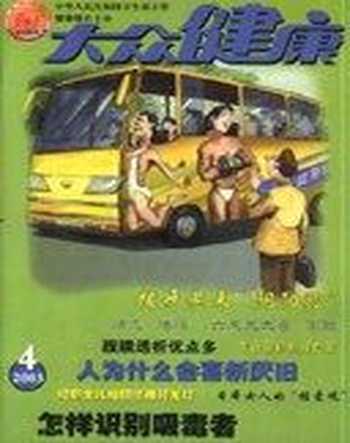腦死亡,人們能接受嗎
段振離
面對已經發生腦死亡,只靠機器維持呼吸、心跳,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搶救成功的親人,您是選擇放棄還是繼續?一個理智的聲音說:既然毫無希望,就不要白費勁兒了。可親情的呼喚卻讓您不忍放棄。就這樣,一個關于死亡的概念——腦死亡,從一出現似乎就處于矛盾之中。
傳統死亡標準受到挑戰
生、老、病、死是人生命的自然規律。在醫學領域內,醫學家們對前三者研究殊多,惟獨對死亡研究得最少。今天人們能夠聚焦死亡,足以說明醫學的進步和人們觀念的更新。過去,因腦干功能喪失而導致自主呼吸消失的患者心跳一定很快停止,理所當然的,呼吸、心跳停止就意味著死亡,這是決定是否死亡的金科玉律。而今,這一傳統的死亡定義卻受到了挑戰。
今天,面對一個腦干和大腦功能完全喪失的病人,現代醫學技術有很多辦法可以使他不“死亡”:呼吸支持技術可以對已停止呼吸的病人進行人工呼吸;循環支持技術可以使病人的心臟繼續跳動,血液循環繼續進行。表面上看,病人并沒有死亡,因為他的心跳、呼吸并沒有停止。然而,由于腦功能已經喪失,他的心跳、呼吸也并非自主進行,而是靠人工進行的。所以,一旦撤去機器,心跳、呼吸也就停止了。
有關學者認為,人的死亡,關鍵在于“腦死亡”,而不是“心死亡”。以腦為中心的中樞神經系統是人體的司令部,是整個生命賴以維系的根本,神經細胞一旦死亡就無法再生。如果全腦功能因為神經細胞的死亡而陷入無法逆轉的狀態時,全身各個臟器功能的喪失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大量臨床實踐證明,凡是腦干功能喪失者,即使人工呼吸維持再久,也沒有搶救成功的實例。
解讀腦死亡
腦死亡的臨床診斷標準有以下4條:1.自主呼吸停止。自主呼吸的產生依賴于中樞神經系統不同部位神經元的協調與整合,它的消失無疑是神經細胞廣泛損害的結果。2.不可逆的深度昏迷,對外界刺激毫無反應,無自主性的肌肉活動。3.腦干反射消失,瞳孔散大,對光反射消失。4.腦電圖呈平直線,說明腦部已沒有電活動。以上臨床現象均表明,患者的絕大部分神經細胞已經死亡。為慎重起見,應當在24小時或72小時內反復測試和多次檢查,只有當結果無變化,并排除體溫過低(<32.2℃)或剛服用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兩種情況時,才能正式做出腦死亡的診斷。
值得一提的是,腦死亡不同于植物人。植物人的昏迷不醒是由于大腦皮質受到嚴重損害或處于高度抑制狀態,其腦干功能還是正常的,因此病人可以有自主呼吸、心跳和腦干反應;植物人能睜眼看人,但視而不見;少數病人還有蘇醒的可能性,這在專業雜志上已有報道。當然,植物人可以轉化為腦死亡,但植物人絕不等同于腦死亡。
讓腦死亡者死得體面
按照傳統的死亡標準,只要人的呼吸、心跳不停止,哪怕腦干已經死亡,也要奮力搶救,這被認為是醫生的天職。明知不可能活過來,還要繼續輸液、輸氧,繼續應用昂貴的藥物(有的一天就耗費數千元甚至上萬元),既浪費了醫療資源,又增加了病人家屬的經濟負擔。對這種行為,醫生沒有感到不正常,還美其名曰“做到仁至義盡”,對病人家屬似乎也是一種精神安慰。然而,從腦死亡的角度看,這是一種愚昧的醫療行為。據粗略估計,國家每年為此支出的醫療費用達數百億元,因為搶救一名腦死亡患者一天所消耗的醫療資源是普通病人所需費用的十倍甚至百倍。同時,這種醫療行為還嚴重影響其他的搶救工作。
醫生是一個崇高的職業,之所以崇高,是因為他應有良好的職業道德:愛護病人,尊重病人。病人既有有社會呼喚《腦死亡法》
尊嚴地活著的權利,同樣也應當享有有尊嚴地死去的權利;他活著的時候應受到尊重,死亡時也應受到尊重。可目前的事實是,只要經濟條件允許,很多病人家屬不會選擇放棄。即使經濟條件不好,他們也會東湊西借,以延續病人的“生命”。于是,醫生給腦死亡的病人插上許多管子,并且不斷進行人工呼吸、體外心臟按摩。這些醫療行為,對于生命垂危的病人,無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對于一個腦死亡的病人,純粹是無效的勞動,只能是讓病人更受折騰,使病人的尊嚴喪失殆盡。那么,病人家屬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接受親人已經再也救不活的事實,更無法承受失去親人的痛苦。說到底,他們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慮自己的感受,卻沒有考慮病人的“感受”。如果一個腦死亡的病人能有感受的話,相信他一定會在生存絕望的前提下,選擇安靜、體面地死去。可腦死亡的病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感受了,所以只好由著親屬為他做主了。早知今日,我們何不趁活著的時候為自己寫下遺囑,選擇死的尊嚴呢?
社會呼喚《腦死亡法》
腦死亡的判定有助于推進器官移植醫學的發展。據醫學資料披露,目前我國心、肝、腎等器官移植技術已達到相當的水平,由于沒有腦死亡立法,我國的器官供體質量不如國外,數量也難以保證。我國目前有約150萬尿毒癥患者在急切地等待腎移植,但由于腎臟來源匱乏,每年僅能做3000例腎移植手術;我國有約400萬白血病患者在等待骨髓移植,而全國骨髓庫的骨髓加到一起才3萬份;我國約有數千萬肝病患者,其中一部分最后會發展為肝硬化,而對于大多數晚期肝病患者,肝移植是惟一的治療手段,可目前肝臟的供給比腎臟還緊張。許多晚期肝硬變患者因等不到器官而死亡。
腦死亡者的器官有很大的利用價值。假若有一個《腦死亡法》,而死者生前又同意捐贈器官的話,那么即使人死了,腦死亡者的器官仍可以為他人服務。然而,在我國,這一法律的制定與實施談何容易!幾千年來,儒家的傳統觀念在我國根深蒂固。人們信奉“軀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即使是死后,也要保留尸體的完整。許多人認為,人都死了,還要取其器官,未免太過殘忍。其實,這只是陳舊的思想觀念在作怪,我們不妨換個角度考慮,這些器官在腦死亡者的身體中已不再具有生命力,而移植到他人身上,則可以使之獲得新生,使生命因此而得到延續,這樣不是更有意義嗎?
承認腦死亡并不意味著腦死亡者都要進行器官捐贈。那些通過了腦死亡標準的國家,他們的器官供體仍然十分匱乏。因為器官捐贈必須尊重死者生前的意愿,辦理相關的法律手續,并進行公證,使器官捐贈正常有序地進行。而且,《腦死亡法》的制定也不僅僅是器官移植的需要,它的社會效益是多方面的。
世界上第一個腦死亡的診斷標準是1968年由美國制定的,不久美國又提出腦干死亡就是腦死亡的概念。1976年,英國皇家醫學院通過了腦死亡的原則。1981年,美國通過了確定“腦死亡”的醫學、法律和倫理的報告,并在全國執行“腦死亡”的統一標準。1983年以后,西方國家已經普遍接受了“腦死亡”原則,并制定了相應的法律。亞洲的日本、印度等國也已頒布了腦死亡法。我國也開始推行腦死亡概念,著手起草以腦干死亡為死亡標準的《腦死亡法》,以實現與國際接軌。筆者認為,考慮到我國的傳統習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腦死亡”與“心死亡”并存也未嘗不可。
至于腦死亡的判定,不是哪個醫生就能說了算的。除了有嚴格的診斷標準外,還必須有一整套嚴格的程序。應該由一個獨立委員會來做出決定,而該委員會的成員應是來自不同專業的專家。未來的《腦死亡法》無疑是十分嚴謹的,因為它要經過各行各業的專家論證,并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關鍵是執行時的公正和嚴肅。用老百姓的話說,“經是好經,不要叫歪嘴和尚念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