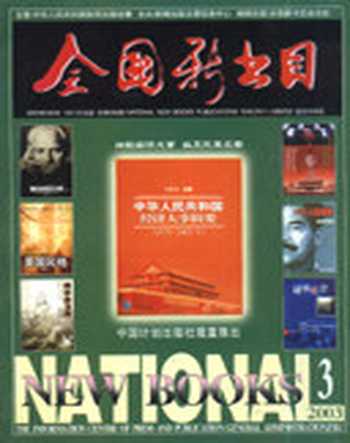作家沈喬生推出最新力作《狗在1966年咬誰(shuí)》
朱安妮

曾創(chuàng)作長(zhǎng)篇小說(shuō)《股民日記》、《白樓夢(mèng)》、《就睹這一次》的著名作家沈喬生推出他的又一部力作《狗在1966年咬誰(shuí)》。這是一部描寫人在恐怖中失重的小說(shuō)。在當(dāng)代社會(huì)中人們的各種各樣恐懼情緒(如犯罪威脅、遭遇傷害、下崗、失業(yè)、環(huán)境污染、艾滋病威脅等等)還普遍存在的情況下,這部小說(shuō)的問(wèn)世有它的特殊意義。
小說(shuō)的背景是1966年的上海,一個(gè)15歲的男孩,資產(chǎn)階級(jí)家庭出身的狗崽子,在當(dāng)年的恐怖中游弋。兩個(gè)母親的愛(ài)在爭(zhēng)奪他,又在撕裂他,顯現(xiàn)了一段真實(shí)而又荒誕的生活,唱出了一曲黑色的青春祭歌。和以往反思小說(shuō)不同的是,作品的鋒芒不是指向外部,而是指向主人公內(nèi)心,在自己身上抓鬼。故事生動(dòng)有趣,使人在感覺(jué)精神痛苦的同時(shí),忍不住捧腹發(fā)笑。
在小說(shuō)中,作者用許多鮮明而生動(dòng)的細(xì)節(jié)一再提出一個(gè)命題:人擺脫恐怖的方法是什么,是把別人也拖入恐怖中去嗎?從而對(duì)人性的弱點(diǎn)作了一次深刻的拷問(wèn)和反省。小說(shuō)有著出色的描寫、神奇的想像力和深刻的黑色幽默。
著名學(xué)者、華東師范大學(xué)教授王曉明對(duì)作品予以肯定,他認(rèn)為:“我們每個(gè)人都有不愿意重新翻檢的往事。個(gè)人也可以完全拒絕回顧歷史。但是一個(gè)社會(huì)卻不能這樣做,因此,我們的社會(huì)一定會(huì)挑選一些特別的人,以各種方式逼迫他們不斷地翻檢記憶。這翻檢當(dāng)然是不愉快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也正是這些人以自己個(gè)人的痛苦,為社會(huì)挽回了名譽(yù):它終究告訴了活著的人,你們的現(xiàn)在正是由于過(guò)去造成的,而且這過(guò)去還將一直活在你們的將來(lái),你們?cè)绞菍?duì)它閉上眼睛,它就越可能比你們活得長(zhǎng)久。在這些特別的人當(dāng)中,作家經(jīng)常是人數(shù)最多的一種。小說(shuō)喚起了我的大量記憶,有許多我似乎忘記了的兒時(shí)的人事,都在作品里活靈活現(xiàn)地跳了出來(lái)。作家更讓主人公經(jīng)歷了大量的情感和理智的折磨;得意、張狂、恐懼、悔恨、軟弱,陷在家庭和政治的紛爭(zhēng)的漩渦中上下起伏,可說(shuō)是遍體鱗傷,卻始終孤立無(wú)著……”
著名文學(xué)批評(píng)家洪治綱認(rèn)為:“沈喬生的這部小說(shuō)以一種強(qiáng)勁的力度,將生命中最富詩(shī)意的成長(zhǎng)過(guò)程,演繹成一種人性中最為慘痛的裂變,使生命的啟蒙變成了一場(chǎng)悲劇性的祭奠。”
作者沈喬生承認(rèn),這部小說(shuō)有一定的自傳成分,不少細(xì)節(jié)都是實(shí)有其事,是當(dāng)年作者親身經(jīng)歷的,是經(jīng)過(guò)30多年的沉積在作者心中無(wú)法消磨的。但是,他又說(shuō),作品是經(jīng)過(guò)精心的藝術(shù)構(gòu)思的,即便是真事,也是用藝術(shù)的筆法來(lái)描寫的,從這層意義上說(shuō),它是一部小說(shuō),或者說(shuō)是一種邊緣文體。責(zé)任編輯伍恒山認(rèn)為,這是一部釋放心靈隱秘的亞自傳體小說(shuō)。
由于小說(shuō)表現(xiàn)的是少年成長(zhǎng)的故事,所以,一些讀過(guò)該小說(shuō)的當(dāng)代青年讀者也覺(jué)得津津有味,很得人心。這不僅得力于文筆的饒有生趣,還因?yàn)殡m然相隔36年,但是青年人的心是相通的,在幾十年這個(gè)時(shí)間段里,人性的要素并沒(méi)有發(fā)生多少變化。
《狗在1966年咬誰(shuí)》沈喬生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03.1定價(jià):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