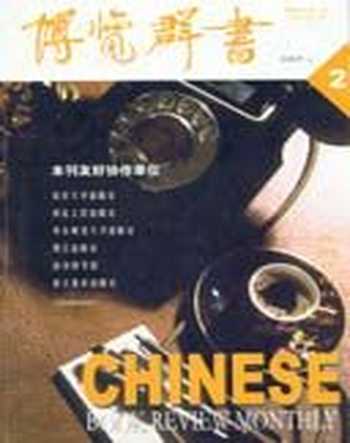問題:學術研究的起點
梁 工
《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有一句名言:“灰色的理論到處都有,只有生活之樹四季常青。”理論往往是灰色的,因為它一經出現,構成體系,就與其賴以產生的生活日益隔膜,喪失青蔥的生命本色而變得灰暗蒼白。而生活,則永遠是生命的本體,每時每刻都煥發出不可扼制的勃勃生機,從昨天走向今天,從今天走向明天,前行的腳步永不止息。
這樣的生活每日每時都在滋生出新的問題,期待著理論發出回應。理論的意義僅僅在于正確回答生活中涌現出的問題,使人得以積極主動地面向未來。只有能夠正視并正確地回答問題,理論才有其存在的依據和價值。而觀察問題、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不斷從傳統中開掘思想資源,在現實中完善、發展、變革前人的理論,則是學術研究的起點和真義所在。
基督教文化研究是一門延續了兩千年的大學問,一門涉及諸多科目的大學術,它的成長無時無刻不與形形色色的問題相依伴。舉一個圣經考據學的例子。在發現希伯來詩歌的平行體之前,傳福音的馬太敘述道:“門徒牽了驢和驢駒來,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太21:6,7),他相信,這件事應驗了古代先知撒迦利亞的預言(太21:5,參見亞9:9)。然而,馬太卻給讀者留下了問題:既然門徒牽來兩只牲畜(驢和驢駒子),他們把衣服搭在了哪只上面?耶穌又騎在了哪只上面?隨著平行體為世人所認識,這個問題的答案昭然若揭了:“驢”和“驢駒子”乃是同一回事,撒迦利亞所謂的“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本是一個遞進式平行句,后句中的“驢駒子”其實是對前句中“驢”的進一步闡明。平行體的原貌彰顯之后,一系列類似的問題也大白于天下:拉麥復仇時殺死的“壯年人”和“少年人”實際是同一個人(創4:23),雅億擊打西西拉的“橛子”和“錘子”也是同一件器具(士5:26)。顯然,后來雅億故事的散文敘事者忽略了希伯來詩歌的平行體,而將雅億擊打西西拉的情節誤寫成“取了帳篷的橛子,手里拿著錘子,……將橛子從他鬢邊釘進去,釘入地里”(土4:21)——乙使同一件器具變成了兩件。這個例子顯明,正是文本中的問題吸引著研究者的目光,而說到底,學術思維的焦點就是各種各樣的問題。
作為古希伯來歷史文化的積淀物,兼為地中海周圍亞歐非三大洲古代文明的某種凝聚體,基督教文化的原典圣經是一座博大精深的思想庫。它不但印證了古猶太民族生生不息的奇跡劇,而且為基督教文化的延續、更新乃至世界文化的成長和演變貢獻出取之不盡的精神資源。然而,這種貢獻從來不是簡單直接地實現的,因為面對新時代提出的種種新問題,深藏于圣經文本中的資源還有待于后人的持續發掘和勤奮開采。而發掘和開采的必然性和艱辛性,就是圣經闡釋學,也是基督教神學研討長盛不衰的根源。
針對“希臘化背景下猶太人如何承續本民族傳統”問題,紀元前后的猶太哲人斐洛嫻熟地運用喻意解經法,將希伯來的宗教理想與希臘的哲學理念彼此調和起來。針對“基督教如何破除猶太藩籬而獨立發展”問題,耶穌對摩西律法做出全新闡釋,抹煞其民族主義內核而賦予它普世主義的靈魂。針對“流散異域的猶太人如何靈活自如地應對新生活”問題,一代代猶太拉比持續進行“口傳托拉”的匯纂,編出卷帙浩繁的釋經大典《塔木德》。針對“上帝的意志如何在歷史中運行”問題,奧古斯丁從公元410年羅馬城陷落事件中引申出有關“上帝城”的理念,認為上帝之城與世間之城并存,世俗國家只有依附于教會,才能投入上帝的懷抱。針對“信仰、理性和神秘主義的關系”問題,托馬斯·阿奎那在《神學大全》等巨著中構筑一個龐大的經院哲學體系,以雄辯的論證使三者達到完滿的統一。針對“新教信徒如何有力地反對教皇”問題,馬丁·路德發展古猶太先知哈巴谷的思想,闡明“因信稱義”理論,并親自翻譯德文圣經,把讀經和釋經的權利歸還給廣大信徒。針對“圣經研究的多元闡釋是否可能”問題,當代哲學家保羅·利科將意志與行為理論、現象學、精神分析理論、結構主義、符號學、語言修辭學、敘事理論等多種元素匯人其理論構架,筑成一種頗具兼容性和調和性的闡釋學體系……可見兩千年來,各種問題層出不窮,思索問題、回答問題的基督教文化研究也從來沒有停止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