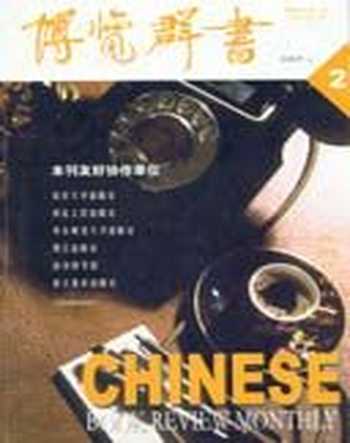中國近代棉紡業發展史的重要資料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陳梅龍執行編纂的《上海機器織布局》(盛宜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六),共輯錄、考訂了盛宜懷書信、函電、奏稿、文札、簿記等珍貴檔案資料七百余件,近五十八萬字。這是中國近代史史料建設的又一重要成果。
上海機器織布局是近代中國第一家“官督商辦”棉紡織企業,在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工業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織布局的資料,以往雖曾有搜集,但由于種種原因,還顯得十分缺乏、零散。新出版的《上海機器織布局》一書對織布局的創辦經過作了詳細披露。開篇的第一則史料《黎兆棠致盛宜懷函》,足征織布局的創辦始終控制在北洋集團手中。
此書不僅使我們對織布局的人事轉換及其原因更加清晰,而且在其資本籌措、場屋建設、地址選定、購料建工等有關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大量信息。
1893年11月,織布局開工生產僅三年后,即因清花車間起火而遭致全廠焚毀,損失慘重。李鴻章札委津海關道盛宜懷赴滬規復。據悉,在12月初,盛宜懷便“已集商股銀三十萬兩,并蒙憲臺面諭,將各局閑款附搭官股銀二十萬兩,不分官商,均作股分,一律派利”。可見華盛是有官股的。盛宜懷到滬后“擬就織布舊廠墻址煙囪建造一層樓,并就原有之五六百匹馬力機器鍋爐,裝置細紗機七十張,約二萬五千左右錠子,先行紡織,……并另選清花軋花廠一座,錢房數座,總期來年六月出紗”。這些資料反映了盛宣懷規復華盛的具體思路。盛宜懷一邊建廠,一邊又推行“限錠四十萬,布機五千張”的主張,以期在繼續實施北洋集團對棉紡織業壟斷的同時,又能給集團中的一些人,當然也包括著自己和家族以辦廠的權利。《上海紡織公所華商上李鴻章稟》是迄今最完整反映這一計劃及設廠范圍、規模的材料,十分明確地指出了十個廠的名稱,設機的數量、規模及地點,有助于解決對這一問題的爭議。
洋務企業的重要特點就是嚴重的官商矛盾。“官為扶持”既給洋務企業的興辦提供了條件,但同時也給洋務企業的發展造成阻滯。《上海機器織布局》對此有比較多的披露。《布案駁議》就是其中很有分量的一篇。這篇出自經元善之手的駁文是這樣寫的:“龔道(即龔壽圖)稟稱入股五萬四千兩,查賬上只有四萬兩。……龔道稟名諂附阿私,希圖侵蝕,又將覬覦其后,不知所指名諂附者何人?若謂諂附鄭道(即鄭觀應),則名方且稟請嚴札飭催。……尚有何事可以覬覦哉?”其他如《趙吉致盛宜懷函》中所揭示的:“在唐某(唐霖溪)架詞捏稟,希圖狡展,而莫公(莫祥芝)不卜,因何與閣下勢不相能”;如《薛福成致李鴻章函》所揭示的:“龔如在局,恐又致散場,最妙莫如撤去,否則假以事權”等,均無不表明織布局內官對商的挾持、欺凌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華盛建立以后,盛宣懷秉權于一已,為規避風險,屢施招商承包。承包商馬裕貴“冤單”披露:“未包以前,面稟督辦、總辦,廠中務需預備三個月零星物料始能接手,及至接手,察看機器動用器具,無一齊全,無一應手,……乃為此大聲疾呼,而京卿仍置若罔聞”。這些則從另一個角度揭露了官對商的侵奪,有利于我們認識甲午后官商矛盾的新發展。
華盛建廠以后,盛宣懷是如何一步一步將企業演變為個人私產,是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但限于資料,總語焉難詳。《上海機器織布局》為我們提供了探究的又一把鑰匙。其實早在織布局初創時期,盛就采取假公濟私、偷梁換柱的手法,以礦務局的抵押公款,轉換為自家錢莊的私款,楔入織布局而成為股東。其心腹趙吉的密函就道出了其中的奧秘:“機器局一事,尊意擬將四萬兩盡作股分,高見極是……一則將來可推入公款,不致大受虧損,二則我將此四數和盤托出,既歸彼局(指彭汝琮之后的紡織新局)之股,若彭姓糾纏,彼局必幫我拒彭。”織布局火燒后,盛宣懷奉命規復,其父盛康就想乘機舉為總辦。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有這樣的話:“我年屆八旬,精力尚健,汝系現任,萬不能抽手,中堂如見信或委我會同商辦,汝意以為然否,此話外間切勿響起,存而不論可耳。”后來盛宣懷委堂弟盛宙懷(字荔蓀)為總辦,但權力和股票始終控制在自己手里。他與盛宙懷的那些聯號信及不斷發生的股票轉換都足以證明這一點。不僅盛宣懷的舉動,從他老婆莊畹玉的信函中也可看出他們已把華盛(當然包括它的后身又新和三新)當作盛氏私產:“現今華盛你在家時只曉得折去五十一萬,據永珊(盛宣懷外甥)、永韶等俱說結來共要折六十余萬,想荔蓀如此糊涂,由別人瞎鬧。……你再不將此人(指韓仲藩)歇去,華盛越無收拾矣”(1899,12,12函);“再華盛越越不對,荔蓀三個禮拜不到此,紗布公司賬房管賬人十分糊涂,據大少奶奶來說,華盛終不會好,大純比華盛好,吾為此華盛十分心焦”(1899,12,16函)。這些話對我們認識華盛的性質及其演變無疑是很有好處的,這里實際上也透露著中國民族資本形成的又一條道路。
同西方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也是織布局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這方面,《上海機器織布局》也提供了相當多的寶貴資料。尤其是使我們明確了不少借洋債的問題。其實,早在1884年,織布局即有“洋商旗昌亦愿入股合辦”之議,只是因李鴻章:“旗昌人股顯違定章”而作罷。次年又有“向匯豐姑商借股本銀二十萬”之說,至于李鴻章最后是否“俯為作保”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在1888年前織布局已有洋債的進入是毫無疑問的,因為該年盛宣懷致李鴻章電中有“擬每年撥還官款二萬,洋債本利二萬六千”之語。馬關條約以后織布局向西方的借款繼續增加,且密度、額度都有增多的趨勢。這些材料對于認清織布局借款的背景、數量、來龍去脈,進而探討其性質和影響無疑是極有幫助的。另外,在如何引進機器設備上本書也披霹了許多重要材料,不僅正確反映織布局訂購國外機器設備的種類、數量、價格、產地、付款方式,也展示了招投標等近代商業規范在中國的開始運用和西商為爭取貨主業務而展開的激烈競爭。至于聘用洋匠的合同則更讓我們看到了織布局洋匠的人員選定、崗位職責、薪資待遇和工作情況。
《上海機器織布局》一書除了發掘了大量織布局及其后身華盛、集成、又新、三新的歷史資料以外,還使我們對與此相關的一些企業,尤其是棉紡織企業有了更多的了解。大純紗廠就是其中之一。以往對大純紗廠的創辦者及其規模、生產等了解甚少。有的文章僅表明其創辦者“盛某”。現在從盛宙懷、嚴信厚致盛宣懷函以及《大純機器紡織廠商辦說略十二則》等來看,大純的前身系由中國電報局總辦楊子萱(宇廷杲)添設的大脖紗廠(可能創始于1893年織布局火燒前)。北洋決定創設華盛紡織總廠后,改由盛宜懷的大兒子盛揆臣經辦,并漸至變為盛家私產。裕源的創辦亦如是。從朱鴻度與盛宣懷的往返信函看,裕源廠的肇發,系出自于盛宣懷、朱鴻度共同的意愿,且兩人各占一半股份。后來在辦廠過程中頗費周折,朱鴻度遂以“鄙意封河尹邇,將來往返函商事不便”為由,提出將先事定購五十張布機(后有擴大)由己獨辦,“一切用人、造廠等事亦暫歸一手辦理”,遂成為后來的“朱局”,即裕源。朱鴻度明言“往返不便”,實質是為了擺脫官勢的束縛。后來李鴻章給盛宣懷電文足資證明。除了紡織企業以外,織布局與其他洋務企業也發生著緊密聯結。早在織布局初創時期,湖北礦務局的押款就進入到織布局。1888、1890年北洋集團兩次對織布局的賬目進行查勘。至于招商局在織布局余地附設紡紗廠,“議定租價,書立租契,俾沾方便之益,而無混淆之嫌”,則更反映著兩者的關系。總之,《上海機器織布局》對我們探究其他洋務企業及其與織布局的關系,也頗多幫助。
縱觀以上,《上海機器織布局》一書內容翔實、豐富,是我國近代較完整、較系統的工業資料,將會對中國近代工業史、經濟史的研究起到促進作用。
(《上海機器織布局》,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陳梅龍編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版,46.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