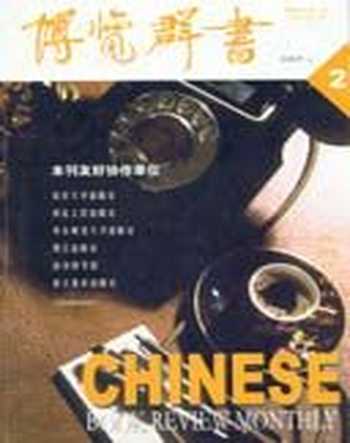往事中國
方漢文
“海塵新生石山下”,“劫灰飛盡古今平”。
世界文明古國無不歷盡滄桑,經受血與火的洗禮,在歷史長河中體驗民族的榮光與屈辱,換來了深刻的民族記憶。而且大多數古代文明都已經只留下昔日的光榮,它作為一種文明的本體已經發生了所謂的轉型(transition),與原有形態相去甚遠了。
希臘輝煌的創造在羅馬人的鐵蹄下成為廢墟,最終匯入基督教文明之中。古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早巳消失于雅利安人的利刃之下,甚至在古老的吠陀經典中都已經無法追溯其起源,只有借助考古學發現才有可能想象當年的興盛。而最早的埃及文明更是早早地轉化了類型,留下金宇塔與獅身人面像作為記憶的物化形態。幾種主要的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國古代文明歷史奇跡般地傳承下來,經歷五千年風雨,至今仍然屹立東方。但是尤可諱言,在我們民族的記憶中,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百年歷史,卻是五千年中最令國人感到屈辱與痛苦的時期。雖然如此也不可否認,這也是中國文明變化最重要的時期。記錄這一變化的印象與影響,從西方人或長期經西方文化熏染者的目光中來發現中國人的形象特征,以他人的目光來凝視;于是就有了“往事中國”這一叢書。這一叢書把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這一歷史時期中人們特別是西方人,從各種視角,抱著各種目的,說著各種話語的對于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上至宮廷朝臣,下至販夫走卒的觀感、評論盡收于此。以此來為我們認識近現代以來的中國、中國文化、中國人的性格提供一個參考。特別關注的是所謂民間的話語,這是種種最鮮活的話語,近似于巴赫金所說的與官方話語不同的“狂歡節話語”。只不過這種話語所面對的是一個有古老傳統的國度,一個與西方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人類生活中的驚異與發現中,最鮮明的、最令人心動的莫過于對與自己相異的種族的印象。所以達爾文《人類的由來》一書中,記述了當時一些生物學家和人類學家的爭論:不同種族的人類,如非洲黑人與歐洲白人等,應當被看成是同一個種,還是不同的種。事過境迂,盡管人們現在已經有了并習慣于對這類問題成熟的見解,但不同種族之間、不同民族文化間的差異,仍然是人類好奇心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所以近代以來,當中國人與南海附近的太平洋島國上的居民接觸時,由于看到其外形與自己有如此大的差異,竟然有人驚嘆:其人幾不似我類者。這種懷疑,可以說是與達爾文時代的歐洲科學家們十分相近。”伺樣,歐洲人對于久已聞名的中國人種與文化也一直十分好奇與驚異,因為從古希臘羅馬時代起,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就行銷歐洲了,但對于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的人,他們卻知之不多。所以近代海路開通以后,對于中國人的觀察印象才成為重要的歷史記憶。1515年,葡萄牙人皮雷斯在奉獻給國王的《東方諸國記中》說;“中國人的皮膚就像我們一樣白凈。”早在他之前,就有歐洲人斷言中國人與他們一樣是白色人種。中國人所熟知的利瑪竇也說過:“中國人的皮膚是白色的;但在南方各省,因為是在靠近熱帶,有的人比較黑。”西方人這種對于膚色的認同并不能使我們感到興奮,我們所關注的是世界對于中國人的印象,即世界其他種族和其他文化人類之于我們的評價,用法國哲學家薩特的話來說,是“他人的目光”。這是一種在主體之外對于主體的認識,這就使它具有了不同于自我的、獨特的視域。它的意義是多重的,并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旁觀者清”,因為文化判斷只能是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選擇,如果從他人來看,旁觀者也就是他人,是異己文化的立場,不能克服文化的自我認證,但可以看成是對于一種民族的文化記憶。這就是說,一種是榮格所說的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一種是對于其他民族的記憶、意識與無意識。
如果用更通俗易懂的話來說,一個民族對于其他民族會留下歷史印象,世人對于每個民族都有種族文化的記憶。這種記憶具有對于這個民族的人種、心理素質、性格特征、宗教信仰、創造發明、社會制度、語言文字、思維方式等種種現象和歷史事件的認知與評價。這種評價是這個民族的自我認識十分重要的參考。希臘人有一句名言——“認識你自己”,將其放之于一個民族,就是認識這個民族本身。
經過十七、十八兩個世紀中國與西方的大規模的文化交往,西方人對于中國的認識日臻成熟。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本身的地位也經歷了變化,成為世界殖民主義的中心。于是,從原先歌德、萊布尼茨等人對于中國古老文化的驚嘆與羨慕轉變為對于一個老弱國家的輕視與敵對。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大批的西方學者以重新發現現代社會背景下的中國為主旨,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中國印象的論著。這批論著的意義就在于:從現代社會認識角度觀察中國,從現代西方文明視域評價中國,從西方與中國文化的比較中來看中國。
這是有史以來最近距離的觀察中國;實際上世事難料,從“五四”運動以后,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歷史進程,西方與中國的關系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有的觀察已不適應于劇變中的中國與世界。于是一段歷史記憶被塵封起來,成了歷史的化石。如同琥珀,在它形成之初的千萬年前,把一只昆蟲包在松香中。當那昆蟲的同類早已經化為灰燼時,它竟然在琥珀的絕對真空中保持了當時一瞬間的形態。歷史成為了現在,保持了永恒!
正如艾略特《四重奏》中所說:“歷史就是現在和英格蘭”。
同一道理,我們這個叢書就是要復活歷史的記憶,回眸歷史話語,顯現人們對于中國的民族記憶與印象。這是活的歷史,是現在的前身,是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的關聯,是立足于現在的過去。
西方中心主義的視域是文中必有之義,現代意識的主導觀念發于西方,它先天地具有對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排異性,這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差異與同一,差異性產生的相吸引與相拒斥是同時存在的。因此當我們從上個世紀初的這些西方人(包括西化了的中國人),當時居于優越地位的西方人的眼光中,如果看到了殖民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的因素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它的實質。這也許只是他們眼中的東方,正像愛德華·W·賽義德所說,一個西方人臆造的東方。
當然,這不是個人思古幽情的闡發,而一個現代民族的自我認識,是歷史現象與其影響。正如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詩中所寫的,這是在歲月的額頭上刻下的標記。它使一種民族的記憶成為財富,即使這種記憶是痛苦的,作為一種經驗,也具有獨特的價值。越來越多的人關注民族的自我認證,其中有自我定位,也有一種自我省察。一個不能自我省察的民族是可恥的,也是可悲的。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給各國造成巨大創痛的國家,有的已經在反省,有的現在還在欺人欺世,這樣的民族和國家就是可恥、可悲的。而對于在戰爭中受到巨大傷害的中國,自省的含義之中就有牢記國恥,不忘弱國貧民的悲慘經歷。
中國人熟知“句踐(即所謂勾踐)雪恥”的故事。句踐復國,得之于民族記憶的鮮明,重視歷史的反省。同樣,古代猶太人走出埃及,擺脫了埃及人的奴役,但猶太人也沒忘記自己的歷史,他們有這樣一句格言:我們的祖先在埃及當過奴隸。
如果我們把這一叢書中的話語與當代中國相比較、相印證、相闡發,就是一種把歷史變為今日的手段。
(“往事中國叢書”,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