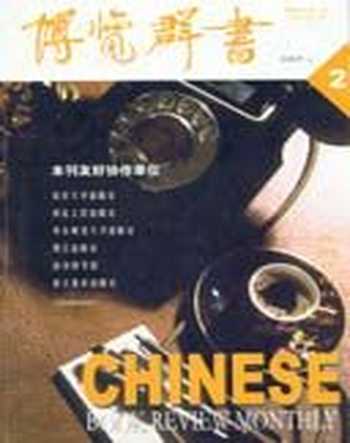尋求畫中的真歷史
東 來
新千年開始,人們的懷舊情感似乎與日俱增。熒屏和銀幕上戲說歷史的作品越來越多,書市上“圖說”,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涂說”歷史的“老字號”系列書也大行其道。經過現代的包裝和梳妝,歷史終于從千年和百年的封塵中走了出來,的的確確成了一個令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不論是戲說者還是涂說者,他所追求的是如何讓小姑娘既可人又可愛,至于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不在他的考慮之中。針對歷史學界批評“戲說歷史”的做法,有位戲說者則明盲:“我就是要氣死歷史學家”。
平心而論,戲說者或涂說者實在是有權利做他們喜歡的事,不過,他們似乎應該事先告訴讀者:“純屬虛構,且勿當真”,否則就有誤導讀者之嫌。對歷史學家來說,他們當然不會氣量小到被戲說的歷史和調侃的歷史“氣死”,不過,他們也應該捫心自問,自己是否鉆進象牙之塔,逃避了自己向大眾敘述真實歷史的社會責任?
看看我們的一些歷史學家,他們筆下的歷史是多么的乏味!在那里,鮮活的歷史變成了對抽象教條的注釋,豐富多彩的變化歸結于主義的演變,無數的風云人物簡單地貼上了好壞的標簽,現實主流的好惡成為歷史惟一的價值判斷。對他們來說,歷史或者是現實斗爭的武器,或者是一個民族自慰的良藥,其目的不過是促進一個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強。當歷史負載了如此厚重的責任,你還能指望歷史學家的筆下會有輕松而又益智的歷史嗎,在這種情況下,廣大觀眾和讀者從文人戲說和涂說中滿足他們的念舊癖,也就不足為奇了。
好在仍然有那么一些歷史學家,他們已經厭倦意識形態化的歷史,也痛恨偽歷史知識的廣泛傳播,認認真真地重構過去的大干世界,實實在在地傳播真實的歷史知識。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陳中丹博士就是這些學者中的一位佼佼者。繼倍受贊揚的《墻頭政治——現代外國宣傳海報解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之后,他又出版了第二本圖說歷史的小書:《畫中歷史——外國歷史畫解讀》。
作為歷史讀物,即使是普及性的,其第一要務仍然是真實可信。如何確定其可信度,一般是根據其參考的資料和引文出處來進行判定,遺憾的是,和所有歷史普及讀物一樣,《畫中歷史》沒有給出參考資料。盡管如此,讀者還是可以看出作者在資料方面的煞費苦心、力求真實可靠。比如,在介紹“飲鴆前的蘇格拉底”一圖時,作者特地給出了學界有關雅典處死其最出色學者的三種不同解釋。在評論“婦女向凡爾賽進軍”這一法國大革命的重大事件時,作者也給出兩種不同的看法。
除了介紹一些不同的觀點外,作者還對一些歷史圖片所展示的不合情理或似是而非的場景進行了細致的考證。僅以書中兩幅涉及中國的圖片為例。其一是表現1851年倫敦世界博覽會的精美圖片,其引人注目之處在于,前排恭賀博覽會開幕的各國使臣中,有一個穿清朝官服的中國人。如果不認真考訂,就會想當然地認定是清朝的官員。實際上,直到1866年清朝才有個知縣隨當時中國海關的英籍稅務司赫德去過歐洲。可見,他決不是清朝的官員。作者根據2002年上海學者的最新研究,指出此人是在上海經營絲綢的廣州商人許德瓊,并認為“他可能按當時中國官場的習俗捐過官,故有全套官員朝服”(87頁)。其二是“法國入侵越南”一圖。為了說明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作者選了一幅越南民間藝術家的作品,反映法國殖民軍隊人侵越南北部興化城,與中國軍隊對陣的情景,題名“興化陣戰”。作者并沒有就圖說圖,敘述中國軍隊當時的抵抗,而是進行具體深入的研究,最后發現當時中國守軍不戰而退,自毀營盤,根本不存在著這一對陣場面(185頁)。類似的考證在書中還有不少,反映了作者一絲不茍的史家態度。如果考慮到本書只是一本普及讀物,這一態度尤為可貴。
真實可信至關重要,但如果作者的解讀和敘述如同嚼蠟,也無法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真實性和趣味性在很多史家那里常常不可兼得,但《畫中歷史》卻很好地、甚至可以說近乎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首先,作者所采取的這一左圖右史、一圖一文(千字左右)、獨立成篇的形式,就非常吸引人,既可以一口氣讀完,也可以隨時翻閱,跳躍閱讀。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作者還用精煉的文字,結合圖片的主題,或敘事或白描或點評,或者兼而有之,來幫助讀者對圖片的了解。這一“螺螄殼里作道場”的本領,對一般的歷史學者來說,實在是強人所難,但陳中丹教授運用自如,甚至可謂是游刃有余。
在解讀拿破侖“撒出莫斯科”一圖時,作者給我們描繪了這樣的圖景:“到處是遺棄的死尸和大炮,有些士兵就地點起了篝火,……只有拿破侖戴著他那著名的三角帽,騎著馬,在竭盡心力籌劃如何把法軍帶出這一望無際的俄羅斯荒原”(107)。這樣的圖文并茂,讓人獲得了一種身臨其境的歷史感。在“羅馬暴君尼祿”一章,作者既結合了圖片說明了尼祿的殘暴和殘忍,又對尼祿的荒淫無恥作出描繪,而且還針對他愛好藝術的特點,把他與中國宋朝的亡國之君宋徽宗進行對比,感慨道:“在歷史上常有一些被命運播弄錯定角色的政治人物。這些人本有自己的特長,尤其在藝術方面,但恰好他們又有幸(或不幸)生在帝王家,有條件承繼大統,躋位君王。而這對他們來說是棄其長,揚其短,最終結局往往是悲劇性的”(32頁)。在評價人物上,作者往往是寥寥幾筆便勾畫了人物的基本特征。在《色當戰敗》中,他介紹敗將、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他“是拿破侖的侄子,處處以他英雄的伯父為楷模,但卻沒有伯父的雄才大略。他也愛好對外用兵,但卻沒有伯父的軍事才干;他也喜歡在國內表現親民的形象,但卻沒有伯父的個人魅力”(118頁)。這樣的敘述,使叔侄兩人的天壤之別,一目了然。
作者在序言中表示,在撰寫解讀文字時,他曾經想將《墻頭政治》重在敘事的“發事隱”形式變為重在說理的“發理隱”,但沒有成功。實際上,作者的這一目標本身就是不現實的,誠如哲人所云“歷史是用事例闡述的哲學”,離開了事例也就沒有了歷史。作為一本歷史書,永遠是以“發事隱”為主,“發理隱”往往是在“發事隱”基礎上產生的副產品。只有這樣的“發理隱”才自然,才周全,才容易為讀者接受。應該說,作者在這方面已經作得相當好了,其精彩的點評,俯拾即是。以介紹“古羅馬角斗”一圖為例。作者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借機對古希臘和古羅馬進行對比,言簡意賅,恰到好處,卻令人印象深刻。我們知道古代希臘和羅馬是西方文明的源頭,希臘的哲學與藝術和羅馬的法律與政治對現代西方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但這兩個民族的差別,在一般歷史教科書中卻語焉不詳。而作者結合角斗一圖,在說明羅馬人好戰嗜血的同時,還把羅馬人與希臘人進行對比,指出羅馬的神雖然脫胎于希臘的神,卻比后者更“好勇斗狠”。以愛神為例,希臘的小愛神是個張開翅膀飛翔的嬰兒,而到羅馬人那里,他“手中就多了一張可以傷人的弓”。“希臘人的城中多劇場,演出悲劇、喜劇,觀眾獲得的是藝術享受;而羅馬人的城中多角斗場,上演的是鮮血淋漓的格斗廝殺,看客追求的是感官刺激”。盡管角斗的盛行與羅馬人的軍事傳統有關,作者還是感嘆道:“古羅馬人居然能對同類想象出如此暴虐的娛樂,不禁讓人嘆惜‘人心惟危,而恥于與他們引為同類了”(36-37頁)。
作者常常能夠在解讀文字的最后,發出類似的感慨或聯想。作者選了一幅“宗教裁判所”的圖片介紹中世紀天主教迫害異端的種種暴行和酷刑,同時還特別強調,教皇給這些“最殘暴的非法手段冠上了神圣的名義”。“今天宗教裁判所的年代已往矣,但用刑訊逼供以獲取定罪口供的做法還沒有絕跡。這就是至今我們還不能忘卻過去這段歷史而要時時保持警惕的一個重要原因”(55頁)。
這樣的聯系和聯想是一般讀者鐘情于歷史的重要原因。而一個出色的歷史學者,為了便于讀者理解復雜多變的歷史現象,就是要想方設法調動讀者已有的知識背景,使其產生各種聯想,從而獲得讀史的樂趣和思想的啟迪。但要做到這一點,絕非易事。特別是在國人不熟悉的外國史領域,要讓讀者容易理解,適當對照、參照中國的歷史,或者討論中外之間的聯系和影響,實屬必要。
在介紹古希臘“斯巴達三百壯士“的結尾,作者筆鋒一轉,談及這一故事“曾在中國的清代末年給有血性的愛國男兒極大的鼓舞”,并以楊度的《少年湖南歌》和魯迅的《斯巴達之魂》為例。“今日我們觀此圖,憶舊事,耳邊似乎猶響1903年留日學生拒俄義勇隊電報中的鏗鏘言詞:‘夫以區區半島之希臘,猶有義不辱國之士,何以吾數百萬萬里之帝國而無之”(19頁)。“使團出行”則談的是1871年日本派團考察西方憲政的故事。正是這次考察,開啟和確定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日本由此開始殖產興業、脫亞入歐的現代化進程。從日本的使團出訪,作者聯想到1905年晚清“五大臣出洋”,但發現結果是如此的不同:“他們西游歸來不但未能開出救世良方,就連有關憲政的報告還要請避居日本的欽犯梁啟超和身為布衣的楊度起草,又怎能指望他們肩起拯危救亡的重任呢,”(179頁)。類似對比和聯想,在書中還有不少。
這些看似平淡的聯想和對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廣博的學識。國內新一代歷史學者,從讀研究生開始(有的學校甚至從本科生開始),就分為中國史和外國史,古代史和現代史,各自有著不同的課程內容和專業訓練。這樣早的專業化,自然導致各個專業領域學者知識面狹窄,視野有限,而按專業劃分的教研室體制,更導致學者間的相互隔閡,往往是老死不相律來。考慮到這一背景,作者把古今中外的歷史知識融于一體,打破這種學科的分野和隔閡,實在是難能可貴。這顯然與作者的訓練和志趣密切相關,陳教授雖然是世界近現代史的博士,但卻長期教授世界古代史;他雖然以世界史為業,但平常卻以大量涉獵中國文化歷史著述為樂。
翻閱這一百幅未必個個精美但卻內涵豐富的外國歷史畫,閱讀這一百篇未必字字珠璣但卻深刻獨到的千字文,實在是一種藝術享受和知識滋養。在讀圖時代有衰變為“偽圖時代”(借用2002年12月20日《中國青年報》的“讀圖時代還是偽圖時代”的表達)的時候,圖說歷史有蛻變為涂說甚至胡說歷史之虞,希望有更多的這樣嚴肅的歷史學者,像陳中丹教授投身于普及科學的歷史知識這樣的啟蒙的工作。
(《畫中歷史——外國歷史畫解讀》,陳中丹等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