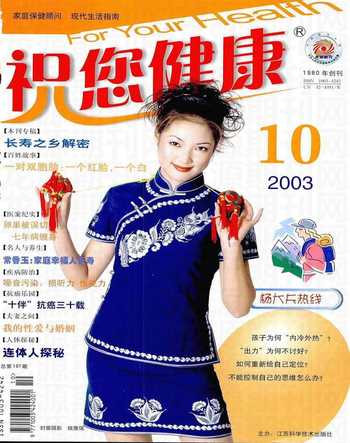妙用藥名賦詩文
黃河浪
藥名撰聯
某一中藥鋪“仁和堂”門旁的一幅對聯曰:“熟地迎百頭益母紅娘一見喜;淮山送牽牛國老使君千年健。”此聯精選十味中草藥名,用“迎”、“送”兩字自然而恰當地相連相串,對仗工整得體。又一藥店門聯日:“攜老,喜箱子背母過連橋;扶幼,白頭翁拾子到常山。”此聯共嵌六味中藥,喜箱子、白頭翁、常山三味是原名,貝母、連翹、時子三味各著一字諧音。全聯潛指醫師要具備救死扶傷、普濟疾苦的崇高醫德醫風。真乃“當歸方寸地,獨活世間人”也!還有期盼生意興隆的:“降香木香香附滿店,黃藥白藥山藥齊全。”中藥世家喜慶的:“琥珀青黛將軍府;玉竹重樓國老家。”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藥名諷貪
明代名醫李時珍在“中國藥鄉”湖北蘄春縣享富盛名。據傳,橫行鄉里貪掠成性的縣令要李時珍開具滋補藥方,李時珍一揮而就:“柏子仁三錢,木瓜二錢,官桂三錢,柴胡三錢,益智二錢,附子三錢;八角二錢,人參一錢,臺烏三錢,上黨三錢,山藥二錢。”這是一個藏頭藥方。每味藥開頭一字連起來便是:“柏木棺材一副(官柴益附),八人抬(臺)上山。”直氣得貪官連連跺腳,自認晦氣。明代還有位學者豐坊,給寧波縣令也開了具藥方:“大楓子去了仁,無花果多半邊;坡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顆。”此藥方用拆字添字法諷嘲貪官們是“一伙(夥)滑吏”,意賅言簡,入木三分,冷嘲熱諷。
藥名賦詩
清人趙翼語:“藥名入詩,三百篇中多有之。”唐代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此詩傾訴了與客相逢的衷腸,并巧用“地黃”、“半夏”、“枝(桅)子”、“桂心”四味中藥名,特別是將前句的尾字與后句的首字相連,巧妙地構成“連珠體”,讀來意味盎然,韻味十足。北宋洪皓的詩也頗有妙趣。“獨活他鄉已九秋,腸肝續斷更剛留。遙知母老相思子,沒藥醫治已白頭。”思鄉念母之情油然而生,妙用藥名賦真情,讀來感人至深,令人回味。
藥名填詞
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滿庭芳》一詞,把藥名隱于詞中,充滿了女子纏綿細膩的逸致閑情:“云母屏開,珍珠簾閉,防風吹散沉香。離情抑郁,金鏤織流黃。柏影桂枝交映,從容起、弄水銀塘。連翹首,驚過半夏,涼透薄荷裳。一鉤藤上月,尋常山夜,夢宿少場。早已輕粉黛,獨活空房。欲續斷弦未得,烏頭白、最苦參商。當歸也!茱萸熟,地老菊花荒。”寓草木以生機,寄藥名于情意,使人“悠然會心,妙處難與君說”。
藥名入戲
清代文人蒲松齡把中藥之功能、性味、特點,運用生、旦、凈、丑等角色行當加以編排,使藥物人格化,情節故事化,書寫成《草木傳》。如“清肺湯”一折中寫道:“那一日在天門冬前,麥門冬后搖了搖兜鈴,閃出兩名婦女,一個叫知母,頭戴一枝款冬花,搽著一臉無明粉;一個叫貝母,頭戴一枝旋復花,搽著一臉天花粉。金蓮來求咳嗽藥方,黃芩抬頭一看,即知頭面各般所有枳實俱是止嗽奇藥,放下兜鈴,匯成一片,便把那熱痰喘嗽一并治去。”有扮相,有音響,有動作,有化妝,活脫脫的一出好戲!看后,令人稱絕!
這真是“藥名賦詩文,韻味意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