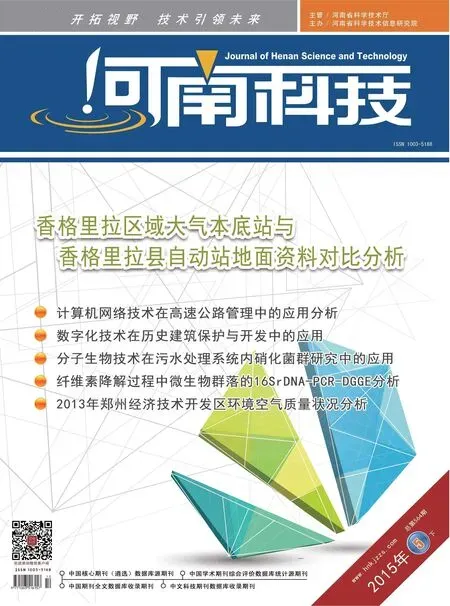空空導彈系統金屬零部件鹽霧試驗與改進措施
趙 青 吳瑞軒
(中國空空導彈研究院,河南 洛陽 47711000099)
鹽霧環境是空空導彈系統要經受的典型氣候環境,已成為空空導彈系統必然經歷的環境試驗之一,鑒于此,需對空空導彈系統的鹽霧防護設計開展研究[1]。文章介紹了常用鹽霧試驗方法及空空導彈系統的改進措施。
1 鹽霧腐蝕機理
鹽霧環境對產品的腐蝕破壞作用,主要是由于鹽霧中含有各種鹽分,氯化鈉等鹽分的富集使得鹽霧中含有大量的氯離子。氯離子很容易穿透金屬的保護膜,同時,保護膜很容易吸附有一定水合能的氯離子,使氯離子取代氧化物中氧而在吸附點上形成可溶性的氯化物,破壞了金屬的鈍性,加速了金屬的腐蝕[2]。
2 空空導彈系統的防護改進措施
2.1 設計上的改進措施
為提高空空導彈系統的耐鹽霧腐蝕的能力,可采用絕緣、密封、鍍層/增加厚度等設計。
2.1.1 絕緣
加施惰性材料制成墊層、套管、膠囊或涂料,插入或涂覆于接觸面,使陰極和陽極之間的電子導電通路斷開。這種方法適用于沒有導電和傳熱要求的部位。
2.1.2 密封
選用含有緩蝕劑的密封材料并直接涂覆,也可做成各種形狀的密封絕緣墊片、墊圈等。
2.1.3 鍍層/增加厚度
除可以用金屬(例如墊片)進行過渡來減少電位差外,還可以用金屬鍍層或適當增加金屬厚度來提高抗腐蝕性能。例如,可以在鍍鋅件、鋁制件連接的陰極金屬(不銹鋼、銅合金、鋼鐵零件等)表面鍍鉻。
2.2 材料上的改進措施
材料的選取以滿足型號的戰術技術指標為前提,同時要考慮材料的耐腐蝕性、強度、經濟性等問題。表1列出了空空導彈系統常用材料的腐蝕速率。
除表1中提到的金屬外,鈦是非常活潑金屬,由于其表面容易生成一層牢固附著的致密的氧化物保護膜,因此鈦合金具有優良耐蝕性。

表1 常用材料腐蝕結果
所以,選擇零件材料時,多選用鉻含量較高的不銹鋼、鋁合金、鈦合金等材料來代替其他金屬材料,以提高導彈的抗腐蝕性能。
2.3 涂覆上的改進措施
金屬表面進行陽極化、化學氧化、鈍化、磷化、涂漆等處理,可以有效地防止鹽霧腐蝕。大提高了腐蝕速率,縮短了得出結果的時間。
鹽霧試驗中將試驗樣件放置于鹽霧箱中,通過持續噴霧,鹽液膜不斷沉降在試樣表面上,從而鹽溶液中含氧量始終保持在接近飽和狀態。經一定時間后觀察試驗樣件的銹蝕、蔓延和起泡程度。
空空導彈系統依據GJB150.11-1986或者GJB150.11A-2009開展鹽霧試驗,具體試驗方法見表2、表3。

表2 GJB150.11-1986鹽霧試驗條件

表3 GJB150.11A-2009鹽霧試驗條件
鋼材在前處理工序中磷化,能使金屬表面形成一層具有腐蝕性的薄膜,會增加其耐蝕性,提高耐蝕強度。
不同金屬制件涂底漆后進行組裝,即可使雙金屬間絕緣,又極大地減少電極面積。在只有一種金屬允許涂漆的情況下,通常在陽極金屬上涂漆。在兩種金屬都不允許涂漆的情況下,如有可能應在接觸邊線附近涂漆,使溶液支路電阻增加,漆層的寬度不應小于10mm。由于電偶腐蝕過程中會產生堿性物質,對漆層有破壞作用,因此防電偶腐蝕用的漆層應是耐堿的。
2.4 提高層間附著力的改進措施
對于多層涂膜組成,漆膜層間附著力的大小對劃痕處是否起泡也很重要。因此,應提高漆膜層間附著力,例如在施涂前,將底材表面的銹蝕、污物充分打磨并擦凈,然后施涂;若欲再施涂,須將上道涂層適度打磨,增加表面粗糙度,就可以增加層間附著力,阻止劃痕處起泡。
3 鹽霧試驗方法
鹽霧試驗是一種通過創造人工模擬鹽霧環境條件來考核產品或金屬材料耐腐蝕性能的環境試驗。與天然環境相比,氯化物的鹽濃度是天然環境的幾倍或幾十倍,大
4 示例
某型空空導彈在做鹽霧試驗時,出現多處螺釘銹蝕,分析原因為表面光潔度低、鍍層薄、噴漆層破壞。
經過第2章節分析,采取改進措施為將上道涂層適度打磨,提高表面光潔度;增加鍍層厚度;重新噴涂底漆。進行驗證試驗,銹蝕問題得到有效解決,改進措施有效。
5 結論
鹽霧試驗是考核空空導彈系統抗鹽霧腐蝕能力的重要手段,是一種重要的實驗室加速腐蝕環境試驗,只有通過科學的試驗和先進的腐蝕防護方法,才能更好地為裝備選材、結構設計、工藝選擇、產品運輸存貯及使用和維護提供有效的數據,提高空空導彈系統的抗腐蝕能力。
[1]師昌緒.材料科學與工程手冊:上券[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110-115.
[2]高瑾,米琪.防腐蝕涂料與涂裝[M].北京:中國石化出版社,2007:8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