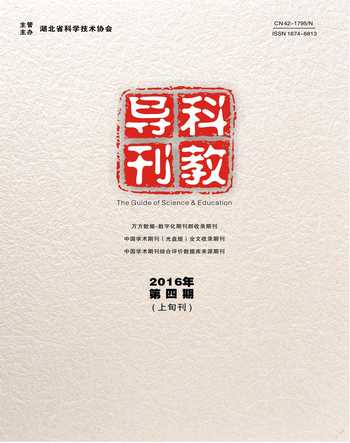優秀班集體的要素探析
丁倩影
摘 要 班集體作為學生學習的基本單位,它對學生的發展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在優秀班集體中有助于培養他們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紀律、有文化的四有新人,適應新社會對人才的發展要求。另外,作為學校的基本組織單位,班級對學校的辦學質量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建設優秀班集體具有很強的必要性。下面本文就優秀班集體的形成要素如班風、班級文化、辦干部隊伍、評價機制等作簡要探析。
關鍵詞 班級 優秀班集體 形成要素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6.04.077
Abstract Class as the basic unit for students to learn, it i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have a subtle role, in the best class help to train them to become ideals, morality, discipline, culture of Four Haves,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 of tal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ociety. In addition, as the basic organizational unit of the school, the clas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school running.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utstanding class is very necessary. Below this is the outstanding class formed elements such as class atmosphere, class culture, do the contingent of cadres, evaluation mechanism makes a brief analysis.
Key words class; excellent class; elements
1 班級
夸美紐斯曾在“班級授課制”理念中提出“班級”一詞。該理念主張把學生按年齡和學生的學習程度分成班級,并作為教學組織單元,每個班級有一個教師對全班學生進行集體教育,代替傳統的個別施教。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筆者給“班級”下這樣的定義:班級指在學校的學習教育中,按照學生的年齡和身心發展特點,學校把一定的人員組織在一起的單位,在這樣的單位中有共同的學習目標、各個成員身心狀態穩定發展、建立了健全的組織機構,各個成員基本能遵循內部規章制度。
2 班集體
馬卡連柯提出,集體是一個有目的集體,該集體是一個有組織的集體,各成員遵循集體規章制度。集體內部設有相關的組織機構,這種組織機構和成員之間是責任相關的關系。
由此可見,班級與班集體是兩個不同范疇的概念。“班級”更傾向于是一個組織的名稱,而班集體是一種價值判斷,是一種關系的促成。班集體有其自身的特征,如統一的目標,明確的行為規范、規章制度和組織關系等。班集體是一個 “生命力”的集體。
綜上所述,“班集體”由班主任、科任教師和學生組成,有統一的學習目標,和諧的人際關系,明確的班級規范制度,積極向上的班級輿論和強大凝聚力及共同的教育形式的集合。
3 構建優秀班集體的價值
3.1 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21世紀,經濟、文化、科技快速發展,當今的孩子生活在網絡時代,經受著多種文化和觀念的沖擊,接觸新事物快,信息面廣,思維敏捷,但由于學生身心發展尚未成熟,極易出現對前途的困惑和迷茫的現象,在這樣復雜的環境和自身的某些原因,在他們身上就容易出現不和諧問題。近年來,校園暴力、自殺等惡性事件頻發,這些不和諧的現象讓學生、家長以及教育工作者擔憂,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學校是學生學習的主要陣地,班級又是學生順利學習的保障,因此,在這樣復雜的社會背景下,通過建設優秀的班級體來培養學生勢在必行。
優秀班集體重視學生個體生命教育,給每一名學生提供成功的機會,平等看待每一名學生,并且讓學生在通往成功的過程中體驗成長的快樂,保證學生快樂成長,尤其是小學生。優秀班集體建設了一個幫助學生成長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重視培養學生的主動探索能力,讓學生在探索中認知自我,提升自我。這樣的班集體正是和諧社會所需要的,以人為本的班集體有助于培養學生健康的價值觀、人生觀,幫助學生能夠順利應對社會中的復雜問題,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3.2 學校的需要
班級是學校的基層教育組織單位,班級管理的好壞對學校教育的各方面都有影響。優秀班集體擁有統一科學的班級目標,強力而有效的班級凝聚力,積極向上的班級文化和團結友善的同學關系,這些因素都有助于學生學業成績的提高和各方面能力的發展,同時這些也正是學校辦學所需和目的。
3.3 新課程改革的需要
在新課程的改革中,德育已被提到了重要的戰略地位。學校的德育課程對學生的品行影響效果較弱,主要的影響還是在班級的日常活動中進行,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學生的品行,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和行為習慣等。新課程改革強調的“發展”是主動的、開放式發展,課程內容要與學生生活、社會科技發展的緊密結合,轉變學生的學習方式,通過提供品德形成、認知發展、體育與健身等經歷,學生在各種各樣的“經歷”中得到“體驗式”的發展。這是一種建立在學生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基礎之上的開放式體驗。
教育的意義是服務學生個體的終身發展。優秀班集體除了給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快速高效地獲取知識外,優秀班集體更是教會學生如何做人;學生在優秀班集體中能夠逐漸養成良好的學習方法和學習習慣,為終身學習打下基礎,這是對新課程改革中“發展”的充分體現。從可持續發展的觀點出發的優秀班集體,學生更容易在這樣的集體中把學習與生活融為一體,讓學習變為一種“生活習慣”。
班集體不但是學生學習的場所,也是學校教育的基本組織單位。班集體作為學生成長的場所,同時,班級的團體生活對學生的身心和其社會化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如何進行班級管理和建設,應該在新課程改革中得到重視和體現。
4 優秀班級形成的要素
4.1 良好的班級文化
4.1.1 班級文化對優秀班集體建設的作用
積極向上的班級文化,豐富了學生的學習生活,陶冶了情感,提升學生素質,挖掘學生潛能,增強集體榮譽感,為建設和發展優秀班集體奠定基礎。
(1)教育作用。班級文化是一種具有感染力和滲透力隱形的環境教育。學生在良好的班風、學風等班級文化的影響下行為、思想等都等得到較好的發展。硬件方面,通過布置班級環境、宿舍環境等方式,陶冶情操,塑造學生健全的人格。
(2)凝聚作用。積極向上的班級文化具有很強的凝聚力。班級成員在班主任的帶領下能夠逐漸形成有自己班級特色的文化,如學生共同追求的價值取向、學習習性等,逐漸產生班級向心力和凝聚力。能夠輻射傳播的班級文化也能對學校文化產生一定的影響,為班級創造了良好外部形象,反過來又會增強班級學生的自豪感與責任心,進一步增強了學生的內驅力。
(3)激勵作用。班級文化打開了班級成員的視野,給他們提供了享受和創造的空間和靈感,所提供文化內容和一些文化活動設施等,能夠有效地調動班級成員的積極性、創造性。積極向上的班級文化讓學生擁有強烈的使命感,成為班級成員自我激勵的源泉。
4.2 高素質的班干部隊伍
由于我國人口特點,我國采用的教學形式一般都是班級授課制,班主任一人在管理班級,當班主任面臨班額較大的問題時,為了管理好班集體,班主任只有通過選拔優秀的班干部,幫助自己建設優秀的班集體,培養班干部成為班主任的得力助手,成為班主任工作的支柱。種種跡象表明,在班主任管理班級過程中,只有依賴班干部隊伍,才能保證整個班級的工作順利進行,嚴明的班級紀律,端正的班風。
4.3 班級目標
筆者認為,優秀的班集體應該是一個具有共同的科學合理的班級目標的集體。首先這里的班級目標要具有層次性,便于學生的理解和接受,并且便于學生執行;其次,班級目標要保證適度性,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同時班級目標具有激勵性,在班級學生成員實現班級目標的過程中,不斷激發學生的情趣和增強他們的進取精神,從而提高班集體的發展水平,向優秀班集體更進一步。另外班級目標的制定還要做到民主性,保證學生參與到班級目標制定的過程中,在制定班級目標的過程中能夠讓學生認識到班集體建設和自己息息相關,把自己的發展和班集體的發展結合起來,促進優秀班集體的建設。
4.4 評價機制
學生評價,簡而言之,就是教師對學生的評價和學生的互評和自評。教師對學生的評價是教師根據課程教學目標對學生個體學習進行判斷,并把判斷結果作為改進教學的依據。學生評價不僅是對學生學習結果的評價,還包括對學生學習技能的掌握情況,價值觀等的評價。學生評價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主體性原則。羅杰斯說過,當學生在學習中更看重自我評價和自我評判,而把別人對自己的評價放在次要地位時,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及各方面的能力就會得到發展和進步。因此,學生評價中堅持學生的主體性原則,多讓學生自己評判學習的好壞,進步的快慢等,逐漸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判斷標準,更為準確的把握自己的學習,提高教學評價工作的效率。
發展性原則。發展性評價強調學生評價不單單要評價學生學習成績和學習效果,還應該在評價中涉及學生各方面能力的發展狀況。學生評價中,遵循發展性原則,能夠對學生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和了解,也讓學生對自己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簡言之,發展性原則考慮到學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兼顧到學生全方位的評價。
多元性原則。每一個個體都擁有多種智能,由于智能的組合方式不同,造成每個學生具有不同的智能特點。因此,學生評價要考慮學生的智能特點,根據學生的身心特點,制定多層次的,適合學生的評價標準,全方位評價學生。
參考文獻
[1] 騰大春.外國教育史(第一卷)[M].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
[2] 鐘啟泉.班級管理論[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 林冬桂.班級教育管理學[M].廣州:廣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 高正華.和諧:教育的追求與理想[M].吉林大學出版社,2007.
[5] 祖平.淺談如何建設優秀班集體[J].思想政治教學,2010(7).
[6] 蔡傳巧.班主任道德人格與班級文化關系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07.
[7] 宋清華.良好班集體建設之我見[J].曲靖師范學院學報,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