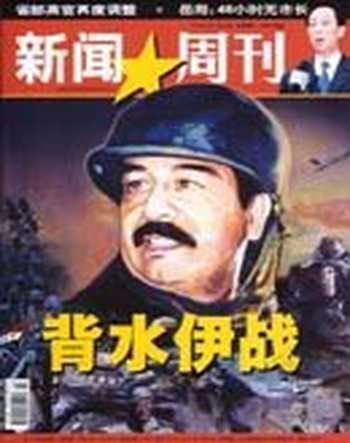中國戲劇的草莽生態
朱沿華

《沃依采克》是一部純學生制作的小劇場話劇。
在體制外游移的小劇場迎來了它的20周歲,每個參與其中者最終目的還是要進入真正的主流舞臺。
中國人歷來對權威是迷信的,對藝術是崇拜的,兩者的結合使人們長久固執地認定藝術實踐只屬于專業藝術院團的職業演員,非專業院團的非專業演員的藝術探索只能是群眾文化活動,那叫自娛自樂。但時下相當流行的小劇場正在模糊著國人的這一傳統認識。就如DV的普及使電影生產變得不再是社會極少數人士的專利,小劇場的發展使三教九流在話劇舞臺上都擁有了自己的藝術履歷。
從絕對信號到絕對沒有信號
2002年的最后一天,北京人在集體懷舊。羅大佑的“圍爐”音樂會讓人們在歌曲中回首光陰的故事,而另一群人則以戲劇的名義匯集到一個叫做北劇場的地方。在那里,人們為一個叫林兆華的人、一部叫《絕對信號》的戲點燃了20支蠟燭。這20支蠟燭同時也為中國小劇場話劇而燃燒,因為《絕對信號》就是其開山之作。
1982年的夏天,尚屬話劇導演界小字輩的林兆華有感于中國戲劇舞臺“斯坦尼”一統天下的極度貧乏,帶著北京人藝的一群年輕人排出了《絕對信號》。該劇在中國戲劇舞臺上首次外化了人物的內心活動,首次打破了戲劇順時間發展的時空連貫性,首次讓演員走到觀眾中間去表演,立時引起了極大轟動,連續演出100場并引發了一場戲劇到底應該怎么演的大討論。
如今的戲迷親歷過當年盛況的已不多了。對于年輕的戲人和戲蟲來說,《絕對信號》只是傳說中的英雄。在這個寒冷的冬天,人們向往已久的英雄終于重現江湖 《絕對信號》熱氣騰騰地重新上演了。只是,這是一次顛覆性的演出。
一名北京貨運服務部的老職工、一名自由職業者和五名大學生是這次舞臺上的主角。他們以“向當年的藝術家們致敬,同時向目前的戲劇現狀挑戰”為口號對原作進行了大膽的解構。演出過程中,創作者以投影和戲中戲的形式將演出策劃、排練時的情形進行了逼真的呈現,并對夸夸其談、實則對戲劇一竅不通且“心黑手辣”的“制作方代表”進行了無情的諷刺。
演出結束后,同樣以學生為主的觀眾紛紛向創作者質疑:原來的《絕對信號》到底是個什么樣子?為什么要把你們的個人情緒放大到舞臺上來呈現,這些與觀眾何干?
令人意外的是,《絕對信號》的原創者,北京人藝的老導演林兆華站了出來,表示了對這個新版本的最堅定的支持:《絕對信號》不是莎士比亞,不是《哈姆雷特》。中國藝術只有一個主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太單調,太貧乏了。這個戲的歷史功績不在戲劇本身,而是對當前戲劇環境的批判,未來戲劇的希望不在國家體制的劇院,而是在體制以外,國家劇院的體制已經腐朽了。
林兆華回憶說:“當年連演100場的《絕對信號》,排練時卻極其艱苦。我和演員林連昆、譚宗堯在人藝一樓小排練廳‘內部演出,連景都沒有,就拿幾個燈箱子當車底,釘個梯子,一小桌,三把椅子,中間一個工具箱,差一個追光,我就拿了一個五節電池的手電筒自己打。黨委和藝術委員會審查那天,開始八九分鐘沒有一個人說話。”后來在一個老藝術家的支持下才終于通過審查。
讓民間戲劇自由生長
在重排的《絕對信號》中,年輕的導演,來自北大的邵柏和來自中戲的邵澤輝設置了一個人物——制作方代表,在演出的間隙,這個人竄上竄下,像小丑一樣盡情侮辱著戲劇。
這些年輕人的怒氣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前一天,投資方在戲演完后搞了一個針對去年話劇市場的頒獎晚會,評出的獎五花八門,有“最有夫妻相的演員”,有“最忽悠的媒體記者”,獲獎者基本上都和這個投資方有關。這些年輕人認為,戲劇在這里被褻瀆了,他們在第二天的演出中,把這些都編進了戲里。
作過十年制作人的袁鴻卻持有不同看法,他覺得自己碰了十年壁,得出的經驗就是:珍惜眼前。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樂評人李皖說,這么早就開始回憶了。我們的年輕人總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你到底經歷了多少苦難?只是一味抱怨,卻沒有人肯彎腰下去撿起劇場里的垃圾。
袁鴻甚至認為現在的戲劇環境不錯,錯的是戲劇學院的學生不好好上學,他們的大多數深夜可能是在KTV、酒吧度過的,而不是討論劇本。
戲劇CEO
“小劇場并不代表民間勢力。”在劇中客串的老象說。老象自稱是“無業游民”,從日本回來后,他一猛子扎進了劇場,從觀眾到與著名的導演、演員打成一片,他已經成為北京人嘴里的“戲蟲”。他有一個戲劇網站,雖然只有他一個人,也是非贏利的,但他也算得上是“戲劇CEO”。像老象這樣癡迷于戲劇的“草莽”人物還有很多。新華社的李晏,20年前只有19歲,他見證了中國小劇場20年的風風雨雨,從沒有落下過一部戲,并為每部戲都拍下了劇照。他感嘆說:“要是早一點認識孟京輝他們就好了,哪怕給劇組買買盒飯呢,我也心甘情愿。”
去年的小劇場,幾乎被體制外的“民間力量”占據。《丑兒的春夏秋冬》導演是雜志記者,《天上人間》導演是中央電視臺的編導。按李晏的說法,民間戲劇的代表人物之一張廣天也是非專業出身,這些人沒有經過戲劇訓練,但現在他們中的一些人,像孟京輝,卻已經進入象征主流的大劇場,而在從前,大劇場的舞臺只能被北京人藝這樣國家體制內的劇院專有。而現在,那些戲劇門外的人,如老象、李晏他們,都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從“草莽”進入“殿堂”的希望。
在袁鴻看來,小劇場無論是從藝術上還是市場上,真正意義上的起步還是這兩三年。北京的小劇場越來越多,今年馬上還會增加兩三個。劇場多了,對戲的需要多了,各種體制的經營者、制作者、參與人,各樣的公司、民間院團多起來,再經過一番像大劇場那樣的藝術比較、市場競爭,才會出現一個真正的高潮。袁鴻在上海劇院看到像空姐一樣服務周到的領位員。他希望北京劇院的商業運作也能這樣全面、專業。
在袁鴻他們看來,小劇場20年的最大功績在于培養了人們對戲劇的持久熱愛,大大拓寬了戲劇觀眾的范圍和參與戲劇創作者的范圍,改變了相當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它為中國的戲劇藝術培養了一批的編劇、導演、演員、制作人,如孟京輝、張廣天、張揚、胡軍、吳越、郭冬臨、廖凡、郭濤等活躍于當今戲劇、影視界的導演、演員都曾是90年代小劇場戲劇的積極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