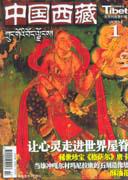藏東第一民居
張建世

1997年我到昌都左貢縣時,第一次聽人說起東壩鄉。那是一個遠在怒江邊的地方,非常偏僻,但老百姓卻十分富裕。盛產核桃、葡萄、梨等水果,聽起來就象世外桃源一樣,令人神往。
2002年6月我參加了茶馬古道考察團到昌都后,就留在了昌都,繼續做福特基金的一個社會調查的課題, 這使我有機會專程去一趟東壩鄉。
6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圖嘎一道再次來到了左貢,當晚住宿在縣政府招待所。第二天吃過早飯后,驅車直奔東壩。汽車離開縣城,沿玉曲河谷而上。河谷開闊,兩岸的青稞地和草山一片碧綠,山上不時還可見片片樹林。大約兩個小時后,拐向了通往東壩的鄉村公路。開始植被還好,當翻過山口后,汽車蜿蜒而下,植被也越來越差,最后是一座座光禿禿的、幾乎寸草不生的大山。同行的東壩鄉書記告訴我,已經來到了怒江河谷,離東壩不遠了。
原來,怒江河谷屬干熱性氣候,降水十分稀少,植物難以生長,到處都是這種光頭山。他們從鄉上到最遠的村莊要翻幾座大山,走一天路,山上即無水又無樹木,夏天被太陽曬得連遮陰的地方都找不到。以前這里不通公路,1991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才修通了這條鄉村路。但是這里的汽車很少,絕大多數農民外出仍是騎馬或步行。現在鄉上不通電話,當然手機也是打不通的。
談話間,汽車拐過一道山灣。突然,眼前一亮,只見在群山環抱間有一片綠色臺地,奔騰的怒江乖乖的在邊上流淌。這就是東壩鄉政府所在地軍擁村。村內樹木繁茂,郁郁蔥蔥,與周圍的光頭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遠遠望去,一座座藏式建筑掩映在綠樹叢中,十分美麗。進得村來,只見溪水涓涓,農田片片,有幾個男人在閑聊,田間除草的幾個婦女也不慌不忙,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
東壩鄉書記把我們安排在白瑪拉措家居住。走進白瑪拉措家里,來到二樓客廳的時候,不禁大吃一驚。客廳高大寬敞,雕梁畫棟,完全出乎我的想像。門窗墻柱上雕刻、彩繪了花草等各種紋飾。雕工精細,色彩鮮艷,富麗堂皇。同行的昌都地方志總編圖嘎也贊不絕口。開玩笑說:“我到過西藏很多地方,也沒見過這么好的農民住房,簡直象宮殿一樣,可以稱之為西藏第一民居。”雖然是玩笑,但作為昌都本地人的圖嘎在昌都還沒看見比這更好的農民住房卻一點不假,將其稱為“藏東第一民居”應該當之無愧。
在白瑪拉措家居住的日子里,不禁對其住房產生了興趣。曾用腳步丈量住房的面積,但還是不過癮。最后向女主人借來了皮尺,與圖嘎一起丈量。白馬拉措家的房屋以一棟長方形、高大的三層樓房為主體建筑。每層高約四五米,長約30米,寬約25米,每層面積約700平方米。底層堆雜物,農具等。二層正中為長方形天井,天井四周為走廊,走廊四周有九間大小不等的房屋。其中客廳約80平方米,廚房約50平方米,是日常活動最多的地方。除外還有經堂、臥室、倉庫等七間房屋。三層的前半部分是平臺(二樓的房頂),后部已有柱子和房頂,準備修建房屋,但離完工尚遠。主體建筑外有院墻,墻內有院壩、馬廄、堆莊稼的小房,與其它人家不同的是還有村內唯一的一個小商店。總的占地面積大大超過了1000平方米。
這種住房在城里人看起來,也許算不了什么。但這是在如此偏僻的山村的農民住房,而且全村的住房都好,形成了一種風格。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當我們對東壩有了更深的了解后,就不由自主地發出由衷的贊嘆了。這里是一個偏僻的地方,幾乎與世隔絕。要翻幾座大山,走幾十里路,才能到最近的左貢縣其它鄉的村莊,到縣城或昌都就更遠了。而且上帝并沒有給予特別的關照。雖然村內自然條件不錯,但很早以來土地就十分有限,現在只有人均0.7畝,僅夠基本生存。周圍的大山卻是那么貧瘠,沒有樹木,連草都非常稀少。不可能像其它山里人那樣靠山吃山,連修房子所用的木材都要到遠地購買。然而,這里卻有著如此高大的房屋。

也許它與當地闖蕩社會的傳統有關。當地習慣,男人如果不是因缺勞動力必須留在家里的話,不出去闖蕩會被人認為無能。所以村里有相當數量的男人在外經商、打工、跑運輸、做手藝掙錢。正是這些外出人員掙回的錢,購買了價值不菲的木材等建筑材料,修建了如此高大的房屋。人們也深知在外闖蕩社會需要本領,所以特別重視教育,都主動送孩子上學。還有不少人家出高價將孩子送到左貢、昌都、拉薩讀小學、讀中學。考到天津、南昌的西藏中學的學生也不是一兩個。白馬拉措有7個兒女,2個在拉薩讀中學、1個在天津讀西藏中學,4個在昌都讀小學,足見對子女教育的重視。這種情況在城市、在郊區農村毫不奇怪,但在邊遠的民族地區確實罕見。須知,這是需要大筆經費的啊!
這是一個具有活力的村莊。人們都努力向外發展,努力掙錢。盡管如此,修建如此高大、富麗的房子也不是容易的事。村內房屋的修建并非一次完工。家庭富裕的人家要先準備兩三年,有的準備三五年七八年,甚至十多年。主要是準備木材等原料。建房一般是一年,也有的兩年完成。建房時筑墻等簡單的活主要是村里人互相幫忙,木工、畫工,特別是雕刻等精細的、技術要求高的木工和彩繪等畫工,須支付工錢。建房一般只完成最基本的部分,如墻、房頂、柱子、門窗、地板及有關部分的雕刻等不完成以后就很難再做的部分。其余的內裝修,有的經濟實力不足的人家甚至還有部分的隔墻,都留下了。住進新房后,根據經濟條件,慢慢的裝修完善。村內有個別人家,新房已住了十多年,由于后續經濟不足,都還未裝修、彩繪。即使是村內最富裕的人家之一白馬拉措家的房屋,二樓許多柱子也沒有彩繪,三樓僅有最基本的柱子和房頂,不知道還要幾年才能完工。從材料的準備到房屋的修建和后續的內裝修,真是集中了一家人多年的人力、財力和物力。
當地的房子很大,已大大超過了居住的需要。最典型的白馬拉措家。四個丈夫,兩個長期在外經商,一個一年中有幾個月外出放牧。未婚的7個子女均在外地讀書。連老母親也到昌都照顧讀書的孫子孫女去了。平時只有白馬拉措和她的一個丈夫在家,偌大的房屋空空蕩蕩。即使全家人都回來,這么大的房屋也超過了實際需要的幾倍。實際上,村內其他許多人家房屋的面積都大大超過了實際的需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人們為什么會花這么多錢,甚至超過自己的經濟實力修建超出實際需要的房屋呢?原來,在當地人的心目中,房屋不僅是為了實用,居住舒服,還是財富的象征,體現了家庭的勢力和無形的社會地位。用當地人的話說就是“房子蓋小了沒面子”。現在有的人在外經商,走的地方多了,也覺得沒有必要蓋這么大的房子,實用性不大,但回到村里真正蓋房子時,又感到蓋小了面子上過不去,仍是蓋大房子。在這里,住房不只是滿足居住的需要,還具有文化的意義,它凝聚了人們的情感,體現了一種價值取向。
這時,我不禁想到城里的姑娘們,為了美麗、時髦,或時下流行的詞語“酷”,不惜上百,上千、甚至幾千元去購買一件時裝。如果僅僅是為了御寒、蔽體,又何須購買這么貴的衣服呢?
這就是文化,東壩的人們看重住房,城里的姑娘看重時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