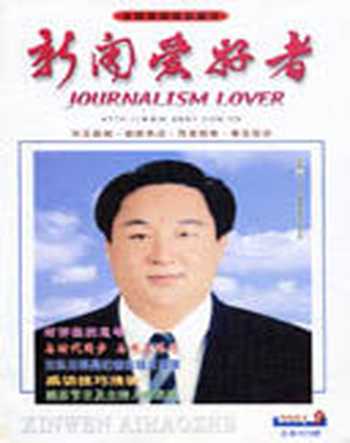建構公民的言論空間
豐 帆 董天策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后,報刊評論逐漸打破“欄”的界限,呈現出版面化的傾向。在這場被稱作“時代先聲”的“時評熱”中,時評正是以“大眾視點”、“平民寫作”來彰顯的。換言之,這一時期評論空間的拓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群言評論”(可歸為后來的“來論”)的“攻城略地”。
以《南方都市報》為例,由普通讀者撰文的欄目先后開設了十余個,其中包括“視點”、“觀點交鋒”、“議論風生”、“讀者來論”等;而從文章數量來看,每天的“來論”數量基本保持在兩篇或兩篇以上,約占“時評”版文章總量的1/3甚至1/2。經過2003年4月2日的版面調整,《南方都市報》的“來論”完全突破了“專欄”的界限,辟出“來論版”,形成獨立版面,以“視點”、“馬上評論”、“一家之言”等欄目為主打,專門刊發來論,不僅起到了豐富評論品種、壯大評論隊伍的作用,而且與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互動互進,在客觀上拓寬了公共空間,提升了讀者的主體地位。
“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又譯作“公共領域”,是哈貝馬斯構建的“政治性烏托邦”的關鍵詞。按照哈氏的定義,它是“允許市民自由發表和交流意見,以形成共識和公眾輿論的地方。它向公眾開放,所有社會成員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在這塊地方自由討論有關公共利益的任何事務。大眾傳媒是這一領域的主要論壇”。
《南方都市報》的“來論版”開辟后,該報最明顯的變化體現在言論空間的擴大:言論版由以前的一個版面擴大到兩個版,評論總量也由擴版前的4~6條增加到如今的8~10條。伴隨著量的激增而來的是微妙的質的變化。
一方面,來論版的相對獨立使得“來論”自成生態、生機盎然。《南方都市報》從2003年4月6日起即在“來論版”下方注明“本版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既表明了該版面的非官方色彩,同時又促進了話題的多樣選擇和表達的自由闡發。
另一方面,“來論版”采用的是與“社評版”對頁的形式,在視覺上不會破壞言論版面的整體感。這種版式與《紐約時報》言論版的做法頗為相似,后者強調“來論”與“社論版”評論的沖突性,在版式設計上體現了一種“平衡”理念。而《南方都市報》的言論版,就目前而言,來論與社評實現了“空間同一”,但尚未實現“共時態”生存。也就是說,在該報同一天刊發的評論中,鮮見社評版文章與“來論”圍繞同一現象或主題展開評論。在筆者看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觀點之間的沖突性。
從話語空間的角度說,來論版的開辟是公共空間的開放;而從傳播主體的角度看,辟出專門的來論版刊登作為讀者的來論,則是社會參與的強化。
20世紀60、70年代,西方傳播學界提出了社會參與理論(或稱民主參與理論),認為作為受眾的公民不僅有“知”(即知曉信息)的權利,而且有“傳”(即表達意見)的權利。《南方都市報》、《經濟觀察報》等報紙的每一篇“來論”下面均會注明作者的真實姓名,所在城市甚至個人職業。《南方都市報》2003年11月4日“來論版”刊發了6篇文章,標明來自北京、廣東、四川、河南、山東、東莞等五省市,職業身份有職員、教師、交警、記者等等。這表明,來論突破了編輯部、職業寫手、政治精英寫作的界限,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普通讀者拿起手中的筆,寫“我”所想,書“我”所感。
誠然,來論及其獨立版面的出版本身是社會民主化的體現,是讀者主體意識的體現,是公民參與傳播過程的體現。
我們有理由相信,以讀者平等參與和交流為基點、形成多元開放言論空間為目標的“來論”及其“來論版”一定會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