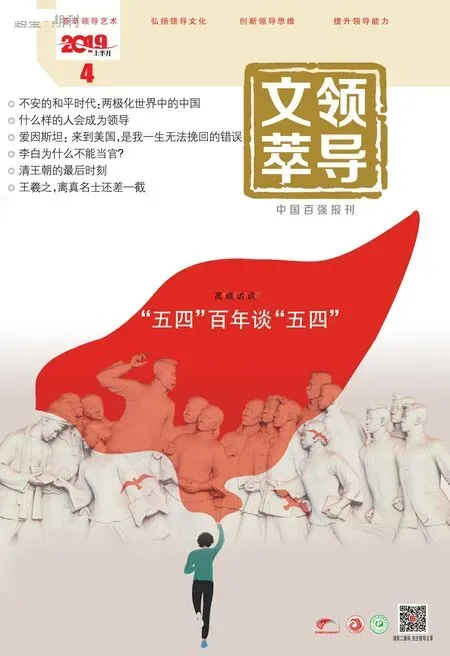行政問責制與民主問責制
喻希來
2004年4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監(jiān)察部關于中石油川東鉆探公司井噴特大事故、北京市密云縣“2·5”特大傷亡事故和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廈“2·15”特大火災事故調查情況的匯報,并對有關責任人作出處理決定。此后,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黨組書記馬富才;密云縣委副書記、縣長張文;吉林市委副書記、市長剛占標,紛紛引咎辭職。除了上述官員,還有其他官員受到連帶的追究和處分,例如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吉林被免除職務,左遷北京市副市長。由此,新聞媒體掀起一波討論和贊揚“問責制”的高潮。
為了避免混淆概念、張冠李戴,我們首先要區(qū)分行政問責制和民主問責制。前者古已有之,是按照行政管理系統(tǒng),上級追究下級官員在重大問題上的行政責任的制度。后者是現(xiàn)代民主憲政所特有的官員(包括最高層官員乃至整個政府)問責制度,它既包括行政問責制,還包括一系列其他的問責制。厲行行政問責制,是整頓吏治、刷新行政的重要舉措,值得稱贊,而實行民主問責制,才是人們久已期待的政治改革的根本性措施。在中國的帝制歷史上,行政問責制包括皇帝問責、御史問責、吏部問責等不同的渠道。從理論上說,大一統(tǒng)的帝制是極端專制獨裁的制度,皇帝擁有無所不能和為所欲為的權力;但在事實上,皇帝并不一定有興趣或有能力來行使這一權力,正如民主制度下的選民不一定會行使自己的選舉權一樣,一些老牌民主國家的投票率只有半數(shù)左右。多數(shù)皇帝是懶皇帝和笨皇帝,是被人操縱的傀儡皇帝,很少了解和追究官員的行政責任,只有象朱元璋、雍正這樣的皇帝,才會干綱獨斷,頻頻追查和懲辦有過失的大小官員。御史是直屬于皇帝的監(jiān)察官員,御史臺是與一般行政部門分立的一個獨立系統(tǒng)。在戲曲中人們常常看到御史出巡時威風八面的場面,實際上御史的品級通常低于地方大員,他們的權力來自于“通天”(其物化象征常常是所謂的“尚方寶劍”)。孫中山倡導“五權憲法”,是對古代御史制度的一種肯定和繼承。吏部是負責選任官員的部門,它對官員的問責是行政問責的主要渠道。吏部主持對官員的“大考”(對現(xiàn)任官員的定期考核,非指對準官員的考試錄用),不論是否敷衍了事,終歸要在表揚和提拔一些人的同時,批評和懲處一批不稱職的官員。
在總體性社會時期,毛澤東把第一種行政問責制發(fā)揮到了極致,他在“三反”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中,一個省一個省地分配“打老虎”指標和“大煉鋼鐵”指標,指示譚政、周恩來等每天打電話給地方上落實,搞得地方長官惶惶不可終日,擔心隨時會被問責免職。由于他倡導“書記掛帥”下的“群眾運動”,不喜歡官僚系統(tǒng),上述第二種和第三種行政問責制在他領導時期都萎縮了。然而實踐證明,沒有民主和自由,好皇帝和清官有可能比昏帝貪官帶來更大的人間災難,到“文革”結束時,人們對毛式官員問責制普遍喪失了熱情。在轉型時期,由于干部老化、最高權力不集中(總書記不兼任軍委主席、建立顧問委員會)和地方權力的擴張,對各級官員(尤其是“一把手”)的行政問責制幾乎處于癱瘓的狀態(tài)。除非是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要求地方表態(tài)與中央保持一致),除非是暴露了重大的貪污犯罪行為,省部級領導人基本上處于沒有監(jiān)督與問責的狀態(tài),處于歷史上空前的隨心所欲之境。中共十六大以來,出現(xiàn)了行政問責制全面復興的勢頭。國家領導人親自主持追究重要官員的行政責任,表現(xiàn)出對古代親民勤政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揚。不久前,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決定,對其派駐中央國家機關的紀檢組、監(jiān)察局實行統(tǒng)一管理。盡管派駐干部的工資福利還由所在部門出,但派駐干部的選拔、管理權將直接由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掌握,派駐紀檢組長人選由中央紀委商中組部提名、考察,由中央紀委呈報中央任免,使派駐紀檢組、監(jiān)察局作為“監(jiān)督者”的身份更加清晰、單純。而且,已經(jīng)開始醞釀各級地方紀檢監(jiān)察系統(tǒng)干部“垂直管理”的體制改革。這說明御史問責制的傳統(tǒng)正在卷土重來。由中組部制定并經(jīng)中央政治局批準的《中國共產(chǎn)黨黨內監(jiān)督條例熓孕校牎貳ⅰ豆開選拔黨政領導干部工作暫行規(guī)定》、《黨政機關競爭上崗工作暫行規(guī)定》、《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guī)定》、《地方黨委全委會對下一級黨政正職擬任人選和推薦人選表決辦法》等新近出臺,則是恢復吏部問責制度的嘗試。然而,要從根本上扭轉貪賄橫行、行政紊亂、干部既擅權又不作為的狀況,僅靠行政問責制是不夠的,還需要全面啟動民主問責制。民主問責制具有多方面的內容,包括選民問責、民意代表問責、司法問責、輿論問責、良心問責等,發(fā)達國家已經(jīng)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
選民問責是民主體制下對政務官員的“大考”。選民是考官,各級政務官是被考核和問責的對象,如果由被考者自己擬定標準答案,就失去了“大考”的意義。這就要求民主選舉必須是直接選舉(多級間接選舉最終產(chǎn)生的全國人大代表半數(shù)以上是官員,由他們來選舉國家領導人就成了“官選官”而不是“民選官”)、平等選舉(按照現(xiàn)行制度,城里人一票等于農民四票,軍人一票等于平民五百票)、競爭性選舉(不論民意代表還是政務官員,一律實行差額選舉,包括各級“一把手”和中央政府的成員)。民意代表在各級代議機構中問責是對政務官員的“中考”。這包括質詢、調查、不信任投票、彈劾、罷免等一系列的手段。民意代表要有時間、場合和能力來行使這些權力,必須是全職、有薪、有適當辦公條件和專業(yè)助手的政治家,而不是兼職、無薪、每年只開十來天會的行政官員和勞動模范。司法問責是對政務官和文官(公務員)的“特考”。這里主要不是指對他們個人行為的問責(包括對行政不作為的審理),而是對他們公務行為的問責。也就是說,應當賦予司法系統(tǒng)進行違憲審查的權力,并加強行政訴訟的力度。輿論問責是對各級官員的日常“小考”。現(xiàn)在,我們一方面把中小學生成天置于考試壓力下,訓練成應付考試的機器;一方面又把官員當成幼兒園里的孩子般小心呵護,堅持表揚為主、批評為輔的新聞報道準則,這完全是一種倒置。從政本來就是一種最富挑戰(zhàn)性的職業(yè),受到輿論的特別關注,在批評性報道方面不能享有與一般民眾同等的隱私權和名譽權,正是這種挑戰(zhàn)的一部分。如果忍受不了新聞媒體隔三差五地放在火上“燒烤”,就干脆不要步入政壇。既然當了官,就不能只想得到鮮花與掌聲,還要隨時準備迎面而來的臭雞蛋,稍有不慎,就會身敗名裂。
良心問責是官員們的“自考”。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準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guī)定》涉及到不同類型的辭職,如“因公辭職”、“自愿辭職”、“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等。顯然,本文開頭所述官員的“引咎辭職”,都屬于“責令辭職”,而不是“自愿辭職”。而在許多發(fā)達國家,已經(jīng)形成了政務官自愿引咎辭職的慣例或者說政治文化。一個政務官犯了錯誤,雖然還達不到罷免或彈劾的程度,但已經(jīng)給政府和執(zhí)政黨帶來了不利影響,自己主動辭職,就可以給同僚減少一些麻煩。中國官員現(xiàn)在還很少有自愿引咎辭職的現(xiàn)象,不是說他們的良心不如人,而是中國的“官本位”太厲害了,官民待遇的差別太大了,辭職的官員也比較難于找到合適的新職業(yè)。
行政問責則應進一步走上法制化的軌道。重慶市政府常務會議最近審議通過了《重慶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從7月1日起施行,可視為在這方面的一種初步嘗試。該辦法規(guī)定,市政府所屬各部門行政首長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涉及18種情形者將被追究責任,問責對象直指市政府所屬各部門“一把手”及主持工作的副職官員。今后將被追究責任的18種情形包括∶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出現(xiàn)了因效能低下,無正當理由未完成工作任務,執(zhí)行不力致使政令不暢或影響市政府整體工作部署的;責任意識淡薄,在重大災害時刻拖延懈怠、瞞報、虛報、遲報數(shù)據(jù),致使公共利益或管理相對人合法權益遭受損失或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的;盲目決策,造成嚴重不良政治影響或重大經(jīng)濟損失的;不依法行政或治政不嚴、監(jiān)督不力造成嚴重不良政治影響或其他嚴重后果的;在商務活動中損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經(jīng)濟損失的;等等。市長根據(jù)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向市政府提出的附有相關證據(jù)材料的舉報、控告,新聞媒體曝光材料,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的問責建議和工作考核結果等情況決定啟動問責程序。啟動問責程序后,市長或市長委托的副市長將責成市政府有關部門的行政首長當面匯報情況,對確有被問責情形的,市長可直接決定將情況提交市政府常務會議討論,研究追究責任的方式。需進一步核實的,可責成監(jiān)察局調查核實。追究責任的具體方式有7種∶取消當年評優(yōu)、評先資格;誡勉;通報批評;責令在市政府常務會議上作出書面檢查;通過市級主要新聞媒體向社會公開道歉;停職反省;勸其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