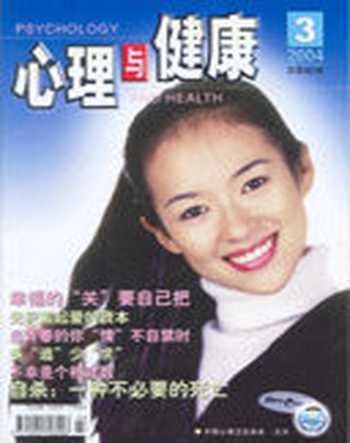把尊嚴還給弱者
吳凌云
記得有這樣一幕:在眾目睽睽之下,記者將話筒對準上臺接受捐助的特困生。當觀眾都期待著她講幾句話時,這個女生竟掩面而泣,頭也不回地跑下臺去,有人跟在她后面喊“拿著毛衣毛褲……”此景頗讓人費解。直到有一天,我從網上看到這樣一則消息:
一場罕見的暴風雪襲擊了紐約州,紐約州立小學仍堅持上課。當人們指責學校讓小學生受苦時,校方回答:“紐約不僅有富翁,也有赤貧家庭。后者既開不起暖氣,也供不起午餐,他們的孩子全靠學校的免費午餐。若是學校停課,窮人的孩子就得在家里受凍挨餓。”有人提出,可以讓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待在家里,只讓那些窮孩子去享受學校里的暖氣和午餐好了。校方的回答是:“我們不能讓那些窮苦的孩子感覺到他們在受救濟,因為救濟的最高準則就是要保護受施者的尊嚴。”
讀到這里,我的心被深深地觸動了:校方之所以要求學生一律到校上課,是為了讓那些窮孩子在享受溫飽的同時,也享有一份平等和自尊。他們不愿讓孩子們感到自己是在被憐憫,不愿在孩子們的心中種下卑微的種子,這是何等的仁慈啊!當我回過頭再次感受那一幕時,我仿佛聽到了尊嚴在女孩心中的吶喊,難道幫助別人就有權公然無視受助者的自尊?
二戰期間,一位德國老人講過這樣的故事:他家在農村,人煙稀少。一天,一個身穿風衣、頭戴禮帽、手提皮箱的男人在他家的院子柵欄外徘徊。他觀察良久,然后上前對那人說:“先生,你是否愿意幫我把柵欄里的這堆木頭扛到那邊去,我老了,扛不動了。”男人眼睛一亮,連聲答應,脫去風衣禮帽,很賣力地把木頭扛過去并擺放得整整齊齊。晚上,滿頭大汗的客人心情愉快地與主人共進晚餐。二戰期間,城里逃難的人很多,老人家的木頭被搬來搬去。每搬一次木頭,就會有一個客人與他共進晚餐,并一起住上一夜。——其實,那堆木頭根本不需要搬動。
我的心又震顫了:這位老人在有能力幫助他人時,卻小心地把自身的優越遮掩起來,給受助者創造一次良機,從而使受助者在付出的同時也能坦然地接受別人的幫助,不愿讓他因無故接受施舍而失去人格之尊。
我想起了一位殘疾青年的故事:他住在一個偏僻的小鎮,以擺書攤為生。有一個小學生,每天放學經過書攤,都要裝作選書的樣子,像賊一樣偷看幾則小故事,然后溜之大吉。直到有一天,一位中年人從后面揪住了這孩子的衣領,不由分說抽了他兩巴掌。“別打孩子,愛看書是好事。”年輕人竭力阻止。“我不是不讓他看書,我只是不愿讓他白看人家的書。”中年人把孩子拽到一邊,說:“你可以拔草賣錢,再買書。”當這個孩子背著草四處尋找買主時,年輕人叫住了他:“賣給我吧,我家有頭耕牛。”從此,這孩子終于能泰然地坐下來,從容地閱讀他喜歡的書了。讓孩子擁有尊嚴,不用感激,這是何等的崇高啊!如果助人只是為了顯示自身的優越,讓受助者感恩于己,那么,這種一相情愿的“助人”,對受助者而言,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在這個貧富分化日趨明顯的年代,某些人習慣于用金錢作標尺來確定、重組人與人的關系,尊嚴的貧血就會成為一種流行病。因此,當我們助人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維護弱者的尊嚴,特別是對需要幫助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