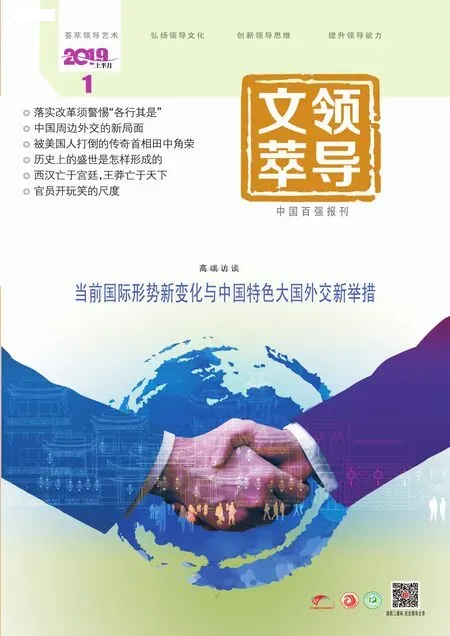閱讀2:與時俱進是政黨生存的基礎
宋少鵬
當代政治是政黨政治。
政黨作為代議制運作的客觀需要出現于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政治中。1800年美國的杰斐遜以共和黨侯選人的身份當選為美國第三屆總統,也算是人類政治史上政黨政治的開端。盡管17世紀英國的議會中已經出現了政黨政治的雛形,圍繞著詹姆斯的王位繼承問題,議會內出現了保王派和國王反對派,后演化成托利黨和輝格黨。但從嚴格意義上而講,托利黨和輝格黨只是議會內部的不同政治派別。群眾性政黨的出現卻是伴隨普選權的擴大因組織選舉的需要而出現的。但政黨產生之初因其明顯的黨派偏私的特點被近代民主制度的締造者們所忌諱、厭惡甚至壓制,而被排斥在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憲政結構的框架之外。華盛頓在他著名的告別演說中,以“最鄭重的態度”警告國民注意“黨派精神的有害影響”。
盡管,政黨和政黨政治作為一種政治慣例被各國的政治實踐所接受,但政黨的法律地位卻只是作為公民結社權的個人自由權的體現和擴展。直到二戰之后,西方各國才從法律上確認政黨作為民意表達和政治參與的基本工具的職能,聯邦德國出現了第一部《政黨法》,西方各國紛紛在憲法性文件中承認政黨在憲政體制中的法律地位。二戰之后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政黨政治作為現代政治的某種標志,成為衡量傳統部族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個指標。是否存在競爭性政黨政治成了西方國家衡量民主化國家民主程度的標尺。雖然,以西方為標準的發展觀和現代化理論遭到了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理論和政治上的批評,但現代政治是政黨政治卻是不爭的事實。
政黨作為代議制民主的工具上升為民主制度本身,或是抽象為社會發展必由之路中的必然,是對政黨和政黨功能的一種政治神化。一個具體的政黨的生存和消亡并不是一個社會政治系統的崩潰,只是表明這個社會的政治系統一度出現了問題,甚至是危機。如同一個人的死亡不能代表人類的滅亡。反之,一個人要健康長存必須了解健康的原理,適應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政黨亦如此。只有適應社會大系統,能圓滿完成自己功能的政黨才能在政治體系中立足、生存和發展。所以,理解了政黨在代議民主制中的工具身份和代表角色,才能理解與時俱進作為政黨生存基礎的重要性。
換言之,政黨作為一種代議工具,它架起了了社會系統與政治系統的橋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黨是集合民意、表達民意的工具。也正因它是民意集合和民意表達的工具,伴隨所代表民意的變化,作為民意集合的政綱應隨著民意的變遷而變遷,而不能固守有所謂的執政傳統,固步自封,作繭自縛。最終的結果只能是被拋出政治舞臺成為歷史陳列室的教材。
綜觀當今各國,傳統大黨都面臨著各種挑戰,新生黨派影響日增,從壟斷政壇多年的傳統大黨的分裂或下野,到歐洲極右翼政黨進入聯合政府,各國頻頻上演因政黨格局的變化而引發的政治地震,而全球范圍內這種政治地震此消彼長,余波綿綿,延續至今。面臨挑戰,適時作出調整的政黨保持自己在政治舞臺上的影響力,反之,不得不謝幕,退出了歷史舞臺。
1993年8月日本政壇出現自二戰后38年第一次出現聯合政府,結束自民黨一黨執政的歷史。1994年意大利的第一大黨天民黨失去傳統優勢,淪為小黨。二戰后到1994年,意大利天民黨始終保持其在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曾組織過15屆一黨政府。雖然多數情況下都是天民黨為首聯合社會黨、社民黨、共和黨、自由黨聯合的所謂“中左五黨政府”的形式。90年代初意大利開始的反對貪污腐敗的“凈手運動”沖垮了天民黨、社會黨等傳統大黨,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
無獨有偶,就算傳統政黨格局未被打破的英美國家里,傳統大黨也遭遇到前所未所的挑戰。1992年,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億萬富翁以獨立侯選人的身份獲得了18.9%的普選票,取得了自1912年以來,美國兩大黨以外的總統候選人所取得了最好成績。盡管,障于美國“勝者全得”的選舉制度,作為第三黨的侯選人幾乎不可能奪得總統寶座,亦很難瓜分議席。當年入主白宮的克林頓也只獲得了43%的普選票。美國選民對佩羅的支持映像出選民對傳統兩大黨的不滿和傳統兩黨所面臨的挑戰。當然,1992年參加競選的克林頓早已意識到傳統政黨面臨的挑戰,打出“新”字招牌,以示與傳統舊黨的區別,從而作出回應。
克林頓是以“新民主黨人”的形象出現在選民面前的,“尋找一種介于自由放任主義和福利國家之間的中間道路”(克林頓語)。大西洋彼岸英國布萊爾打著“新工黨、新英國”的旗幟,以“改革的化身”入主唐寧街十號。當然,這篇文章我不想討論第三條道路的實質及其實際政策效果,也不討論“第三條道路”與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關系。我們雖不能簡單地論斷,第三條道路是對選民意愿的直接體現,有其出現的必然性。但以美國民主黨的克林頓、英國工黨的布萊爾、法國社會黨的若斯潘、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施羅德、左翼民主黨(前身是意大利共產黨)的達萊馬等人上臺執政為代表,曾在歐美興起了走“第三條道路”的思潮,卻是事實。我們強調的是克林頓他們不拘泥傳統教條的改革意識,“不受過時的意識形態的束縛”(布萊爾語),與時俱進的精神。
“第三條道路”最大的特點是“中間化”,淡化左右之爭,模糊意識形態分歧。如果說,布萊爾希望對“第三條道路”進行一些學術修辭,“既要突破舊左派那種專注于國家控制、高稅收和維護生產者利益的觀念,又要突破新右派倡導的那種狹隘的個人主義、相信自由市場經濟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放任自由主義”(《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施羅德則更坦白地承認“新中間”就是一種實用主義,“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舊的意識形態已被歷史的力量所壓倒,我只對當前起作用的東西感興趣”。
“中間化”不僅體現在理論和政綱中間化,也體現在黨的群眾基礎的中間化。英國工黨從20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按“新模式”著手改造工黨。1992年,對黨內的選舉制度進行改革,在領袖選舉上取消了工會在選舉中的集體投票制,實現“一人一票制”,減少工會對工黨的控制。布萊爾的“新工黨”與工會的關系已削弱到破裂的地步,“新工黨”把工黨從一個自稱為工人階級的政黨轉變為所謂的“超越于左右”之間的中間階層政黨,成為“企業界和商業界的政黨”。意大利共產黨在1989年3月召開第18次代表大會,把一個階級政黨改造成“代表全體意大利的公民”的綱領性政黨。1991年,意共第20次代表大會索性將黨易名為左翼民主黨,以示與舊黨的區別。
雖然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光譜中一直有左翼和右翼之分,但執政的政黨或政黨聯盟,不管是“中左”或是“中右”,實質上都只是政治天平在中間準星方位處左右的搖擺,而不會過分脫離中間區段。二戰之后,這種左右兩翼政黨的從黨綱到政策的趨同現象越來越明顯。 相比于舊左派和舊右派在意識形態理論上的堅持階級對應和實際政策上的中間化的表里不一,“第三條道路”把“中間化”理論化,明確承認走中間化道路。
當然,“中間化”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二戰之后,西方世界從圍繞物質財富的工業時代進入以信息和技術革命為標志的產業多元化的后工業時代:“一個私有財產、階級利益和階級沖突已經失去了‘中軸原理的社會形態。”工業大生產使社會分裂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利益分化以階級分野方式表現出來的社會里,政黨很容易地找到自己的群眾基礎,政黨與社會階級之間對應關系非常清晰,政黨很容易地實現著利益整合和利益表達的功能。產業結構的調整隨之而來的社會結構的變遷,西方社會從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抗的兩極結構逐漸向“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結構轉型。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中產階級雖沒有統一的標準,各國的統計數據有所出入,但“中產階級”傾向卻有一種擴大效應。1980年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46.5%的人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普通白領工人”愿意以中產階級自居,以其價值標準和政治傾向作為自己的行為參照。所以,中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力不能僅以社會中職業分布數量來判斷,應考慮其輻射效應。在中產階級數量和政治影響占優勢的社會中,中產階級的階級特點和政治需求會決定政治市場中的需求,影響各政黨所提供的政治產品——黨綱和執政政策的內容。中產階級不同于傳統階級,傳統階級具有相似的職業背景、集中的勞動場所,容易形成階級利益。而在“中產階級”這個標鑒下,是多樣的職業分化和不同的利益要求,多元成了中產階級的特征。多元的利益格局下很難形成一個簡單、明了、統一的階級利益。在以中產階級為基礎選民的西方社會中,各政黨基于選票壓力,只能以模糊和中間化的綱領來融合不同選民的不同的利益要求。政黨在民意集合方面的中間化一方面使社會實現一體化,不至于走向分裂;另一方面利益的模糊的表達方式,泛化的表達內容使政黨不能滿足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表達要求,政黨作為代議工具,民意表達方面這種功能缺失,加劇了政黨危機。“選誰都一樣”使許多選民放棄投票,造成政治冷漠的直接原因。而過度的政治冷漠會直接造成政治合法性的缺失。
所以,與歐洲的中間化道路相對應的政治現象是極右翼政黨在政治舞臺上的活躍,從法國的勒龐現象到奧地利的海德爾現象,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極右翼勢力的關注。極右翼勢力的出現與歐洲的經濟狀況和移民狀況有關之后,選民把選票投給極右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為懲罰性的投票,表達對由傳統大黨及其傳統政客控制的政府的貪污、低效、遲鈍的不滿,對國內各主流政黨模糊的政策的一種反動。選民在挑戰傳統政黨的時候,往往寧愿選擇缺少政治經驗的年輕的精英取代傳統政客。1992年46歲的克林頓擊敗華盛頓的政壇老手布什;1997年43歲的布萊爾取代資深穩健的梅杰;2000年政治經驗明顯不足的小布什擊敗曾擔任過兩任副總統的戈爾,選民渴望變革的要求表達的可謂淋漓盡致。
綜上所述,現代政治是政黨政治,盡管伴隨著計算機,網絡等現代交互技術的發展,電子民主能否取代代議民主制給人類政治帶有直接民主制的曙光尚是一個未知數,除了技術的可能之外,代議民主制作為基于對人類理性的懷疑和對暴民政治的憂患而建構的特殊的政治設置,短期內尚不可能退出人類的政治舞臺。代議民主制仍然需要政黨這種組織。在承認人民主權的社會里,政黨作為一種代議制工具,民意集合和表達是政黨的基本功能,伴隨民意的變遷,與時俱進、適時調整是政黨生存的基礎,也是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