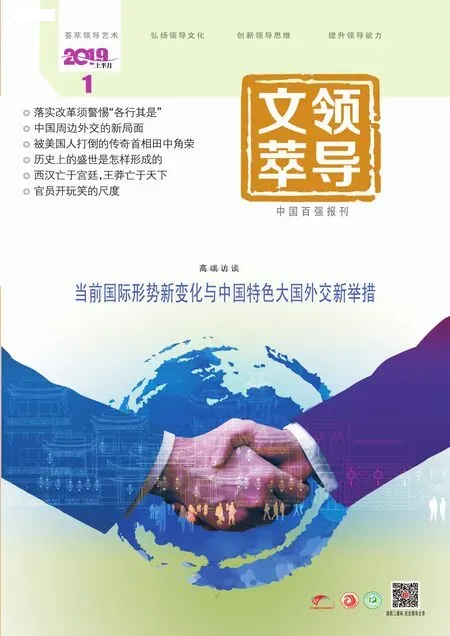“沒有人是不可替代的”
唐 昀
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淡粉色皇宮的一間密室里,穆罕默德·馬哈蒂爾把他那本頗具象征意義的工作手冊交到了接班人阿卜杜拉·巴達維的手中,然后走過鑲嵌著大理石地板的大廳,將他的拇指放在大門的安全感應器上。隨著大門在其身后緩緩關上,一個時代結束了。
歷史的一刻定格在2003年10月31日下午4:30。22年來,馬來西亞總理終于換了一張新面孔。
一聲長長的“再見”
的確,對馬來西亞來說,馬哈蒂爾是一面旗幟。自1981年以來,他擔任巫統主席22年,根據馬來西亞的政治傳統,巫統主席是總理之職的當然人選,因此他擔任馬來西亞總理也長達22年,其間還曾兼任國防部長、內政部長、財政部長。在馬來西亞人的心目中,他是天經地義的領袖;在國際舞臺上,他的名字甚至比馬來西亞還要響亮。國民早已習慣了他的領導風格,似乎從未考慮過沒有馬哈蒂爾的日子會是什么樣子。
然而,奇跡沒有發生。10月30日,馬哈蒂爾最后一次以總理身份出席國會,國會大廳空前爆滿,300多人被迫在走廊旁聽。當馬哈蒂爾走上主席臺準備發表演講時,眾議員擊桌表示歡迎。許多人是流著眼淚聽完他的演講的,整個會議室充滿了依依不舍的氣氛。當時在場的一位地方官員說:“我們都以為自己可以接受馬哈蒂爾的引退,一年前他就要我們作好心理準備,可是當離別的這一天真正到來時,我們卻是百般地難過與不舍,好像才突然意識到:‘它真的來了。”
相形之下,馬哈蒂爾卻顯得相當平靜,他像一位即將出遠門的老父親交代孩子們要看好家門一樣,一再叮囑眾議員繼續履行各自職責,給予繼任總理巴達維全力支持。當一名馬來西亞記者追問馬哈蒂爾是否會在最后一刻改變退休的決定時,他回答說:“不。沒有誰是不可取代的。我已經決定離開,而且我將會離開。一切不會因為一個人退位而停頓下來。”
他把馬來西亞變成“亞洲小虎”
一段時間來,馬來西亞幾乎所有媒體都在連篇累牘地歌頌馬哈蒂爾。面對如此多的贊譽,馬哈蒂爾應該說受之無愧。他擺過水果攤,開過工藝品店和咖啡店,后來攻讀醫學,懸壺濟世。職業的緣故,使他既有商人的精明果敢,也不乏醫生的縝密細心,加上他的倔強與特立獨行,在步入政壇后令世人刮目相看。
在執政的22年間,馬哈蒂爾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先是實施了以工業化為核心的新經濟政策,通過發展“自由貿易區”吸引外資,發展制造業擴大出口,鼓勵國內各企業向東方特別是向日本、韓國和中國學習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近年來又以“多媒體超級走廊計劃”推動馬來西亞走上知識經濟之路,把過去以出口橡膠、錫和錫制品為主的馬來西亞,改造成為今天可以生產電子儀器、鋼材和汽車等現代科技產品的“亞洲小虎”。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幾乎每一個馬來西亞人都能買得起汽車”。
對外,馬哈蒂爾是第一個提出“東亞經濟圈”構想(1990年12月10日)的人,他非常希望能以中、日為核心,帶動東南亞國家,形成一個類似歐盟的政經一體化組織,這一思想直接導致了東亞經濟論壇的產生。1995年,他又提出了“泛亞鐵路計劃”,以新加坡為起點,經吉隆坡、曼谷、金邊、胡志明市和河內抵達昆明,此外修支線通到緬甸首都仰光和老撾首都萬象,全長5500公里。以泛亞鐵路和中泰鐵路為核心的東亞鐵路網建成后,不僅能將中南半島鐵路網和中國鐵路網連接起來,而且還可通過中國鐵路網同歐亞大陸橋連接,直達歐洲。這是一項非常有遠見的建議。
當然,在馬哈蒂爾眾多的改革項目中,也有不少招來非議,比如建造那座號稱“世界最高建筑”的雙子塔——石油大廈,有人認為是一種奢華和浪費。不過馬哈蒂爾自有他的理由,他不希望馬來西亞在外國人口中是“泰國南部或者是新加坡北部的國家”,而希望聽人們說,那是“世界最高建筑物的所在地”。在大廈啟用儀式上,他曾有一段絕妙的講演:每個國家都應有值得抬頭仰望的東西;矮個子必須站在臺階上,而吉隆坡的這座石油大廈就是馬來西亞的臺階。此后便有了一種說法:“馬哈蒂爾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提升馬來西亞的高度。”
“一門容易走火的加農炮”
相對于國內眾口一詞的贊譽,西方社會對于馬哈蒂爾的引退要冷淡得多。一向喜歡指手畫腳的美國,這次表現出難得的“沉默”,其駐吉隆坡大使館竟然沒有發表任何評論。
這一異常反應顯然與10月16日馬哈蒂爾在伊斯蘭國家首腦會議開幕式上的一段講話有關系。他說:“歐洲人殺死了1200萬猶太人當中的600萬,如今猶太人靠代理人支配世界,他們讓別人為他們戰死,但13億穆斯林不可能被數百萬猶太人擊敗。”這段言論惹得美國、以色列、澳大利亞和意大利等國非常不滿,紛紛出面加以“譴責”。
幾天后,在泰國曼谷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現場,美國總統布什和馬哈蒂爾的幾句耳語續演了這場“猶太風波”:馬哈蒂爾說,布什沒有譴責他,甚至對美國政府措辭嚴厲的指責感到抱歉;而布什卻公開表示,他當時確實斥責了馬哈蒂爾,并警告他不可以挑撥離間,使人相斗。對此,馬哈蒂爾毫不示弱:“布什先生這個說法是天下最大的謊言。但是,自從布什說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開始,他就已經習慣說謊了。”
10月27日,美國參議院決定暫停對馬來西亞12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直到國務院確定馬來西亞推動了宗教自由,特別是對猶太人的寬容。對此,馬哈蒂爾嗤之以鼻,說美國參議院的決定更證明了他關于猶太人理論的正確,讓美國人把那點錢“留給自己去吧”。
馬哈蒂爾這一系列典型的“馬氏反應”,對美國人來說并不陌生。在其漫長的執政生涯中,他多次與美國唱對臺戲,令這個世界惟一超級大國很沒面子。遠的不說,“9·11”之后,他曾指責美國移民當局要求入境者接受拍照并留下指紋的新政策是“針對穆斯林的歇斯底里”;美英聯軍出兵伊拉克,他視之為“恃強凌弱的懦夫行為”,使全球重新回到“拳頭就是真理的石器時代”;美國批評馬來西亞沒有宗教自由,他針鋒相對:“那些從非洲被拐賣到美國的黑人,是在嚴刑拷打之下被迫放棄自己祖先的信仰而改信基督教的。”至于有人說他獨裁,他反唇相譏:“我是世界上第一位身體還健康就主動下臺的獨裁國家領袖。”
他不單單是跟美國“過不去”,對于國際事務中的諸多“不平事”,他也總要像俠客一樣“吼上一吼”、“斗上一斗”,故而落下一個“國際社會的唐吉訶德”的稱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他先是怒斥索羅斯是“掠奪馬來西亞人民財富的罪犯”,后又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交惡,逆其道而行,推行外匯管制。當西方國家肆意渲染“中國威脅論”的時候,他第一個站出來仗義執言:“根據我們的經驗,有人從8000英里外來到馬來西亞征服我們,殖民我們,但是中國離得這么近,卻從來沒有這樣做過。”就連聯合國,馬哈蒂爾批起來也毫不客氣,認為它只是按照強國的意愿行事,完全漠視了成立時的原則和目標,他甚至要求職合國秘書長安南立即辭職!
就這樣,馬哈蒂爾的不畏強權、敢說敢做在國際社會聲名遠揚,美聯社因此送了他一個綽號——“鐵齒銅牙”,并在其卸任之際編發了他的“語錄”:路透社稱這位已經78歲的老人為“憤青”:而曾遭其怒罵的索羅斯則將他比喻成“一門容易走火的加農炮”。
別看馬哈蒂爾有時候顯得有點口不擇言,其實這門“加農炮”十分清楚什么時候該“放炮”。在卸任前的記者會上,他道出了一個秘密:為馬來西亞爭取更高的曝光率是他的一大成就。“馬來西亞現在更廣為人知了……盡管他們可以不同意,但我想沒有人可以忽視我們的聲音。我們造成了影響。”
隨著馬哈蒂爾退出政治舞臺,這門“加農炮”似乎該“歇火”了,但他的一席話卻表明他并不準備偃旗息鼓:“下臺之后,我將更加不負責任地說話。因為我不再是總理了,人們也許不會注意我說些什么,所以我可以更自由地說‘臟話。”對此,布什的一名高級助理酸溜溜地說:“我們祝他退休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