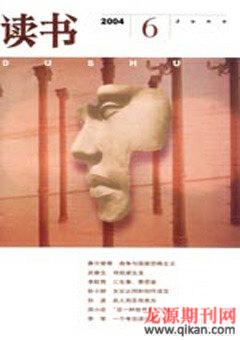日本對外擴張中的人民
周建高
“人民”的含義,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內容。綜合幾種不同語言的辭書對人民的解釋,共同之處可以歸納為兩點:一、人民是表示群體的集合名詞,在整個國家人口中占絕大多數。二、人民在一國內處于被統治地位,不屬于社會上層,不直接決定國家政策。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話題中,“日本”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國家名稱。與之相關的,“日本軍國主義”、“日本人民”之類的詞語也屢屢提及。現在簡要舉例分析一下我們的用例。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當時的中國政府首腦蔣介石說:“我們要嚴密責成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切不可予以報復,更不可對于敵國無辜人民加以侮辱。” 一九四八年四月六日發表的《中國各界名人對日政策聲明》中稱:“我們反對日本復興,完全因為現在日本政權仍掌握在少數侵略派手中,并非反對一般日本人民,反之我們很愿意與日本廣大人民合作,促成日本真正民主化早日實現。”一九五○年一月十七日,題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人民日報》社論說:“日本帝國主義曾經并且現在仍然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但是日本人民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有共同的敵人,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支持者美國帝國主義。”持此三種言論的人代表不同的政治立場。他們共同之處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侵略派、帝國主義者區別對待,而且認為日本人民與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處于對立位置。
一九五六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日本戰爭犯罪分子免予起訴決定書中稱,“鑒于日本投降后十年來情況的變化和現在的處境,鑒于近年來中日兩國人民友好關系的發展”,因此決定對日本戰犯寬大處理。當時日本與中國尚未建交,沒有政府之間的直接往來,只有民間交流。在這種語言情境里,也是把日本人民跟日本政府作不同立場看待的。
日軍侵華期間在山東擄掠了一個叫劉連仁的農民去日本做苦工。劉連仁不堪忍受北海道煤礦的強制勞動虐待,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逃出煤礦,隱匿于荒山中輾轉藏身十三年,受盡苦難。直到一九五八年才被人發現,而日本政府非但不道歉救助,反而稱劉連仁為有“非法入境的嫌疑”。后來在日本友好人士和在日華僑的幫助下回到祖國。劉連仁在回國的前一天,發表“感謝日本人民并譴責岸信界政府逃避責任的聲明”。在這個語境中也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作為對立的二元實體認識的。
根據此中“日本人民”一詞的用法來看,給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民一貫與政府對立、反對日本對外擴張侵略。歷史似乎并不如此簡單。
一八九四年日本和中國開戰后,三井、巖崎、涉澤等實業家組成了報國會,積極籌集軍費。婦女們則從事恤兵運動。與政府嚴重對立的議會,在開戰后也通過了巨額預算,作出了協助戰爭的決議。原計劃募集三千萬元的公債,實際募集到七千七百萬元。佛教各宗和基督教隨軍布教,慰問軍隊。《雪的進軍》、《婦人從軍歌》等軍歌在國民中廣為流傳,使軍隊斗志昂揚。《國民之友》雜志和《國民新聞》報的主編德富蘇峰,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日本開國以來“所淤積的磅礴活力的發泄”,是“與維新革命一脈相連的一次噴火”,大肆稱贊天皇的戰爭行為,認為皇室與國民上下一心,“發揚三千年以來世界無與倫比之大日本國體”(德富蘇峰:《大日本擴張論·序言》)。福澤諭吉,這位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以在日本提倡“文明開化”出名,一直高喊自由、平等和獨立。在戰爭打響后,不但在報上發表文章積極支持政府的侵略行為,認為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而且帶頭在民間募集軍費。戰后他在自傳中說:“這種官民團結一致的勝利,實在令人高興,值得慶幸。”福澤諭吉的弟子尾崎行雄,曾經參加過自由民權運動,后來被稱為“憲政之神”。一八九五年,他認為“并吞中國符合日本帝國之利益,亦為中華民族之幸福也”。甲午戰爭中日軍打敗清軍,日本社會充滿歌頌戰爭的聲音,連小學生也唱起了這樣的歌謠:“支那佬,拖辮子,打敗仗,逃跑了,躲進山里不敢出來。”
甲午戰爭中日本侵略朝鮮、中國之際,出現了空前的民族團結。這種情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的對外侵略中再度出現。
“九一八”事變為標志的侵華戰爭開始后,日本各地的火車站,連偏僻鄉鎮的小站,都經常出現歡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揮舞著小旗。人群中高呼“萬歲”。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軍在上海戰斗中,三個士兵陣亡,陸軍把他們渲染為“炸彈三勇士”。三日后,四個公司爭著以此為主題拍攝電影,一周后就在日本電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時,全國應征者達二十萬篇;還為“三勇士”豎立銅像和紀念碑,把事跡很快編入教科書,攝制了百部以上的電影。可見日本人民對于侵華戰爭的普遍關注和熱情支持。
日本工人、農民反對國內的資產階級,但是并不反對對外戰爭。“九一八”事變后,社會民眾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在堅決反對始終擁護資產階級權益這種態度的同時,我們也堅決不采取因為是資產階級的權益,滿蒙就應該無條件放棄這種空想的國際主義態度。”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該黨大會的口號中提出“把滿蒙的權益從資本家手中奪回來!”全國勞農大眾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召開的代表大會上,也提出“把滿蒙的權益從資本家手里奪回來,交給工人、農民”,“把我國現在的二百萬失業者派到滿蒙的原野,滿蒙的權益應該通過他們的手來處理。”
工人階級反對壟斷資本,擁護建立天皇制法西斯專政。“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工人組成了國家社會主義工會(德國法西斯自稱“納粹”,意即“國家社會主義者”。日本沿用之),他們主張強化國家的統治職能。日本勞動同盟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首先成立,包括三十八個工會,二萬七千四百多人。它主張東洋國際主義,支持擴軍備戰,反對和攻擊日本的反戰力量。一九三三年以后,日本主義取代國家社會主義,更加強調日本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整體一致的利益。日本造船勞動聯盟、國防獻金勞動協會,都積極支持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擴張。一九三四年二月成立的日本產業軍工會,在誓言和盟約中提出:我產業軍奉戴一君萬民的建國精神,以確立產業大權為我們的本分;產業大軍作為陛下的工人和農民,盡其本分,和祖國日本生死與共。許多日本主義工會的共同特征是呼吁“君民如一,舉國一致”“勞資一家”,掀起民族排外浪潮。一九三三年,日本共產黨的領袖佐野學和鍋山貞親在獄中發表共同聲明“轉向”,站在一國社會主義的立場,批判打倒天皇、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日共方針,提出要在天皇領導下進行一國社會主義革命。隨后,大量共產黨和接近共產黨的人改變方向。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勞農階級更走上與資產階級聯合支持對外戰爭的道路。“七七事變”后,日本政府發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令》和《國家總動員法》,全面加強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工廠企業則紛紛建立產業報國會,實現了真正的勞資一體。工會明確在綱領中寫上“產業報國”或者“產業報公”,規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爭減少事故,節約材料,利用廢物,提高勞動生產率。開展認購“愛國公債”活動,要求每個工人月月儲蓄,募集“國防獻金”。七月九日,日本上下議院一致通過了“感謝皇軍的決議案”,無產階級政黨的議員都贊成該決議。一九三八年,總同盟在十月大會上通過《對皇軍官兵的感謝決議》,稱贊“皇軍官兵的神速和果敢的行動”,表示要向皇軍學習,發誓在后方也要“像槍林彈雨中的皇軍官兵那樣的緊張,盡報國的微力”。他們召開歡送歡迎大會,組織募集慰問金活動。發生勞資矛盾、有些企業工人罷工時,工會則做調和工作,向工人曉之以理,在戰爭的困難時期,要求不能使生產下降,說明當時日本處于“舉國一致、勞資合作的時代”。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所謂日本建國紀念日,工人、政府和軍方代表在東京舉行“產業協力大會”,會議在《愛國進行曲》中揭幕,全場齊唱國歌《君之代》,遙拜天皇,然后為侵略戰爭中的“皇軍英靈”默哀,為戰爭勝利祈禱。與會者齊聲宣誓“在空前重大的時局里”“提高國家產業人員的自覺性,拿出勞資合作的誠意,為確保產業和平和生產力的發展,傾注殉國的熱情”。
在對外戰爭中興起的產業報國會這種民間的工農團體,一九三八年底達到一千余個,一九三九年四月激增到兩千多個,會員達到一百多萬人。它們要求政府“更加積極地領導”,于是厚生省和內務省按照行政區劃建立了各級產業報國聯合會,由行政長官和警察長任總監,工會與政府完全合為一體。各種原先主張不同的工會都“與時俱進”地改換方向,一九四○年,產業報國會在七萬個工廠企業中建立了支部,會員達到四百一十八萬人。到這年十一月終于成立了以厚生大臣為總裁的全國總工會——大日本產業報國會,它隸屬于法西斯政黨大政翼贊會。
太平洋戰爭開始后也是這樣。由于日本蓄謀已久,準備充分,起初階段軍隊推進很順利,從一九四一年底進攻珍珠港以后不到半年,相繼占領了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緬甸等地,政府、軍隊和絕大多數國民,都為日本的勝利陶醉。日本全國所有的力量,工人、農民、文化人等等各界各層的人們都被動員起來,產業報國會、農業報國聯盟、大日本婦人會、文學報國會等都集合到大政翼贊會旗下,支持戰爭。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輿論界在內閣情報局的指導下組成了“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強化對于言論的統制,新聞工作者們用“鬼畜美英”這樣的詞語,激發國民的同仇敵愾精神。特別要指出的是,大日本言論報國會領袖是堅持平民主義、主張自由民主的德富蘇峰,骨干有國家社會主義者津久井龍雄、評論家野村重臣等人。
再看后方的百姓。“七七事變”后,婦女兒童們,每天手舉小旗去車站歡送出征的士兵。許多成年人對于日軍在中國強暴婦女的行為,帶著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談論。新聞界,敢于真實客觀報道前線日軍暴行的記者一個都沒有出現,并掩蓋、隱瞞日軍失敗程度,使廣大國民不了解事實真相。南京陷落后,日本全國提燈游行慶祝,《讀賣新聞》社主辦了大慶祝會,萬余人會聚在一起歡呼,高唱《愛國進行曲》。不但出現妻子送丈夫、母親送兒子上前線,后方工人努力生產支援戰爭的情景,還有婦女、學生直接參加戰斗的。美軍在攻占沖繩戰斗中,遇到頑強抵抗,犧牲了四萬二千多人,傷亡超過諾曼底登陸戰役。當時沖繩本島人口四十七萬,有三分之一戰死。當地不少居民混在軍隊中,婦女裝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藥包,有的手握竹槍參加戰斗。女學生的“山丹部隊”、師范學校學生的“鐵血勤皇隊”都拼至最后一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沒有出現“二戰”后不少國家發生的那種國內民主派推翻專制政府的革命,不少民間志士相約集體自殺,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宮前嗚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請罪。
任何國家,無論專制政體還是民主政體,居于社會頂端直接決定事關全體利益的政策的人必定是極少數。構成日本社會的主體的群體,是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稱他們為日本人民,應該沒有疑義。那些支持對外擴張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百姓,他們構成了人民。
“日本人民”這個詞,在習慣于把人分成階級、從階級感情出發對人和事做價值判斷、而且自己覺得是站在人民立場說話的人看來,自然而然產生親切感。在民主改革之前的日本,人民確實沒有多少真正的自由。他們處于受剝削和壓迫的地位。作為人道的旁觀者,我們寄予同情。但是,在近代日本侵華歷史中,固然有被脅迫入伍者,但是從比例上說,沒有證據說明他們占了人口的多數。工人、農民、企業主、知識分子(包括宗教界、教育界、新聞界等)這些人民的基本成分,是積極支持對外擴張的。他們是日本社會的基礎。如果這些支持戰爭的人不算人民、只有反戰的人才被稱為人民的話,那么人民在日本社會中就是極少部分人。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人編撰的日本史著作,對于日本人民與政府密切配合、熱情支持對外戰爭的情形,絲毫沒有論述,只有極少數幾篇論文中偶爾提及。提到戰爭時期的日本人民,都是寫他們的反戰斗爭。這里面可能存在這樣一種邏輯:政府是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是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對立的。日本的對外擴張、侵略,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反動的,不得人心的,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對;而人民是進步的、愛好和平的。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侵略戰爭。于是一般中國讀者以為日本侵略戰爭是少數帝國主義者、軍國主義者、法西斯分子操縱國家機器、逆歷史潮流而發動的。這是從觀念出發編寫的歷史,沒有揭示出歷史的全部真實。就近代日本歷史而言,反對侵略戰爭的固然有,但是支持侵略戰爭的人更多。
在日本國內,有許多不同的思想意識,全體國民也因此分屬于許多不同的團體,有的還是尖銳對立的。但是在主張、維護日本民族利益這一點上,大多數日本人,是非常一致的。一旦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對外的時候,原先國內階級之間的矛盾就被民族矛盾、國際矛盾代替。那種把日本人首先定性、分類,然后根據某類人具有某種性質的公理,稱軍國主義者本性就是要侵略,人民天生愛好和平,而且他們之間判若天壤,再推導出結論來的分析方法,是用靜止的、絕對的觀點看待人和社會。作為大前提的公理首先就不符合人類社會的實際,當然難以獲得對對象的正確認識。例如中國人把“二戰”時期日本人民與資本主義、與政府的矛盾斗爭說成是“反戰斗爭”,與此不同,日本工會首領松岡說:“我確信,勞資官民為建立真正的舉國一致體制和確立東洋和平必須共同努力。作為日本人,當然有愛國心。迄今,為抵制政府和軍部鎮壓,屢次進行了斗爭,但是,這都……不是反戰、反國家運動。”要說日本人民的反戰,如前面提到的,他們是反對資產階級獨占海外利益,倒不是同情受害國人民。沒有國民自覺的主動積極的戰斗精神,日軍在戰場上絕不會表現得如此兇猛。一九四二年五月阿留申群島的阿圖島之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部太平洋的吉爾伯特群島的塔臘瓦島、馬金島之戰、一九四四年六七月之間馬里亞納群島海戰,日軍全部陣亡。尤其是塞班島的戰斗中,日軍戰至最后一人,非戰斗人員包括婦女則集體跳海自殺。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間,美軍進攻硫磺島、沖繩島過程中,又遇到同樣的情況。沖繩之戰中,日本軍人死亡八萬五千多,人民死亡達九萬四千人。日本走上戰爭道路,不僅是天皇個人、內閣、軍部少數人推動的,而是全體日本人,在國內、國際多種因素作用下,各種力量相互影響的綜合結果。
我做此文,是鑒于近兩年一些媒體上對于中日關系的討論中,仍然出現用固有思維看待日本社會的現象,即把某個對象從它原生環境中抽出來,孤立地分析、評論。例如說日本有和平憲法;日本人民大多生活富裕;日本國會中有反對黨,各派勢力相互制衡,因此不可能再走上戰爭道路。外交問題進入學術討論領域,是中國進步的表現之一。人們可以發表各種主張,但是立論必須遵守邏輯規則,首先大前提必須真實。就近代日本來說,人民、政黨和政府,時常出現紛爭,但是在對外擴張侵略中,他們是高度一致的,這也是日本民族集團主義的表現之一。我沒有因此得出結論說“日本人民是好戰的、富有侵略性”,讀者也切勿根據我的文章得出這樣絕對的公式。個人也好,民族也好,其思想、行動由多種因素決定的;而且人的思維、習性是隨著時代、交際而改變的。社會環境決定人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