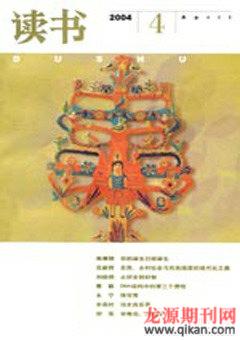文化多樣性 裕固族 文化研究
巴戰龍
我們身處的時代被宣稱為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居住的這個曾一度被認為是宇宙中心的星球也被想像成一個小小的“村落”——“地球村”。美國人塞繆爾·亨廷頓說,人類群體間的暴力沖突應該被解釋為地域文明間的沖突,而更多的人也相信,軍事—武力的霸權已經演化成了經濟—文化的霸權。睿智的人們觀察到:隨著源于西方的現代性的擴展,特別是全球貿易體系的構建和實踐,西方文化鋪天蓋地席卷而來,無情地吞噬著非西方文化,非西方文化在這場“歐美化”的浪潮中無聲無息地退縮和消亡;在一些民族國家內,悲劇同樣在上演著,產生于十九世紀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被進一步庸俗化為合法的意識形態,所謂的主流文化以“傳統—現代”、“野蠻—文明”和“落后—進步”等水火不容的“二元對立”為合法性依據,冠冕堂皇地給非主流文化和地方性知識判死刑,并積極地加以消滅。人們開始擔心起來,由于全球化所導致的“天下大同”,會不會使人類文明最終走上毀滅的不歸之路。這個問題更多地得到了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這群以探求人類社會文化的“奧秘”為使命的人們的觀察和思考。
還是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十九世紀,社會學和人類學都接受了當時的顯學——生物學的“啟蒙”,將“社會”和“文化”同生物有機體做了有趣的聯想和比附,發展出各自的“古典進化論”并借以自立。在“古典進化論”者自認為過著“最文明”的生活的日子里,人類也在“最野蠻”地對自己生活其間的生態環境進行“蹂躪”和“摧殘”,使生物種類迅速減少。晚近“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口號和理念或多或少反映出人類對自己作為未來惟一的物種孤獨地生活在這個星球上——一個“獨夫”的凄慘晚景的想像的恐懼。很可能又是在生物學的“啟蒙”下,“文化多樣性”這個術語被發明出來,據說是為了對抗具有“帝國主義”色彩的另一術語——“全球一體化”。
在這種大的時代背景中,請設想一下:一個人口只有一萬三千余人的民族會怎樣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如果再把這個民族進一步定位在中國西部的甘肅省,再接下來,如果不做任何解釋,直截了當地宣布這個民族叫做“裕固”,大多數人也許都能體會到絕望情緒的不斷增進。
裕固族不為人知是事實,盡管這讓許多人感到理所當然,畢竟不像不知“盎格魯—撒克遜”那樣讓人覺得尷尬不安和難以接受!獵奇的媒體并沒有對裕固族的歷史文化做“深度報道”,而只報道他們“荒服殊俗”的一面,間或有“翻身做主人”和“發展”、“進步”的政治性宣傳穿插其中。
從現在刊布的資料看來,裕固族這個現代民族是一群西方探險家重新“發現”的。繼最早涉足裕固族地區的俄國生物學家戈·尼·波塔寧(Potanin,G,N)之后,芬蘭前總統曼內海姆(Mannerheim.C.G,又譯馬達漢,)于一九○七年和一九○八年的年節更替之時到達那里,做了較為詳細的人類學考察。他在一九一一年發表的題為《撒里與錫喇堯乎爾人訪問記》的民族志之第一部分《在撒里堯乎爾人中間》的結尾處不無傷感地寫道:“我清楚地感覺到,這個迷失的突厥語部落,這個男人靠織襪子為生的部落,正在一步步趨于消亡。”(鐘進文:《芬蘭前總統曼內海姆對裕固族地區的記述》,載劉郁宋主編:《中國裕固族》,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21頁)在歷史推進了八十多年之后,一位名叫毛郁生的地方政府官員在寫給兩位辛勤的民族文化采風者編寫的書籍的《序》中說:“我認為,裕固族在中華少數民族歷史發展的長河中能夠長期繁衍生息,很值得研究。”(田自成、多紅斌編著:《裕固族風情》,甘肅文化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序》,2頁)這兩段文字告訴我們,這個自稱“堯乎爾”的民族在“趨于消亡”中不知歷盡多少磨難和艱辛又“活”過來了。歷史的結果常常讓人意想不到!
裕固族聚居在祁連山北麓的山區草原和河西走廊的戈壁綠洲及平川牧場上。斷流的黑河之源頭和刮出國境的沙塵暴之源頭都與裕固族地區有著某種關系。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使這個民族以畜牧業生產為主、狩獵與農耕為輔的生產方式難以為繼。政府及其“參謀”——幾個社會學研究機構里的博士——勸導走廊里的裕固人“休牧還草”、“改牧為農”。這一次是中國人類學(含民族學)的“異數”張承志來“清算”自漢武帝以來中原農耕生產方式毫無節制地在河西走廊擴張導致的惡果,同時他也針對“生態移民”的行為以一種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的口吻寫道:
其實這條走廊,這條平川牧場早已經一半沙漠。河西早已不在羌胡時代,它早已變成無孔不入的農耕啃咬殆盡的一塊骨頭了。幾個裕固人能左右如此巨輪么,他們早就脫下了袍子靴子,等著最后做完向農民的蛻變。
博士論文居然參謀說:可以在銀行里存一個游牧方式。先休牧,等生態好轉以后,從銀行取出定息豐潤的“休牧儲金”,用這款子買回牲畜。我讀得啞口無言。看來,新事物還不僅只是棄牧為農的牧人;在時代潮流中急欲亮相的知識分子也開人眼界。——在人工草坪上恢復牧業嗎?用存款買回一個文明嗎?只怕你落入千載的輪回,旱死渴斃,再也無法超度!
……明花“農業綜合開發基地”的裕固人,居然請來韓國的資本,把十萬畝草場一下子墾為農田!真是特有的民族,特有的故事!看來,住在民化飛地上的裕固人,無法再維持他們牛毛帳篷的游牧生活了。在與農耕和同化的攻防中,掙扎了不知多少世紀的半農半牧方式,終于被一些敗家子在一頓飯的工夫,最后地翻了底。(張承志:《匈奴的讖歌》,載《收獲》二○○二年第二期)
事實又一次教訓了人們:“新世紀”和“新千年”并沒有帶來新生活,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并沒有增加人們的幸福!同時值得一提的是,張承志和給政府做參謀的博士都在同一時段去裕固族地區考察過,觀點和立場卻如此相異,關涉的又豈止是研究倫理!
不能不承認,這世界變化得就是快。新時期以降的二十多年,中國的“民族研究”已經走過了一條“民族學”的道路,如今又在轉向“人類學”和“社會學”,它的從業者已經從“民族研究專家”學科化為“民族學家”,近期又自稱“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了,“民族研究”當然也得相應地轉為“文化研究”。
“裕固族研究”是 “民族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裕固族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大致有下述種種:(一)這個民族有語言無文字,她的歷史由于缺乏典籍文獻的記載而顯得“撲朔迷離”,這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想像力和工作熱情。(二)盡管這個民族操著兩種分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和蒙古語族的本民族語言,卻都自稱“堯乎爾”,供認是一個“民族”(很顯然,對于堯乎爾人來說,“裕固”和“民族”都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后才有的東西),這始終都對斯大林的經典“民族定義”構成一種挑戰。(三)這個民族的風俗習慣,特別是婚姻習俗中被認為有“母權制”和“母系社會”的殘余,這為排定中國民族社會“進化的譜系”提供了“佐證”。(四)這個民族的兩種本民族語言被認為非常“古老”,特別是西部裕固語被認為是古突厥語的“活化石”,是一種仍然“活著”的最古老的突厥語,是回鶻文獻語言的“嫡語”。在國外裕固語研究成果斐然的壓力下,“本土研究者”被認為有一種“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為國爭光”的光榮使命。(五)改革開放打開國門后,隨著“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有專家發現這個民族的一些民歌和口頭文學與遠在歐洲的匈牙利民族的一些民歌和口頭文學居然“如出一轍”,這又一次引起了有關人士的極大興趣,在裕固族地區也訛傳起“歐洲也有裕固族”的說法。
國內“裕固族研究”的成果,很多是為了落實國家關于“搶救落后”的號召,在“民族識別”和“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兩大工程中積累起來的,除了就一些情況和材料是否“真實”的討論之外,缺乏對上述研究成果進行較為深入的梳理和反思。從總體上看,“裕固族研究”也同過去的“民族研究”一樣,注重迎合“國家建設”的需要,以不很“科學”的手段積累和重復著“民族志”知識,陶醉于民族歷史文化的“自我敘事”,致力于作為一種“人文類型”的獨特性的建構或“族性建構”。從這個案例看來,要擺脫“民族研究”的“慣習”,談何容易。
在“民族研究”轉向“文化研究”的過程中,像裕固族這樣的“小民族”或“人口較少民族”的研究有可能由于被忽略而走向衰微。現在“文化研究”,特別是人類學研究的主流是以“村落”觀“帝國”,進行“中國研究”,“海外研究”也開始被積極地嘗試。曾被中國“民族學”引以為驕傲的一批具有少數民族文化背景的“本土研究者”如今處境尷尬。
由國家主導的西部開發再次為“本土研究者”提供了發言機會和研究基金。在“保護文化多樣性”的議題中,“本土研究者”為裕固族提供的“處方”除了“休牧還草”、“改牧為農”,還有教導老百姓做出“現實選擇”,把“裕固文化”通過影像拍攝和文字記錄送進“博物館”去給后代和游客進行展覽的“高招”。看來,從“民族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術語變換并不一定能帶來“本土研究者”內在的研究理路和范式的變換。
在對“和而不同”的人文世界的追求中,像裕固這樣的民族面臨的問題依然尖銳地挑戰著人們的智慧,而早已躋身城市的“本土研究者”卻多少有些“隔靴搔癢”或“站著說話不腰疼”。站在歷史文化“十字路口”上的裕固人如今仍然孤獨而無奈地生活在他們祖先的土地上。一位青年語言文學專家告訴我,他在裕固族地區的田野調查中聽到最多的是裕固人清晰且意味深長的感嘆:“唉!”或“唉——”
是耶?非耶?難道我們真的要把一切都推給“歷史”去進行“審判”嗎?!
(《中國裕固族研究集成》,鐘進文主編,民族出版社二○○二年版;《裕固族文化形態與古籍文存》,賀衛光編著,甘肅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漂泊的洞察》,王銘銘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