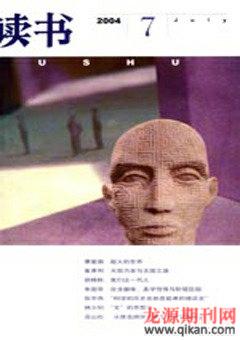“文”的思想史
“文”的概念是東亞知識(shí)分子,尤其是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思想史的核心概念,但這一簡(jiǎn)單事實(shí)在百余年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一直為人們所忽視,鮮有中國(guó)哲學(xué)史、思想史談及。
“文”的式微與現(xiàn)代性的理念(idea)息息相關(guān)。“現(xiàn)代”以及與此相關(guān)的理念登堂入室之際,也正是“文”這一核心概念黯淡無(wú)光之時(shí)。不獨(dú)中國(guó)如此,鄰國(guó)日本亦然。因此從“文”的角度重新審視日本知識(shí)分子史將為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審視自己的思想史提供一種可能。
“文”究竟是什么?章學(xué)誠(chéng)曾從訓(xùn)詁的角度解釋一般意義上“文”的概念:“胡虔氏曰:‘文字古有二訓(xùn):‘依類象形謂之文,此文字之‘文也;‘青與赤謂之文,‘五采備曰文,此文質(zhì)之‘文也。其以文質(zhì)之‘文為贊美辭之美者,《易》之‘旨遠(yuǎn)辭文,《左傳》之‘言之無(wú)文,行之不遠(yuǎn),皆是也。則‘文字乃虛字,不過與‘辭輯、‘辭懌之‘輯‘懌相等耳。魏、晉以來(lái),以辭章為‘文,不與辭字相屬,竟作實(shí)字用矣,此亦徇俗而昧初義之失也。”(《文史通義》外篇,312頁(yè),遼寧教育出版社)。關(guān)于學(xué)科意義上的“文”的概念,中國(guó)歷史上也有過劃分,但這些劃分之間未必歷然可辨。如南北朝時(shí)宋明帝曾設(shè)儒玄文史四科。章太炎討論“哲學(xué)”在中國(guó)學(xué)問中相應(yīng)的研究領(lǐng)域時(shí)就曾提及此四科,曰:“南北朝號(hào)‘哲學(xué)為‘玄學(xué),但當(dāng)時(shí)‘玄、‘儒、‘史、‘文四者并稱,‘玄學(xué)別‘儒而獨(dú)立,也未可用以代‘哲學(xué)”(《國(guó)學(xué)概論》,30頁(yè),上海古籍出版社)。章氏質(zhì)疑的是近代學(xué)科制度中的“哲學(xué)”一詞的正當(dāng)性。清代則有義理、考據(jù)、詞章之學(xué)之分。戴震謂“義理即考核文章兩者之源也”,未免有以“義理”傲視其余二科之嫌。然祖述其說(shuō)的段玉裁則稱:“先生合義理、考核、文章為一事”(《東原年譜補(bǔ)訂》,見《戴震全書》第六卷,708頁(yè),黃山書社),此后曾國(guó)藩更將三科變成四科:“有義理之學(xué),有詞章之學(xué),有經(jīng)濟(jì)之學(xué),有考據(jù)之學(xué)。義理之學(xué)及《宋史》所謂道學(xué)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xué)在孔門為言語(yǔ)之科。經(jīng)濟(jì)之學(xué),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jù)之學(xué),即今世所謂漢學(xué)也,在孔門為文學(xué)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也。”(《曾國(guó)藩治家全書》卷上《日記·問學(xué)》,岳麓書社)不過,戴氏的“義理”是建立在對(duì)曾氏“義理”(宋學(xué))的批判之上。需要注意的是,按段氏的說(shuō)法,戴氏將三科合為一事,而曾氏力主“闕一不可”,章氏也強(qiáng)調(diào)南北朝“‘玄、‘儒、‘史、‘文四者并稱”,頗耐人尋味。
筆者在此強(qiáng)調(diào)的是方法論意義上的“文”的概念(倫理意義上的“文”將另文探討)。方法論意義上的“文”的概念與上述的訓(xùn)詁角度及學(xué)科史角度的“文”的角度雖然不同,但卻不無(wú)關(guān)聯(lián)。它的關(guān)聯(lián)至少表現(xiàn)在其語(yǔ)言學(xué)的屬性上。須知,所謂知識(shí)分子思想史和文學(xué)史,無(wú)非是由語(yǔ)言建構(gòu)的歷史。其語(yǔ)言學(xué)屬性具體體現(xiàn)在知識(shí)分子對(duì)理論體系的探求、對(duì)書寫體的選擇以及作為話語(yǔ)歷史的知識(shí)分子話語(yǔ)之間的編織及沖突關(guān)系等方面。這里的“書寫體”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美國(guó)批評(píng)家法蘭克·倫特力奇亞在其《新批評(píng)之后》第四章中所言與個(gè)人化“文體”有別的,指一個(gè)時(shí)代的作家有一定共性、規(guī)則性、習(xí)慣性的整體要素(Frank Lentricchia:After the New Critic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二是德里達(dá)所言對(duì)應(yīng)聲音中心主義的“書寫”概念。關(guān)于后者,筆者想指出,東亞思想史中未必有類似德里達(dá)力詆的形而上學(xué)傳統(tǒng)語(yǔ)境中的聲音中心主義,但在理論和經(jīng)驗(yàn)意義上卻明顯地存在著一個(gè)壓抑“文”的概念的聲音中心主義。這一點(diǎn)中日皆然,只是兩者壓抑“文”的語(yǔ)境同中有異。
因此,“文”的概念的重提意味著東亞思想史,尤其是中國(guó)思想史語(yǔ)境中的語(yǔ)言學(xué)轉(zhuǎn)向。東亞近代學(xué)術(shù)體制源于西方近代學(xué)術(shù)體制,其中哲學(xué)雄踞群學(xué)之首,這一“哲學(xué)”以強(qiáng)調(diào)其與“文學(xué)”、“史學(xué)”之異而維持其眾學(xué)之冠的地位(類似的劃分前提也適用于近代意義上“文學(xué)”、“史學(xué)”的成立)。在西方,自尼采洞察哲學(xué)在修辭性等語(yǔ)言學(xué)性質(zhì)上其實(shí)與其他學(xué)科(特別是文學(xué))并無(wú)二致之后,近代的學(xué)術(shù)體制開始遭到質(zhì)疑。尼采的說(shuō)法似顯激進(jìn),但只有如此才能將學(xué)術(shù)史從形而上學(xué)堆砌的理念中解放出來(lái)。
其實(shí),類似尼采的說(shuō)法在東亞傳統(tǒng)中可以說(shuō)是常識(shí),區(qū)別只在于兩者的語(yǔ)境。如宋代的批評(píng)家陳(一一二七——一二○三)曾說(shuō):“《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shī)》之有比,以達(dá)其情;文之作也,可無(wú)喻乎?”(《文則》丙上卷)他將《易》、《詩(shī)》都視為“文”。既然視為“文”,就須訴諸修辭性。“文”的概念甚至有著更寬泛的內(nèi)涵。《國(guó)語(yǔ)·鄭語(yǔ)》的“聲一無(wú)聽,物一無(wú)文”,談的正是作為事物本質(zhì)的差異性以及尊重這一差異性的重要性。由后者可見,“文”的問題又是倫理問題。如《左傳》說(shuō)“言之不文,行之不遠(yuǎn)”,此處之“文”不僅是近代學(xué)術(shù)制度中的修辭學(xué)意義上的“文采”,更是語(yǔ)言與他者性這一倫理性的問題。在近代學(xué)術(shù)史上,不僅“文”,甚至“文”重要的派生概念“修辭”也被矮化。《易經(jīng)·文言》中的“修辭立其誠(chéng)”的內(nèi)涵在現(xiàn)代被抽而一空,即屬此例——“修辭”這一東亞傳統(tǒng)思想的重要概念被代之以近代學(xué)術(shù)意義上的基于分類、歸納方法論的狹義“修辭學(xué)”(亦即rhetoric的翻譯詞),與此相關(guān)聯(lián)的,是修辭方法論從中日近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中的消失。“物相雜,故曰文”(《易經(jīng)·系辭傳》)顯示的作為差異性原理的“文”,本該在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中將其開放的多元主義價(jià)值在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過程中發(fā)揚(yáng)光大,但百年過后,我們卻瞠目于一個(gè)無(wú)情的事實(shí):東亞學(xué)術(shù)中的相當(dāng)部分原來(lái)只是西方學(xué)術(shù)(尤其是形而上學(xué)傳統(tǒng))和一些排他性理念的冗長(zhǎng)注腳。
既然方法論概念的“文”將思想史視為知識(shí)分子的話語(yǔ)歷史,我們有必要對(duì)“話語(yǔ)”一詞做一限定。所謂話語(yǔ),在語(yǔ)言學(xué)理論中,它指大于句子、由句子構(gòu)成的語(yǔ)言表現(xiàn)。同時(shí),也指歷史的意義上某一集團(tuán)、社會(huì)固有的語(yǔ)言表現(xiàn)。因此,后者往往與語(yǔ)言權(quán)力性(意識(shí)形態(tài)性)的探討相關(guān)聯(lián)。方法論意義上的“文”的概念體現(xiàn)為對(duì)知識(shí)分子的社會(huì)實(shí)踐與其語(yǔ)言學(xué)性質(zhì)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進(jìn)行考察的方法論視角,換言之,也是一種從語(yǔ)言學(xué)角度觀察歷史的嘗試。在這個(gè)意義上,“文”的重提也是從語(yǔ)言角度考察歷史、恢復(fù)歷史性的重要視角。如果說(shuō)作為語(yǔ)言學(xué)轉(zhuǎn)向的“文”的重提意味著將語(yǔ)言從觀念(理念)的統(tǒng)治中解放出來(lái),那么這同時(shí)也意味著語(yǔ)言所包含的歷史關(guān)系性將穿透觀念和意識(shí)形態(tài)隱蔽而厚重的黑暗重獲光明。
但是,從理論的角度看又必須充分注意:一個(gè)歷史事件與對(duì)這一事件的敘述(語(yǔ)言化)之間未必可以相合無(wú)間地畫上等號(hào)。就是說(shuō),經(jīng)驗(yàn)與語(yǔ)言有著不可避免的縫隙。而且,如何語(yǔ)言化“一個(gè)歷史事件”同時(shí)又避免從誘發(fā)“這一事件”的錯(cuò)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性中將其切割出來(lái),并使之實(shí)體化,這往往又是一個(gè)復(fù)雜問題。首先,我們?cè)谠O(shè)定一種“歷史”時(shí),事實(shí)上卻往往只設(shè)定了某一類的理念以及從屬于這一理念的某一類敘述方式而已。如“某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可能只是“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現(xiàn)代化”這兩個(gè)統(tǒng)治性的理念的間接派生物。稱之為“間接派生物”是因?yàn)樗皇墙饬x上的literature的翻譯語(yǔ)的“文學(xué)”這一派生性理念的派生。這樣的“文學(xué)”以宣稱自己與另外兩個(gè)學(xué)科的“哲學(xué)”和“史學(xué)”是如此的不同而為其成立條件。同樣,現(xiàn)代學(xué)科制度中的“某國(guó)哲學(xué)”與“某國(guó)史學(xué)”的成立背景亦可作如是觀。因此,如何將上述“文學(xué)”“哲學(xué)”“史學(xué)”從理念中復(fù)原其語(yǔ)言學(xué)的性質(zhì),甚至將歷史性從理念隱秘的統(tǒng)治中解放出來(lái),是一個(gè)重要問題。其次,我們時(shí)刻不能擺脫的,是我們所選擇的語(yǔ)言與我們內(nèi)在的意識(shí)形態(tài)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以及我們所選擇的語(yǔ)言與時(shí)代總體的敘述方式和敘述方向所隱藏的意識(shí)形態(tài)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從這一意義上說(shuō),語(yǔ)言對(duì)人們的控制無(wú)時(shí)不在。同時(shí),我們往往無(wú)從直接判知這些隱秘的意識(shí)形態(tài),而只有通過語(yǔ)言這一意識(shí)可以他者化(對(duì)象化)的材料才能得以究明。這是一個(gè)不可避免的悖論。這也揭示了對(duì)意識(shí)與語(yǔ)言之間不言自明的同一性的虛幻。
關(guān)于意識(shí)與語(yǔ)言之間的非同一性的論述,在漢字圈的思想傳統(tǒng)中俯拾即是。比如《易經(jīng)·系辭》中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說(shuō),此處的“意”雖然原指圣人之“意”,但從理論上說(shuō),談的正是“言”、“書”、“意”三者之間不可同一地畫等號(hào)的問題。《莊子·天道篇》中也說(shuō):“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yǔ),語(yǔ)有貴也。語(yǔ)之所貴者意也,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此處所言正是“書”、“語(yǔ)、“意”三者之間不可避免的錯(cuò)位。陸機(jī)(二六一——三○三)在《文賦》中也說(shuō):“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說(shuō)的也正是“文”“意”“物”三者之間的斷裂。將意識(shí)與語(yǔ)言透明地相等,或者說(shuō)將語(yǔ)言簡(jiǎn)單化,這是現(xiàn)代以來(lái)的一個(gè)認(rèn)識(shí)上的失誤。近代以來(lái),我們淡忘了一個(gè)重要事實(shí)——漢字文化圈思想的一個(gè)重要傳統(tǒng),正在于對(duì)語(yǔ)言與意識(shí)的復(fù)雜關(guān)系的綿綿不斷、鍥而不舍的思考。而這一思考正是通過“文”這—概念在美學(xué)、倫理等意義上展開的。
還是回到歷史性的正題吧。如此一來(lái),“歷史性”是否被虛無(wú)化了呢?恰恰相反,上述問題的提出正是為了恢復(fù)作為關(guān)系性的歷史性。借此擺脫預(yù)設(shè)的,甚至是觀念化的“歷史”對(duì)我們的統(tǒng)治。語(yǔ)言——各自迥然相異的意識(shí)或以碰撞或以交錯(cuò)的方式相關(guān)聯(lián)的這一公共空間——為我們提供了相對(duì)化這一預(yù)設(shè)的“歷史”以及棲身其中的“觀念”的控制的重要方式。基于語(yǔ)言的方法論,“歷史”將被暫時(shí)地?cái)R置起來(lái),轉(zhuǎn)而探求文本的話語(yǔ)本身的歷史性,并希望通過這一方法接近圍繞某一事件某一社會(huì)歷史狀況的種種關(guān)系性,以避免“真實(shí)的歷史”這一說(shuō)法本身的獨(dú)斷性。這至少是探討歷史關(guān)系性的一種重要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學(xué)術(shù)與狹義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差別,正在于后者是依據(jù)某一中心的預(yù)設(shè)性的語(yǔ)言操作,而前者則是致力于相對(duì)化這一中心之“關(guān)系性”復(fù)原作業(yè)(筆者堅(jiān)信此乃學(xué)術(shù)之意義所在)。因此,歷史上的“文”——這一語(yǔ)言實(shí)踐的產(chǎn)物——成為最為關(guān)鍵之處。在這一方法論視角下,如下的問題的探討變得重要:文本中具體的語(yǔ)言操作如何,其內(nèi)在結(jié)構(gòu)怎樣,促成這一語(yǔ)言取向的意識(shí)形態(tài)性(借用尼采式的說(shuō)法則是其權(quán)力性)是什么,它與某一時(shí)代固有的語(yǔ)言表現(xiàn)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促成這一時(shí)代固有的語(yǔ)言表現(xiàn)的外部因素又是什么……這些手續(xù)意味著對(duì)被分析的語(yǔ)言對(duì)象的種種關(guān)系性的復(fù)原。這一關(guān)系性正是話語(yǔ)所處的“場(chǎng)”,用語(yǔ)言學(xué)術(shù)語(yǔ)表達(dá),就是所謂的“語(yǔ)境”(它自然包含了社會(huì)的語(yǔ)境)。在此,“關(guān)系性”與“歷史性”這兩個(gè)用語(yǔ)是同一意義的。而這些術(shù)語(yǔ)的選擇與回避實(shí)體主義和觀念論(idealism)的意圖息息相關(guān)。
正是在此意義上,近代意義上的“文學(xué)”與“史學(xué)”之硬性劃分的問題性凸顯出來(lái)。何況,如果說(shuō)“某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可能只是“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現(xiàn)代化”這兩個(gè)統(tǒng)治性理念的間接派生物的話,那么,對(duì)這些理念在具體歷史語(yǔ)境中的展開方式的研究(也就是近代學(xué)術(shù)制度意義上的“文學(xué)”的研究),與歷史研究在本質(zhì)上究竟有多大的區(qū)別,也是一個(gè)顯而易見的問題。近代學(xué)術(shù)制度意義上的文史哲三科相互排斥的自我特權(quán)化由此可見一斑。在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制度中,“文學(xué)”、“哲學(xué)”、“歷史”之間被劃分得涇渭分明,它們共通的語(yǔ)言學(xué)屬性也因此被掩蓋起來(lái)。指出“語(yǔ)言”這一它們所共有的媒介,有助于打破此種人為的設(shè)定,以達(dá)至文史哲三學(xué)科在語(yǔ)言學(xué)方法論中的融合。因此,重提“文”與學(xué)科史的關(guān)系,并非討論改變學(xué)科劃分這一約定俗成的事實(shí)的可能,而是想借此概念強(qiáng)調(diào)知識(shí)分子思想史本身(亦即“文”本身)的語(yǔ)言學(xué)屬性以及“文”這一概念的方法論重要性。
因此,“文”的問題也是一個(gè)與現(xiàn)代性相關(guān)的問題。日本如此,中國(guó)亦然。如果說(shuō)近代西方的普遍性的到來(lái)令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包括部分東亞知識(shí)分子)對(duì)原有的普遍性產(chǎn)生了深刻危機(jī)的話,那么,作為其結(jié)果,后來(lái)的中國(guó)革命則可以說(shuō)是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在苦斗中覓得的另外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的表現(xiàn)方式。從狹義的角度看,中國(guó)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正是一種新的“文”的語(yǔ)言形式。從廣義的角度看,中國(guó)革命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在特定的歷史時(shí)期尋找新的“文”的社會(huì)接點(diǎn)、實(shí)踐新的“文”的獨(dú)特的方式。同時(shí),馬克思主義的中國(guó)化也具有歧義性。一方面它為原有的普遍性提供了一種西洋化(新的普遍性)的表達(dá)方式,另一方面它又是在一種“古今”“東西”二元對(duì)立方式下的線性進(jìn)步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近代以來(lái),線性進(jìn)步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往往互為表里)。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一九一四——一九九六)曾說(shuō):“通過馬克思主義這一普遍的世界觀,中國(guó)才得以突破華夏民族主義。”(《日本現(xiàn)代的革新思想》,49頁(yè),巖波書店二○○二年)雖然丸山真男未能意識(shí)到中國(guó)式馬克思主義與傳統(tǒng)概念的“文”的關(guān)聯(lián),亦即語(yǔ)言的關(guān)聯(lián),但是丸山之言可謂發(fā)而不失正鵠。如果說(shuō)“文”與現(xiàn)代性的問題今天仍是貫穿日本知識(shí)分子思考中的一條主線,那么,在近現(xiàn)代,歷史迥然有異的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文”與現(xiàn)代性的關(guān)系則更是一個(gè)仍然在苦苦摸索中的問題。甚至可以說(shuō),“文”的問題是中國(guó)的現(xiàn)代性中最大的懸案。尤其是在今天,在經(jīng)歷了十年“文革”之后,帶著許多歷史的正負(fù)遺產(chǎn)進(jìn)入商品化大潮的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將面臨著新時(shí)代中的“文”的問題。無(wú)“文”,則非“知識(shí)分子”——想必這一命題有助于讀者理解本文強(qiáng)調(diào)的語(yǔ)言學(xué)視角的重要性。日本知識(shí)分子尋找“文”的種種努力,相信能給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帶來(lái)啟示,因?yàn)椤拔摹北旧硎浅絿?guó)界的一個(gè)語(yǔ)言性公共空間。
基于上述的思考,帶著中國(guó)思想史文學(xué)史的問題,在《文與日本的現(xiàn)代性》一書中我選擇了從十七世紀(jì)至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后現(xiàn)代思潮為止的幾位日本思想家和文學(xué)家為論述對(duì)象,以期展示日本知識(shí)分子如何在不同的時(shí)代尋找自己的“文”,以及因之而來(lái)的種種內(nèi)在沖突。從“文”的角度看,由于同屬漢字文化圈,也許沒有一部知識(shí)分子史能像日本知識(shí)分子史那樣對(duì)中國(guó)有借鑒作用。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日本”是一個(gè)思考“中國(guó)”的重要的視角。因?yàn)椋瑹o(wú)論在正面還是負(fù)面的意義上,兩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思想史都是對(duì)方的鏡子。
按論述對(duì)象的思想家、文學(xué)家所處時(shí)代的不同,本書在內(nèi)容上劃分成“前近代的日本知識(shí)分子”、“近現(xiàn)代的日本知識(shí)分子”、“后現(xiàn)代的日本知識(shí)分子”三部分。將江戶碩儒荻生徂徠(一六六六——一七二八)置于本書的開篇,是因?yàn)榘偌覡?zhēng)鳴的江戶思想與近現(xiàn)代日本知識(shí)分子思想史之間,恰若一條川流不息的長(zhǎng)河,其間有著“抽刀斷水水更流”的關(guān)聯(lián)。正如不言晚清,何談“五四”一樣。長(zhǎng)期以來(lái)中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認(rèn)識(shí)日本的現(xiàn)代性,在時(shí)間上習(xí)慣于以明治維新為起點(diǎn),在角度上則過于偏重政治和經(jīng)濟(jì),這樣很難完整地認(rèn)識(shí)日本。必須指出,政治、經(jīng)濟(jì)、侵略戰(zhàn)爭(zhēng)都不過是歷史關(guān)系性的產(chǎn)物,不明了其歷史的關(guān)系性,便很難對(duì)對(duì)象本身有一個(gè)較為全面的認(rèn)識(shí)。這一部分主要涉及儒學(xué)等前近代思想的重評(píng)問題。本書的第二部分“近現(xiàn)代的日本知識(shí)分子”,則以著名文學(xué)家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新感覺派代表作家橫光利一(一八九九——一九四七)、現(xiàn)代主義詩(shī)人西脅順三郎(一八九四——一九八二)為對(duì)象,從理論的角度探討他們?cè)跁鴮懻Z(yǔ)言等問題上與現(xiàn)代性的種種沖突。這一部分主要涉及近代的聲音中心主義批判以及文學(xué)上的現(xiàn)代主義問題。最后的“后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思想”部分,則主要論及了以柄谷行人(一九四一——)為代表的八十年代以來(lái)日本的后工業(yè)時(shí)期日本知識(shí)分子圍繞著現(xiàn)代性的問題所展開的種種論述。這一部分涉及何謂日本語(yǔ)境中的后現(xiàn)代思潮的問題,同時(shí)也希望為中國(guó)的“后現(xiàn)代”提供一個(gè)借鑒(如果中國(guó)也有一個(gè)與后工業(yè)社會(huì)無(wú)關(guān),但作為知識(shí)分子思想而存在的“后現(xiàn)代”的話)。
筆者相信,任何學(xué)術(shù)史都是平凡的勞動(dòng)薪火相傳的歷史。這本身正是“文”的一種歷史。讓我們遠(yuǎn)離獨(dú)斷論式的聲音中心主義的單一性,步入“文”這一紛繁多義的語(yǔ)言空間。在這一語(yǔ)言的空間里,讓我們重新冷靜地審視作為關(guān)系性的歷史,以重評(píng)我們的現(xiàn)代性。
(《“文”與日本現(xiàn)代性》,林少陽(yáng)著,中央編譯出版社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