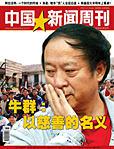董光璧:從當代人類面臨的挑戰看中國傳統文化和未來的科學
方玄昌 鄭偉庭
“中國文化的輝煌在技術主導的農業文明時代,衰落在制度主導的工業文明時代,新生的機遇在觀念主導的科業文明時代。我們的輝煌與技術相關,失敗與制度相關,新生將與觀念相關。”
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由技術、制度和觀念三大子系統構成,文化的演化業已經歷了技術主導和制度主導兩個階段,當代正在向觀念主導的時代過渡。觀念系統包括信仰、理性和價值,它的發展經歷了信仰主導和理性主導,現在走向價值主導。人類的文明之車依靠兩個輪子前進,一個輪子是科學技術,另一個輪子是倫理道德。
當代的人類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三個,一個是環境惡化的傾向,一個是高技術發展的預測困難,一個是科學與人文發展的不平衡。工業文明時代的人類生存在技術崇拜和恐懼的張力中,感受到技術的反傳統性,也認識到科學理性的缺陷,并試圖通過觀念重建來調整文化。
現在一些思想家開始從中國傳統中尋找智慧,我們熟悉的有李約瑟,他覺悟到應該按東方的見解辦事,包括李遠哲在內等諾貝爾得獎者“回到孔子”的呼吁、世界宗教會議的《世界倫理宣言》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普遍倫理計劃”,都試圖改變當代世界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不平衡的狀況。
在這種尋求價值觀的努力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被關注。《易經》塑造了一個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它從春秋戰國時代開始逐漸取代了商代時期的神學思想,為進一步演化發展為中國文化核心角色奠定了基礎。學者們有關“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表明,它既不是人類中心主義也不是自然中心主義,而是以兩者的關系來思考人類和自然的問題。它是一種宇宙觀和世界觀,同時也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思維方式,并且代表著一種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
中國哲學家馮友蘭把人類精神劃分為四個階段,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中國歷史學家錢穆認為“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終歸屬,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人類的最大貢獻。中國哲學史家牟宗三認為確立了中國傳統文化主流價值觀的《周易》,包括了能夠產生科學的數理、物理和客觀三種觀點。
中國傳統文化在面對人類當代的挑戰時有什么意義呢?易學與科學的結緣表明易學是中西文化的契合點,中國是在儒學格物致知延伸意義上接受產生自歐洲的現代科學的,并經歷了從“格致”到“科學”的轉變。明朝末年的徐光啟不僅把易學象數學和傳教士傳入的科學對等,還借《易傳》“會通”的概念,提出“中西會通”的主導思想。在國外,通過了阿拉伯人和傳教士,易學傳到了歐洲。所以有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和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等科學家對易學的研究。易學作為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結合點,也吸引了當代一些學者的關注。
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產生在17世紀的歐洲,在溯源的意義上才有古代的和中古代的科學,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文明,和中國傳統文化沒有源流的關系。但在類比的關系上,可以談論中國科學。在19世紀中葉隨著科學的發展,中國開始接受產生在歐洲的科學,但是迄今對科學發展的貢獻微不足道。
如何理解中華文明在科學上的失敗,如何改變當今中國科學事業的落后狀況,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中國文化的輝煌是在技術主導的農業文明時代,衰落是在制度主導的工業文明時代,新生的機遇在觀念主導的科業文明時代,即以科技產業性為其標志的新文明時代。所以就主導因素來考慮問題的話,我們的輝煌與技術相關,失敗與制度相關,新生將與觀念相關。
現代科學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是沿著產生自歐洲的科學傳統演進的,但其未來走向并不一定總是沿著既定的方向。在如何建構后現代科學的話題中,中國文化傳統受到關注,意味著中國傳統中的某些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可能會重新獲得生命力。李約瑟反對把中國傳統科學視為失敗的典型,認為它保留了內在而未誕生的充分意義的未來科學,但是什么叫“未誕生的充分意義的未來科學”,他沒有給出更詳細的闡述。
最近幾年我一直在探索中國傳統科學的理論特征,我認為任何科學傳統的差異,都不在科學內容本身上面,因為自然規律不會因發現它的民族的不同而改變,其差異主要表現在科學規律的表述上面。而表述不同是基于哲學觀的不同及其影響的邏輯形態和理論構造方式的不同。
在中西對比下,考察中國傳統科學的特征,我把它概括為生成論的自然觀、比類和互補的邏輯推理、模型化的理論構造。這里不能詳細說了,我舉個例子。我們要問,鹽為什么是咸的,花為什么是紅的,解答歸結為原子的結合和分離,這就是現代科學的構成論觀點。而生成論把變化看成是產生和消滅的過程,這樣的觀點在現代科學中最重要的體現就是量子場論,它是專門描述基本粒子的產生和消滅的理論。但是不是所有的物理學家都有這種自覺。
我們的現代科學習慣于把理論搞成公理化的體系,因為牛頓就是那樣做的,愛因斯坦也是這樣做的。這種表述方式使得科學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也存在問題。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的發現,對公理化理想是一個致命性的打擊。這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模型論的構造是不是就不好?它跟公理論的構造有同樣的推理功能,有些科學哲學家認為模型論可能更加適合現代科學的發展。
在科學的當代演變中,一種新的科學理性也正在形成。過去科學家總是把科學的運用視為科學之外的社會問題,原子彈爆炸之后科學家不完全這樣認為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開始把科學的社會運用也包括在科學探索的過程之中。過去的科學研究活動對價值因素的考慮較少,現在越來越重視科學活動的價值問題,價值作為科學理性的新成分開始規范科學家的行為。以前的科學理性主要考慮邏輯理性、數學理性和實驗理性,但它們只能保證科學知識的條例性、精確性和可靠性,卻保證不了科學一定能為人類造福,所以我們要增加一個新的科學理性因素——價值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