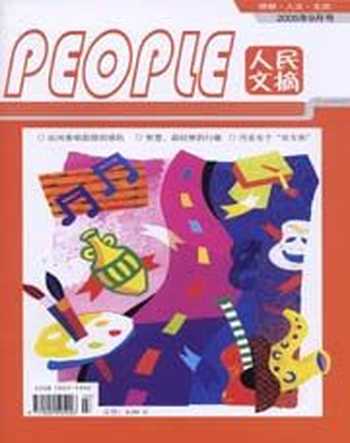我眼中的中國農民
黃銳杰

在我眼中,農民是和土地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他們以最為謙卑的姿態行走在黃河中下游廣闊的平原上。他們佝僂著肩,聲音嘶啞,眼里爬滿如土地般厚重深沉的哀痛。他們一走走了五千年。
我還小,住在江西南面的一個小鎮。我的祖父,一個倔強沉默的男人,時常來看我。他往往出現在黃昏。我從學校放學回來,端了凳子坐在屋外寫作業。冬天的天黑得快,天一黑空氣里就要帶上寒意。我寫上幾行,手不聽使喚地抖。冬日的陽光是一種白慘慘的亮,令人心慌。當我停下來往手里哈氣,便看見一團黑影。那是祖父,他總是以一副亙古不變的姿態俯身看我。他的眼睛里寫滿我所不能理解的疼惜。那種眼神,我至今不能忘記。
祖父的到來是父親的一件大事。他不管多忙,總要停下手里的工作。兩個沉默的男人,他們躲在屋里的一角用我所不能理解的語言低聲交談。這是一段神秘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他們就某些問題達成共識。又一個白天,祖父收拾好東西啟程離開。他的身影穿過小鎮外崎嶇的山道消失在冬日黯淡的天際。我知道,這么一趟短短的旅程,在祖父的生命中,是一個永遠也解不開的結。
父親那時候的面容在我的記憶中已經日益模糊。我的父親,他有和祖父一樣粗糙的右手。他的臉總是帶著秋雨般的陰郁。他體形瘦削,卻曾經和朋友打賭一口氣吞下了五籠雞蛋大的小籠包。就是這么個男人,他第一個走出了祖父所在的小山村。他在外地讀完師范,來到我們這個小鎮,娶妻生子,安安穩穩地做起了小學教師。
逢年過節,我們總要回到祖父所在的小山村。村子建在山腳下,很多房子零落地散布在不大的范圍內。一條馬路,混合著砂石和黃泥,從村子前經過。
祖母總站在屋子前的一座土包上等我們。看見我們來了,她的嘴角毫不掩飾地牽扯出難以遏止的笑意。她以嘶啞而又熱情的土話招呼我們。而在她的兒子面前,她顯得有點拘謹。
祖母一生生育了六個孩子,最小的一個男孩子在十二歲時死于突如其來的肺炎。我的父親,他成了這個不幸的家庭里惟一的男丁。
祖父和父親的見面是一次無言的交流。他們互相看著對方,長久不發一言。后來,祖父點了點頭。他轉身走開,繼續手里的農活。
這個晚上,兩個男人留在客廳里。我躺在隔壁的床上,能聽見他們細若蚊蠅的聲音。話題大多關于農村的事。祖父談起村里的一些爭端,向父親征求處理意見。其實大多數情況下祖父已有主見,他只是向他名義上的繼承人征求同意。這類談話要持續很久。我總是在天亮前才模模糊糊地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從床上醒來,祖父已經準備好農具,地里的莊稼正列隊等待他的到來。
母親斷斷續續地向我談起祖父和父親的事。在父親之前,小山村里還沒有人在外面上過學。我能想象當年少的父親向祖父提出這個要求時祖父臉上的表情。在村里人眼里,身為長子的父親是理所應當要擔負起一家人的生計的。然而,父親沒有。
我不知道當時的父親是怎么樣說服祖父的。這其中必有不為人所知的內情。也許他們曾激烈地爭吵過。也許祖父的拳頭曾經如雨般落在父親的身上。如今這一切都已經隨時間逝去。然而總有些線索如宿命般纏繞在這兩個男人的身上。
就是在村里人眼里,祖父對土地的態度也近乎于固執。他總是在早上六點準時起身,吃過祖母準備的簡單的早餐便帶上農具前往田地。他在一塊廢棄的田里種滿了莊稼。每一天,他細心為這些莊稼松土、澆水、施肥、除蟲。在整個村子里,祖父的莊稼是長勢最好的。他對莊稼的熱愛,一直維持到他去世的前幾天。
祖父去世的時候,我讀四年級。父親由于工作出色,早在一年前已經調到廣東的一座小城市工作。接到電話是在晚上,電話那邊的大姑語音哽咽。聽到祖父去世的消息,父親愣了愣。很長時間內他沒有說話。我們在接到電話的第二天啟程返鄉。這是一次沉默的旅行,父親自始至終未發一言。
葬禮定在三天后舉行。在一片沉痛的哀悼聲中父親的表現是最為平靜的。葬禮上人們談起祖父生前的事,語氣都是嘆惋的。他們說,祖父和父親其實是一樣倔強的人,在祖父年輕的時候也曾要求離開這個村子。他的要求遭到了曾祖父的強烈反對。而他在一個晚上離家出走,從此下落不明。七年后,他突然又出現在村子里。這時曾祖父已經離世,留下了一間土屋。祖父在這間土屋里住了下來,并且在村子里娶了一個老婆。他們還說,祖父死之前經常端了一張凳子坐在大山前。他的嘴角時常帶著笑意。
葬禮后,我們又回到了父親現在工作的地方。父親越發沉默起來。他的眼里時常帶著我所不能理解的憂郁。他時常站在窗前眺望遠方。他的目光穿過擁擠的樓房落在遠方某處不確定的地方。只有我知道,在那里,有曾經養育過他的廣闊的土地。
(陸 健摘自《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