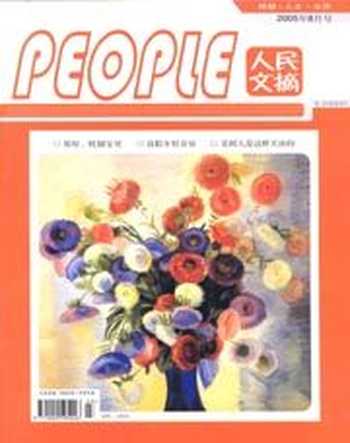最后的44天
肖存玉

春節期間,父親從臺北打電話給我,聲音顯得沒力氣,時有咳嗽的聲音。
“爸爸您病了?看醫生了嗎?”我有點著急。
“去過醫院了,這次咳得太久,可能有些麻煩。”爸爸說。
“您趕快回來吧,我找最好的醫生給您看病。”父親接受了我的意見。
父親毅然決定結束在臺灣五十多年的旅居生活,回大陸度晚年,讓我們全家雀躍。
父親在一個臺灣朋友的護送下,乘坐臺灣—澳門的長榮航班。我們按時來到珠海拱北海關等侯,那天風大雨大霧大,飛機在澳門上空盤旋一個多小時后迫降香港機場,待天氣轉好再返回澳門。
在焦急的祈盼中,我們站在關口熬了六個多小時。更讓我想不到的是當父親出現在我面前時,我卻一下子沒認出來:輪椅上坐著一個戴著深藍色圓頂絨帽,系著大圍巾的小老頭,在帽子和圍巾之間露出一張蒼白、胡子拉雜瘦得只有巴掌大的臉。我叫了一聲:“爸爸”,心里一酸,眼淚往上涌,又強忍了下來……
我的兒子連忙收起攝像機,雙手托起父親抱進汽車里。這時,我才知道爸爸已無法進食、身上穿著紙尿褲、說話無聲,只是兩只眼睛瞪瞪地望著周圍的環境,神智還清晰,從他的表情看出他心里流露出的絲絲愉悅。
第二天,父親住進醫院。經CT檢查,發現肺上一個比橙子還大的腫瘤將食管掩埋,肝上一個大過乒乓的腫瘤將氣管擠到只有一條縫,診斷為晚期肺癌。當醫生一邊指著照片一邊對我說這番話時,我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無法理解眼前的事實,我絕望了,我感到我失去了所有的能力,為我無法挽救父親的生命而極度傷心。
輸氧、消炎和營養點滴使父親的病情得到了暫時的緩解。我守坐在病床前,爸爸斷斷續續地對我說:“在臺灣沒有家的感覺。”我在本子上寫了一句話:臺灣像飄蕩在大海上的一只小船,大陸才是一塊堅實的土地。遞到爸爸跟前,爸爸看了后點了點頭。
我請了一個24小時的陪護,白天我基本守在那里,晚上回家休息。可是,每當我清晨趕到病房時,同病房的黃伯就向我“投訴”:你爸夜里總是叫你喲。我對黃伯解釋說:“我們與一般的父女不一樣,我今年57歲了,只見過父親幾次,積累的就是牽掛,他剛從臺灣回來,只在家里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到這里來了,他心里自然不踏實。”
父親的呼喚又怎能讓我安心?夜里時時驚醒、咳嗽、發燒,我也病了。爸爸睡在住院部病床上,我躺在門診治療中心打點滴……
一天下午,我打完點滴,來病房看爸爸,見他臉色不好,我緊緊地抓著他的手,他望著我,知道我病了,示意我坐下來。一會兒,爸爸松開我的手,手指往外彈,要我回家。我拖著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沒有睡著,這時,接到了醫院的電話:父親病情危急。
我和先生立即趕往醫院,見父親呼吸急促,兩手不斷地劃動,我緊緊地抓住爸爸的兩只手,不時呼喚著:爸爸,爸爸!爸爸已感覺到了,他有意識地抓緊了我的手,但時間不長。我無助地看著監視儀的數字不斷地滑落、滑落,很快就降到了零。
我的爸爸就這樣走了,他的手還被我緊緊地抓著。他終年在大陸待了44天,也是我們相處時間最長的、憂傷的44天。
(侯 真摘自《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