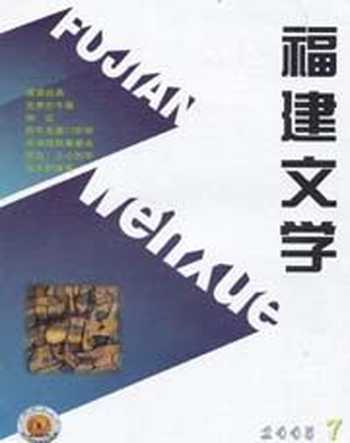誰是誰的上帝
魏艷琳
繁華街區的十字路口,一個少女躺在血泊之中,身旁是一輛濺染著鮮血的大型卡車。
這樣的場景不時可見,對于當事人和肇事者來說,分明就是一場飛來橫禍,也許從此將改變他們的人生——如果他們之中還有人“生”的話。而對于旁觀者,無非是發出一兩聲感嘆,再共同制造出一串長長的塞車隊伍。
這讓我想起小時候經常玩的堵截螞蟻的游戲。拿一塊小木板在埋頭匆匆趕路的螞蟻面前一橫,擋住了它的去路,感覺自己手中有著扭轉乾坤一樣的巨大權勢。而小東西連頭也不抬一下立刻掉轉方向朝另一個目標繼續前進。目標?我不知道它是否有目標,或許有,不是聽說過螞蟻王國嗎?那么它也許人在往家里趕,去和它的親人團聚。這么說,在我居住過的那幢易于筑穴壘巢的老屋里還為眾多的微型動物們提供了棲身的家園呢!我像上帝一樣俯瞰著它的走勢與動向,仿佛我能左右它的前程。它每走幾步,我使用于中的道具讓它改變方向。這樣不厭其煩地去挑逗一個弱小的生物以此滿足一個長期總在聽命于大人們指揮的小人兒偶爾也能操縱一下他人命運的快感。難道不是嗎?我只要輕輕往地上吹一口氣或者往它的身體上澆一盆水,頃刻間它便會不知去向,甚至,我只要伸出我的小指頭輕輕一碾,它的微不足道的生命便會同它的旅行一同結束。并且,它的同伴們將永遠找不到它就此消逝的緣由——因為一個無所事事的小女孩對這個世界與對“他人”世界的好奇與躁動,還可能是某種破壞性的強迫癥而導致的某個時空段落里的一場悲劇。會是悲劇嗎?這樣的死難對于生命輕如鴻毛的它們來說,也許是每分每秒都會發生的事情。它們會發出求救訊號,登出尋親啟示,四處探問同伴的下落以致終日惶恐不安嗎?抑或,在確認了同伴的死訊之后,它們會舉行盛大的哀悼儀式,追思并且永遠懷念它們的親人嗎?這些我都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我卻清楚,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一輩子都不會知道答案。這樣也好,這能確保我不會在獲知了許多事物的真相之后對這個世界全然失去興趣。帶著某種對前方始終無法洞悉的茫然、惶惑和本能的生存慣性,我依然賴活著,渾渾噩噩地延展著我的人生之路。
也許,在盛栽著人類的宇宙天體里,每一個人都是那只不時要遭逢堵截的螞蟻,而凡塵俗世上的一切苦難均是上帝伸出的攔截之手,會不會也是它偶爾無聊時耍玩的一個小把戲,將它無意中犯下的錯失嫁禍于人間,可是因為人類在它面前的渺小羸弱,在他看來只是一塊小木板般輕微的阻擋,便足以改變一個小人物一生的命運,甚至足以將它毀滅。
這讓我相信,一場龍卷風的突然駕臨來自于上帝倦怠時打出的一個呵欠,由于氣流大大,人類瞬間遭殃;一場洪水的傾巢而出就更是上帝嗆出的一個噴嚏,他的唾沫四溢,造就了人間的洪災;還有那些蔓延森林的無名之火,只可能是上帝急火攻心,往地面上發泄的一股怨氣……
就在我胡思亂想并且開始對這個單調的游戲感覺有些乏味的時候,媽媽來喚我去吃飯了。我立刻放棄了剛才那場關于生死存亡的思想戰斗,臨走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只陪伴了我一個下午無聊時光的小生靈,它依舊泰然自若孜孜不倦地一味行走,好像它的目標永無盡頭。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出乎我意料之外,讓我措手不及的事情:媽媽要來拉我去吃飯的一只腳不偏不倚地踩在了那個一秒鐘前還運動著的身體上,那只腳看起來碩大無比,像是從天而降,并且它因為我忽然的遲疑不前也沒有及時抬起來,還在那里來回扭動著,原因只是她拉不動呆若木雞的我,更加使勁地施力于她所占據的地盤上,企圖將我挪動開來。最后我被媽媽像老鷹捉小雞似的挾持起來,一邊聽到媽媽失去耐心的埋怨:“這個孩子真是越來越遲鈍了,跟木頭一樣!”我毫無反抗意識地保留著那個被挾持的姿勢,只把頭轉過去看我期望看到的東西——除了那塊被我扔在地上的小木板,那里空空如也。仿佛它原本就什么也不存在過。毀滅總是毫無先兆地在轉瞬間降臨。
吃飯的時候,我還在想著那只螞蟻,我很想鉆到桌子底下去看看媽媽的鞋底,可是我終于什么也沒有做,因為媽媽的數落聲越來越大:“你看看,玩得都傻了,飯也不好好吃,掉了一地!”
那只螞蟻永遠從我的視線中消失了,不是因為我向它吹氣或澆水,更不是因為我用手指頭去碾它,它是從媽媽的鞋底下消失的,這一點我看得千真萬確。
這么說,媽媽才是它的上帝。
其實我不想做上帝。真的——我不想傷害它。
那以后,我不再對地上的細微生物發生興趣了。因為它們讓我不明所以地感到憂郁。我轉而對天上的事物比較關注起來了。我時常抬頭去仰望天空,是微若塵埃的生命望向楚天的迷離。它是那樣高遠,那樣深不可測。風云與大地丈量著我們的距離,一個神秘的不可往來的國度,那里會有天堂嗎?還有上帝?他可曾像我俯視一只螞蟻一樣觀望過這一群仰視他的人類嗎?曾經有一度我以為死去的奶奶會是上帝,因為媽媽說,奶奶會在天上看著我長大,并且一直保佑著我們。可是我越長大,越感覺到事情并非我原先料想的那么簡單。面對神的旨意,我們的想象力顯然過于貧乏而拘謹。
看著看著,我逐漸感到暈眩。一個站在灰色天幕下的卑微的生傘,是誰賦予她思想的權柄?她如此驚訝地感受著宇宙間詭異莫測的力量,她費力地去想象著上帝會有怎樣的一副尊容,它是否應有一張滿是皺折的臉,身體里流著抑郁的血。為什么,會打呵欠和噴嚏,會發脾氣的上帝,在不該沉默的時候卻緘口如瓶。它難道沒有聽見人世里熙熙攘攘哭叫求援的聲音?或者,他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像一個人在與死神較量的最后時刻,像天使欲哭而流不出的眼淚,像突然被風吹開的《圣經》扉頁無力地翻打在臉上的不病不癢……我驀然看到它眼睛里最最深刻的悲哀。
那具不知死活的少女的身體己被遲遲趕來的工作人員像搬東西一樣地抬走。積攢了一時的車隊漸漸疏朗開來。方才還零亂不堪的場面立即又恢復為表面的井然有序。那個留下刺眼的血跡的方位,在不久以后的日子里,便會被人們徹底遺忘,仿佛它原本就什么也沒發生過。而它背后的故事,將永遠不會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