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宵別夢寒
蔣 蕓

到青山寺去求一根簽,想問問自從父親去后,為什么總也夢不到他。簽上說他正在遠游。年輕時的他,愛游山玩水,現在塵緣已了,正可以還他心愿。只是他一個人太寂寞了。路過道教的青松觀,還是放心不下,還是要求一根簽,想問問父親的近況:錢夠不夠花,冬衣暖不暖,那些他游歷的地方好不好玩。真是寂寞啊!沒有人陪他,為什么連夢也不捎一個來?大概他還在生我的氣。他生氣時,總是這樣不言不語,透著些疏淡,叫我看了傷心,比罵我還難過。
就是在他七十歲生日的前一個月,悄然離開,等不及我回去見他一面。靈堂前,照片中的父親俯視著我,眼中有太多要說的話,也好像在等我跟他說話。
在他病重的那些年里,我本來應該守候在他榻前,跟他說些令他寬慰的話,說些我從未告訴過他的秘密往事:在成長的過程中,曾小心隱瞞著他的事兒,但是,我仍然拋不開那些俗事俗務。當他仍在人世的歲月中,心中帶著牽掛與病魔搏斗,而我卻為了并不充分的理由,疏遠地往返著,真是對不起他。而他去后,曾經寫過那么些文字的我,竟無一言一語來紀念他,只是一味支撐著心里面的凄涼、傷心、絕望與無可彌補的歉疚。雖然那樣明白,日子過得愈久,那些感覺愈濃,那樣的想念他,那樣的愛他,卻是太遲了。
父親的影子,漂浮在我童年的記憶里,在一年一歲的成長歷程,在一些記愛與記恨的思緒中,逐漸壯大。我總是要讓他知道啊,父親是那樣疼我,我想臨去的那一霎,他仍是惦著我的,親愛的父親。
我在記憶中翻尋,可曾有過依偎在他膝前的歲月?可曾向他發過小女兒式的嬌嗔?他可曾對我說過一些足以寵壞我的話?不,自我懂事以來,他和我們總是聚少離多。父親的慈愛躲在他高大的身影里,躲在他緊抿的唇角中。但是,每一個我長大的重要時刻,他總會趕來。那一年,在風城,面臨緊張的升高中考試,從臺北回來的父親得了腹膜炎,躺在醫院中。我帶著復雜的心情,惦著他的病,惦著自己的考試結果,從新竹女中到新竹醫院的路程變得那樣長,慌亂的自行車,幾次差一點把行人撞倒。我不敢去看榜,只想早一點看到父親。那個夏天的風城,竟沒有風,街道兩旁,仿佛連路燈也沒有。一排排的病床前,父親虛弱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母親以棉花替他濡濕著,他只是說:“考不取也沒關系,不要擔心。”三年后,上臺北考聯考,同現在已當了十多年修女的偉利住在光鹽宿舍。晚上,父親成了修女宿舍中惟一的男訪客,沙嬤嬤引他進來,父親的影子在黯淡的燈影中顯得那么慈愛。只是我那時實在不知道前途,真想撲在他懷中大哭一場,告訴他,我實在不想考這勞什子的大學,這樣辛苦的準備,不知道為的是什么。但我只是像一個中學生站在老師面前一般,一句話也沒說。父親仍然說:“考不取也沒關系,不要擔心。”與三年前同樣的一句話,竟成了我的定心丸;它是吉利的象征,對我。
他實在不是一個多話的男人,他的嚴肅與威儀使我從來沒有機會對他說:爸爸我愛你,我想念你。我大概也遺傳了他的這份倔強,不會說一些甜蜜的話,即使是真的感覺也難以啟口。在木柵的第一年,父親請了假來看我,宿舍里每個同學都說他神氣,我很驕傲,卻也沒對他說過。我們一同走到車站,我送他回臺北,一路上,沒有什么話說。而假日,我去看他,他不在,工友替我打開爸爸的房門,一屋子的陽光。我就在他的宿舍中暖暖地睡了一覺,到現在還能感覺到那股直透心底的溫暖。天黑了,父親回來,看到我,笑了。那笑容也像下午的陽光,隔了二十年還記得分明,我卻從來沒有對他說過那時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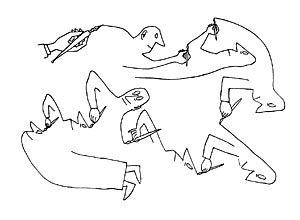
離開家以后的那些年,我習慣拿那些年紀與父親差不多的人與他比,客觀地比,總覺得沒有人能比得上父親。親愛的父親,有人拿玉樹臨風這四個字來形容男人,而年輕時的父親,最配得上這四個字。十七歲那年,他獨自從蘇州到上海討生活,在艱難的環境中自學自修,從不間斷。我們常翻他讀過的書,眉批上的字,詳細而獨到;他苦練的柳體,挺拔秀氣得像他的人;他自己發明的讀詩讀詞的聲調,韻味十足,冬夜里,聽來特別蒼涼。好幾回,耳際響著父親讀詩詞的聲音,催眠著我思鄉的夢。啊,我親愛的父親,今宵別夢寒。
每一回過年,我們總搬個炭爐子進客廳,讓父親大顯身手做蛋餃。他的蛋餃做得真細致,一般兒形狀、一般兒大小。他原是一個整潔的人,等他病倒了,再也沒有做蛋餃的心情,年也不像年了,總覺得缺少了什么,雖然,記憶里仍然留存著橘子皮在炭火中爆發的香,混合著蛋餃的香,彌漫在我們小小的廳中。這些也無可追尋,在外頭,更怕過年了。
父親做事的機關,是負責外銷商品檢驗的。有時,家中也來些送餅干的人,餅干盒中自有乾坤,而我們每回早已懂得以跑一百碼的姿態,將餅干盒送回饋贈者的手中。因為,總也忘不了,第一回打開盒子時,見到鈔票,父親憤怒的臉脹得通紅,他一生最恨人不誠實。還記得初來香港第一年,看臺灣的報紙,爸爸局里的金牛貪污案,大大小小官員牽連好幾十人。編劇部的董千里先生開玩笑說:“有沒有你父親的大名?”
以父親的職位,不可能不受牽連,但我臉不紅,心不跳,連報紙也不看,名單也不查,坦然地說:“絕對不可能,我父親是一個清廉的奉公守法的公務員!”我可以毫無慚愧,自自然然打心里說出這話來。
感謝父親,他一向使我對他信心十足,他使我們在家境困難的歲月中,仍然保存著自尊、自愛。他也使我們懂得,窮困家境中長大的孩子,惟一的財富便是自尊心。
他有過許多機會,但他認為尊嚴比金錢物質更重要而不屑一顧,非常地能安貧樂道。
父親的一生都是不阿諛逢迎的,對人好,卻不媚俗。家搬到臺北來以后,假日,廳中常會坐著一兩個高談闊論不請自來的年輕人,父親最多只冷淡地點一下頭;來的次數多了,坐得久了,下班回來的父親有時會板著臉不招呼,常令我尷尬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回,父親對我說:
“好的男孩子,不說太多話。”
他自己就常是輕描淡寫的一兩句。后來,我發現背后罵我的人,便是曾在我家廳中坐的次數最多、話也說得最多的人。父親看人有他自己的一套,只是當時我不覺得,一心想著,這樣板著臉,不太傷人嗎?想起來,慚愧自己的天真:怕傷人,卻傷了自己。
來香港之后,幾回,父親也曾托人替我帶來寒衣,尺寸不差,正好合適,那是他為我設計的。穿在身上,人家總問:在哪兒買的時裝呀?真別致。而我總驕傲地說:爸爸為我設計的。人家再問:你爸爸是做時裝的嗎?不,不是,當然不是,爸爸只是一個學什么,像什么,做什么都要求好的人。他穿衣服別有品味,教我們身上不能多于三個顏色,永遠保持自然與清爽。當我穿上他為我做的衣服,感覺上,不像一個已走出社會的大人,而只是一個小女孩子。但是,已離他太遠了,在離家那段歲月,真正是想念他的,只是,在他的教育下,早已學會了不婆婆媽媽,也一樣地倔強,不肯訴苦。我真正是愛他的,只是,那些年來,早已學會了不去吐露。走在尖沙咀的店鋪中,拿著第一個月的薪水,替他買一只表,但是,金光閃閃的,他舍不得戴;替他買一個打火機,但是他早已戒了煙。一面逛街,一面思量,其實我真是愛他的,而且希望更像他,有他那一身的傲骨與做事的能力,也有他那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的灑脫。我在異鄉中回憶,小時候,他帶我去看電影,一部接一部地看,看到華燈初上,文藝片、西部片,喜劇、悲劇。但他從來沒看過我編過的電影。現在,我也學會一口氣看好幾部電影,幾番悲歡離合都經歷了,卻不能與父親面對面坐下來,說一些我的得意與失意,說一些離家以后在江湖上的事,說一些以前不敢開口問他、不敢告訴他的事。讓他看我像看一個成年的女人。
人來人往的街頭,看到朋友的父親,帶著他成年的女兒親密地走著,每回看得發癡,看得心疼。而香港,曾是父親南來的一個驛站,他也曾在這里奔波過。十多年來,我摸熟了這里的街道,這里的名勝,這里好吃好玩的東西,卻沒有機會陪他舊地重游,也沒有機會帶著他,站在嘈雜的英皇道上,叫他看,對面高樓,突起的一塊天臺,有九盞紅紅的燈,有細細密密下垂的竹簾、灰色的磚墻,那便是我自己搭建起來的王國。我還擁有其他的東西,我的夢在現實中成形了一大半,但我并不快樂,因為他再也看不到了。
父親大殮前,替他清理一些衣物、書籍,想找出一些心愛的東西,讓他帶去,竟找到一封他中風后,用左手寫給我的信,歪歪斜斜的幾行,還沒有寫完。在那樣風雨飄搖的日子里,他仍愛我至深,而我竟不知道!而我寫給他的這一封信,卻未及發出,他再也看不到。其實,我要對他說的話有更多的字數,而且我是從來沒有對他說過的。我實實在在以我父親為榮,我也要他以我為榮。他在不言不語中,教我做一個真正的人,教我憑自己的本事在這個社會上生活,成與敗、好與壞都對自己負責任。父親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也像一些平凡的男人一樣,有過錯誤,有過一些小小的光榮。以我們成長的眼光,重新看他,更了解他,也更愛他。他的一生,雖然已終結,但是,我們子女對他的愛,以及他對我們的愛,將使他永遠活在我們的記憶中。
(選自香港《散文精讀·親情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