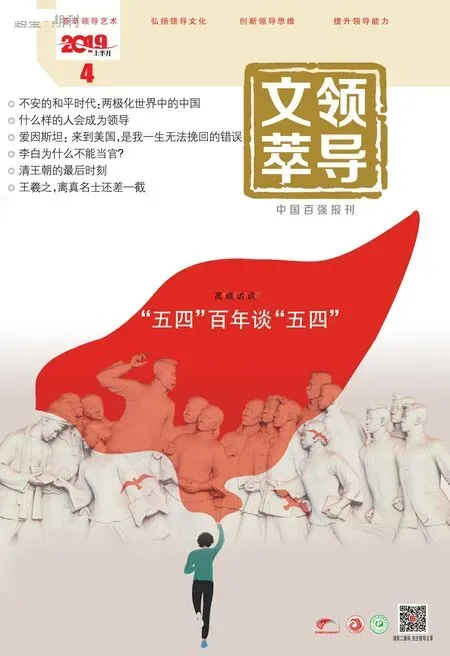黨務干部,你還會說話嗎?
張克文
階級斗爭年代,單位黨委書記作一次報告,可以與所有的員工說話,不管你是青年人、老師傅,是工程師、操作工,一套革命話語系統就可以打遍天下。
可是在今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開始多元化了,不同的年齡段,不同的職業,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黨務干部還想用同一套話語來說話,就會面臨“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尷尬。有時黨務干部與一些白領員工談一個嚴肅的話題,他們都覺得自己那套革命話語很難說得出口,譬如“各條戰線”啊,“戰斗堡壘”啊,等等,于是用一種調侃的方式把它說出來。
面對黨的不同工作對象,黨務干部普遍地覺得自己難以說話。有的同志自嘲地說:“與新社會階層說話,說不上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年青人說話,說不進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這樣,在很多場合,我們的黨務干部處于一種集體失語狀態。
與新社會階層說話,你具備這樣的能力嗎?
聽清華大學一位著名社會學家說過一個真實的故事:北京有一家物業公司與業主委員會鬧矛盾,談判那天,去了七輛奧迪轎車,下來七位西裝革履的白領,進入會議廳后拿出七臺筆記本電腦,一字排開。這架勢就把物業公司鎮住了。業主委員會主任介紹完他的律師、財務顧問、物業管理顧問等后,由他的律師發言。律師拿出有關這次糾紛的法律文本、物業公司的違約依據等,并作了簡潔有力的說明,不到半小時,這場糾紛就全部搞定,物業公司一敗涂地。
我們知道,不少物業公司是傳統房管所的翻牌公司,當他們面對一個全新的社會階層時,覺得有點不知所措。今天,我們的黨組織也將面對這樣的階層,他們有雄厚的資本,有寬闊的視野,有廣泛的社會聯系,有很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和組織能力。特別是他們有文化,善管理,懂法律,面對他們,我們黨務干部怎么說話?
重要的是要擺正位置,與新社會階層相處,你必須承認,你與他的關系是一種合作共事關系。你要承認他的成功,尊重他的事業,學會欣賞他的長處和優勢。他們熟悉的東西,你也要熟悉;他們精通的東西,你也要了解。不要一個經濟政策或市場現象出現了,老總老板們反應很強烈,而我們自己卻木然無知;不要在老總老板講經營講管理滔滔不絕時,我們的黨務干部卻插不上一句話。如果你在他們的企業里工作,你就是最敬業的員工。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去幫助他們,用最快的速度表示你的真誠。
在黨的工作上,如果你要得到新社會階層的支持,要選擇最合適的時機,用最短的時間去說服他們,最好從他們有興趣的話題開始。原則問題不要輕易讓步,遷就不會帶來他們對你的尊重。
周恩來是我們黨杰出的社會活動家,白區斗爭時期能周旋于社會上層,團結了不少民主人士,都憑著他的豐富的學識、資歷和社會關系。周恩來總結白區工作的經驗時,提出要勤學、勤業、勤交友,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借鑒意義。要學會交更多的朋友,社會關系多了,信息知識就多。在社交圈,信息多、學識多的往往處于強勢地位,才可以與地位、聲望比自己高的人打交道。
黨組織在挑選到非公企業開展黨的工作的干部時,也要注意把有一定資歷與社會工作經驗的同志派過去。黨員干部不是天生的強者,只有經歷過艱苦的鍛煉和學習,才有可能成為強者。
與困難群眾說話,你是否了解他們的現狀與過去?
不少同志都感慨,現在老同學已經很難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了。因為在飯桌上說話最多的是老板、領導干部、外企白領,津津樂道于講自己買了什么房,換了什么車,周游了幾個國家。說話最少的是下崗的支邊支疆的同學。他們的人生也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但他們不想說,大家也沒想到要聽。這種場合很少有人說,要學會贊美別人。
今天在開展對困難群眾的工作中,身份的差異是我們與困難群眾不能拉近距離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有的同志米多少錢一斤他不知道,什么時候漲價了,也不知道。所以當街道送給困難戶一袋米,他們拿回去還要秤一下,他就覺得很奇怪。他不知道群眾困難到什么程度。
有的同志不知道下崗工人下崗前曾為企業作出很大貢獻,獲得過許多光榮稱號;也不知道支邊支疆青年的英雄歷史,不知道他們為國家領土完整與統一所作的奉獻。更不能了解他們“走時豪情萬丈,歸來卻是空空的行囊”的體驗。這樣他們與困難群眾說話時,缺少通道,效果當然不好。
有些單位不合理的改制中,一些干部已經成為既得利益者。碰到困難群眾的問題,他們就采取簡單化的方式,對下屬的黨務干部說:“你去給我搞定”,而黨務干部只是對自己的工作對象說些“朋友,幫幫忙”之類的話。有些群眾工作部門甚至還出現了一些“漿糊大師”、“太極高手”,對群眾只出虛招,擺迷魂陣。這樣的人與困難群眾說話,怎么說得下去。
上海凝聚力工程的初創期,曾提出要“了解人,關心人,凝聚人。”其中“了解人”是基礎,群眾有什么困難,為什么會困難,黨組織到底能夠幫助些什么,要搞清楚。這就需要深入困難群眾家庭,傾聽他們的訴說,在了解他們為國家建設、社會發展作出的犧牲中,來了解他們、感受他們。這樣對困難群眾有了感情,說話才可能讓他們聽得進去,做事才可能主動,涉及群眾的利益甚至要據理力爭,也只有這樣,對困難群眾的幫助才可能到位。
與年青人說話,你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嗎?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社會的大變遷和世俗化,使得今天的年青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黨的青年工作來說,主要是在文化層面的。
時代使傳統的成年人對年青人感到陌生了。在成年人看來這是意識形態,是世界觀、人生觀,在一些年青人那兒,這不過是與不同的人們的不同活法有關的一些自由選擇而已。在成年人看來是重要的事情,年青人不屑一顧;成年人推崇的“先進分子”,在年青人那里卻受到質疑和挑戰,他們更看重各個領域的成功者。許多家長對自己的孩子教育失敗了,原因就是他們從來就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黨務干部如果要想與年青人說話,必須了解他們的文化,要了解他們在想什么,喜歡什么,追求什么。譬如,青年文化的表現形式是否就是“酷”文化,它的本質特征是什么,它在顛覆傳統、反抗師長、滿足自我中有何表現特點。我們不是說青年文化都是積極的,但青年人代表著未來,他們中的一部份文化確實也會成為文化發展的一種趨勢。我們應當正視它。
黨務干部如果要與年青人說話,要懂得年青人的語言。現在網絡語言對年青人的語言影響很大,黨務干部不上網,就聽不懂。
從事年青人工作的黨務干部應當多上網,多與年青人在一起,要了解年青人的語言,讀年青人喜歡的書,聽年青人喜歡的歌,在BBS上看看他們在談些什么,也可以參與交談;要研究他們的“酷”文化。毛澤東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同樣,沒有體驗也沒有發言權。因為這不是看幾本青年工作的指導手冊,就能解決問題的。
與老同志說話,你知道他們在思考什么問題?
前個時期地鐵中接連有幾個人跳下去,于是媒體有一篇報道題目叫《自殺流行,禍起黃梅?》,好象自殺是黃梅天引起的。文章最后還說,自殺多可能與人種有關。這樣說話,老同志看了肯定不舒服。因為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任何社會現象的后面,都有它的社會原因。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提綱》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所以人的自殺不能簡單地歸咎于他的自然屬性,而應更注重他的社會屬性。可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許多從事宣傳的同志都不清楚。如果他們要與老同志說話,確實很難。
第二天又有一篇文章,提倡做自殺的干預者,標題卻是《要做一只多管閑事的貓》,老同志如果看到了就更反感了。這樣沉重的話題,居然用這么輕浮的語言說出來。他們會說,這篇文章有對群眾的感情問題。
“三個代表”有個時期我們討論得很熱烈,可是老同志說,最終你們要回答究竟解決了什么問題。老同志不喜歡新概念,他們愛抓住老問題。譬如說,老祖宗不能丟,究竟哪些不能丟,為什么有的已經丟掉了?又譬如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富裕,現在貧富差距反而更大了,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再譬如說,經營者持大股算不算剝削,他們怎么體現作為黨的領導干部的先進性?
老同志很執著,抓住基本問題一定要求講清楚。特別是什么是社會主義。老同志在位的時候,這些問題他們講得清清楚楚,可是今天學習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你以為自己已經搞清楚了,可是,老同志拿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拿出鄧小平文選一比較,認為你并沒有完全講清楚。許多理論問題我們怎么能讓老同志接受,今天的黨的干部應當感到慚愧。現在的干部缺少理論研究的習慣,本來這方面的素養就少,去黨校學習的很多,但真正研究一些理論問題的并不多,這與老同志相比是有差距的。
黨務干部如果真的想與老同志對話的話,應當多學習,多想問題。老同志在位工作的時候,每天都在學習,在他們的床頭柜上都有馬克思主義著作,毛澤東選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還有《支部生活》。今天的黨務干部書房、書櫥可能比老同志的還大,但新書多,反復看被翻舊的很少,他們的床頭柜上可能已經沒有書,如有,也可能是一本金庸的小說。
還有就是思考問題。觀察社會、了解群眾、思考問題過去一直是我們黨務干部的基本功。不要嘴上講著“三個代表”,對周邊的事情不聞不問,這樣的干部,老同志為什么非得聽你說話。
總之,黨務干部說話前要先做好功課,這就是讀書、想問題、交朋友,問題看清楚了,想明白了,你才有資格說話。
(莫新摘自《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