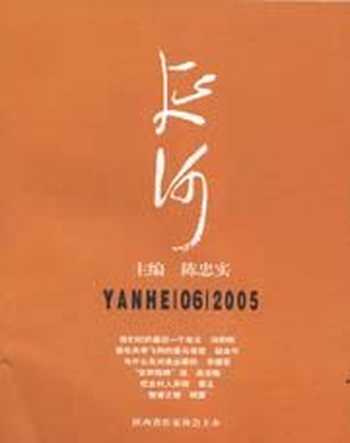追思與懷念
邰尚賢
一、一座豐碑。被人們敬仰的當(dāng)代著名作家王汶石離開我們五年之后,匯集作家,一生作品,近200萬字的四卷《王汶石文集》,終于在2004年12月由陜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
《文集》表明,從1941年創(chuàng)作《畢業(yè)歌》起,一直到1999年,近60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勤苦奮爭,筆耕不輟(“文革”10年除外),鑄就了王汶石在中國當(dāng)代文壇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他的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說,在1954年至2001年的近半個(gè)世紀(jì)中,贏得了如潮般的好評(píng)。僅《文集》附錄所記載的就有茅盾、唐弢、康濯、李希凡、胡采、杜鵬程、閻綱,嚴(yán)家炎、鄭伯奇、肖云儒、曉雷、韋昕、韓望愈等名家在內(nèi)所發(fā)表的170多篇評(píng)論文章;王汶石被譽(yù)稱為“短篇小說大家”,“一代文學(xué)宿將”,“當(dāng)代短篇小說作家中寫農(nóng)村生活的高手”。特別是周揚(yáng)稱譽(yù)王汶石為“中國的契訶夫”。
四卷《文集》,匯集有作家的短篇小說,中篇小說、散文、詩詞、文論、席文、文學(xué)通信,戲劇作品,第四卷是作家《日記》,記載了作家讀書、生活、工作、性格多方面的史實(shí),展現(xiàn)了作家豐富多彩的情感世界。我讀《文集》,深感王汶石是兼融小說、戲劇、詩詞、散文、文論為一體的一位全能式的文學(xué)大師。王汶石說過:“生活就是歷史”。一位作家的《文集》,就是作家的一部生命史,也是一部文學(xué)史。它記錄了時(shí)代風(fēng)云的變幻,也記錄了中國人民走過的歷史足印,更記錄了作家思想、情感、追求的生命軌跡。因此說,作家的人生旅途結(jié)束了,而他的生命繼續(xù)著,這就是他豐盛的作品,就是他厚重的四大卷《文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時(shí)間的流逝是無情的,歷史的變遷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而《文集》的生命力永存,則作家的生命就得到永生!王汶石曾以他的作品鼓舞著一代又一代人生斗爭,《文集》也將激勵(lì)后來人繼續(xù)去奮斗!
《文集》中的許多小說、文章、詩詞、所記錄的恰是中國近、當(dāng)代歷史的極其重要的時(shí)期,這些作品以藝術(shù)的形式把中國近、當(dāng)代史串連起來,使人們記憶猶新,成為今日描述中國的特殊線索,它體現(xiàn)了《王汶石文集》的重要?dú)v史價(jià)值。解讀一位歷史人物是很艱難的事情,解讀一位文學(xué)巨匠就更為艱難。20世紀(jì)已經(jīng)過去,《文集》在21世紀(jì)的解讀,應(yīng)當(dāng)是歷史性的。王汶石以他的生命,為我們鑄就了一座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豐碑!
二、一種“信條”。王汶石說:“寫新人,這是我給自己立下的文藝創(chuàng)作的信條。”因此,作家終生不渝地執(zhí)著地寫新人。為什么?在《文集》卷一的代序中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時(shí)代需要新人”。他說:“在我們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在我們的周圍,依然不缺少那種品格高尚的人。這是一些具有共產(chǎn)主義理想和道德而又肯艱苦實(shí)干的人,正是他們帶領(lǐng)著億萬群眾為共同富裕,建設(shè)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把祖國推向空前繁榮。文學(xué)藝術(shù)有責(zé)任塑造他們的光輝形象,照耀人們的生活道路”。又說:“以我的理解,這也就是主體旋律”。
正是在這樣的一種“信條”的強(qiáng)烈主導(dǎo)下,《文集》所匯集的王汶石的22篇短篇小說,尤其是以《風(fēng)雪之夜》為題集中的小說和中篇小說《黑鳳》所描寫的人,恰恰都是那些閃著時(shí)代光輝的社會(huì)主義普通的勞動(dòng)者。王汶石認(rèn)為這些普通勞動(dòng)者,“是在共產(chǎn)主義理想光輝照耀下翻天覆地,創(chuàng)造新世界的巨人,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感情的海洋比起前人來,不知要深遠(yuǎn)廣大多少倍!”因此,他始終將描寫普通勞動(dòng)者的廣闊情懷和創(chuàng)造精神,作為文學(xué)“新開拓的富饒的疆土”,用他的筆“更加深刻地展示了勞動(dòng)者的精神世界的全部寶藏和無限美。”王汶石小說里的主人公,不論是區(qū)委書記嚴(yán)克勤(《風(fēng)雪之夜》),年輕的賣菜人開平(《賣菜者》),新時(shí)代的大學(xué)生江波(《土屋里的生活》),年過六旬的王大嬸(媽)(《老人》),年輕的創(chuàng)業(yè)者陣大年(《沙灘上》),植棉能手吳淑蘭、張臘月(《新結(jié)識(shí)的伙伴》),還是黑鳳,芒芒、葫蘆、月艷(《黑鳳》)等等,都是普通勞動(dòng)者,他們身上充分體現(xiàn)了社會(huì)主義的農(nóng)民(其他勞動(dòng)者也是一樣)那種淳厚、慷慨、蠻勇、豁達(dá)、堅(jiān)忍不拔、雄奇悲壯、善良溫和、冷峻熱情等優(yōu)秀品質(zhì)和性格特征。我以為,王汶石小說中的人物,有著強(qiáng)烈鮮明的渭河平原人的性格特點(diǎn),有著豐富多彩的渭河平原人民生活的風(fēng)俗和風(fēng)景的畫卷氣質(zhì),這里性格特點(diǎn),也就是這些人物所具有的那種百折不撓的堅(jiān)毅精神和勇往直前的創(chuàng)造力量等等,均被王汶石描寫得生機(jī)勃勃,淋漓盡致,以小見大,展示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民族精神。作家牢牢記住并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描寫社會(huì)主義新人,是社會(huì)主義文學(xué)的“中心和重要任務(wù)”,并且認(rèn)為“這也是社會(huì)主義文學(xué)藝術(shù)的重要規(guī)律之一”。
曾經(jīng)有人質(zhì)疑:王汶石小說中的新人,多為“合作化”、“公社化”、“大躍進(jìn)”時(shí)代的“左”的政策時(shí)期的新人,可信嗎?對(duì)此,作家有明確的解答,他說:這個(gè)時(shí)期的一些口號(hào)和“這個(gè)時(shí)期的一整套設(shè)計(jì)指標(biāo),方針政策,都是一次嚴(yán)重的失誤,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這是領(lǐng)導(dǎo)上的錯(cuò)誤,是決策者的失誤。而廣大勞動(dòng)群眾為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為改變自身的貧窮的處境,為建設(shè)富裕的社會(huì)主義的美好生活,而意氣風(fēng)發(fā),斗志昂揚(yáng)的忘我勞動(dòng)的熱情,到什么時(shí)候,都不應(yīng)受到指責(zé)而應(yīng)當(dāng)?shù)玫奖Wo(hù),珍惜和贊唱的”。他還針對(duì)《黑鳳》的時(shí)代背景深沉地說:“我的心頭,至今還常常活躍著黑鳳姑娘,芒芒、葫蘆及月艷們的身影。我是深深地愛她(他)們的。”我以為,上述的認(rèn)識(shí)和回答,是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性的判斷,也恰恰是王汶石終生執(zhí)著的堅(jiān)持寫新人的創(chuàng)作信條的根本的世界觀!
三、一個(gè)信念。《文集》的字里行間,使我們清晰地看到和理解了王汶石對(duì)黨、對(duì)人民的無限忠誠,對(duì)社會(huì)主義,共產(chǎn)主義理想的堅(jiān)定信仰。1962年他在與青年作家座談時(shí),深情地說:作為一個(gè)文學(xué)工作者,作為一個(gè)作家,“應(yīng)當(dāng)記住總的主題:我們的黨不愧為偉大的黨,我們的國家不愧為偉大的國家,我們的軍隊(duì)不愧為偉大的軍隊(duì),我們的人民不愧為偉大的人民。”因此,要“以堅(jiān)定的信念,無限的熱情,全部的心血,畢生的精力來描寫它,宣揚(yáng)它,是我們責(zé)無旁貸的任務(wù)”。《文集》告訴我們,王汶石這種堅(jiān)定的信念,是在1938年的“白色恐怖”中,在“競中黨組織”的教導(dǎo)下,就已經(jīng)形成了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堅(jiān)定的共主產(chǎn)主義信念,鼓舞著王汶石終生獻(xiàn)身于黨和人民的文學(xué)事業(yè),將文學(xué)作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一種責(zé)任,矢志不渝,奮斗了六十多個(gè)春秋!他忠實(shí)地實(shí)踐著:“一個(gè)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不可能沒有理想。這種理想,在小說中總是通過人物表現(xiàn)出來的。作家總是把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符合他的生活理想的人物,介紹給讀者,用以照耀人們前進(jìn)的道路。”王汶石的理想,信念,同樣充分地體現(xiàn)在他的作品的一系列新人的品格之中。
不論遇到什么挫折和困難,王汶石都堅(jiān)信“在我們的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里,具有共產(chǎn)主義思想品德和性格的人,多如夏夜睛空的繁星:證明共產(chǎn)主義的價(jià)值觀并非像某些人說的是一種烏托邦,而是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真真實(shí)實(shí)的存在,且在日益發(fā)展,波瀾壯闊,終將吸引全人類走向共產(chǎn)主義的明天。不論這個(gè)過程需要多長時(shí)間。”在他古稀之年為朋友、戰(zhàn)友的贈(zèng)詩中,仍然表達(dá)著自己對(duì)人民事業(yè)的堅(jiān)定信念,對(duì)理想追求的執(zhí)著。詩曰:“朝暾年華赴延安/夕照銜山志未閑/忘食廢寢尋常事/只緣理想在遠(yuǎn)邊。”仍然決心“欲向余年鼓剩勇。”為此,王汶石在生命的晚夕之年仍然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文論,詩詞,并且時(shí)時(shí)關(guān)注著中國文學(xué)事業(yè)的發(fā)展。
四、一生追求。《文集》還告訴我們,王汶石把作品的創(chuàng)新、超越,作為自己畢生的,無止境的追求。他說:“作家藝術(shù)家都是在不斷的追求,畢生在追求,追求獨(dú)創(chuàng),追求出新,追求不斷地超越自己,也追求超越別人,追求高水平”。王汶石將這種追求作為他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生命!就是在1985年,他仍然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追求出新,仍是創(chuàng)作界的當(dāng)務(wù)之急”。他曾對(duì)自己發(fā)誓:“將終其一生,用文學(xué)這個(gè)武器,在群眾中堅(jiān)持不懈地傳播共產(chǎn)主義,揭示生活的真理,揭示社會(huì)發(fā)展的必然趨向,提高群眾認(rèn)識(shí)觀察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同時(shí),“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為了實(shí)踐作家的諾言,王汶石永不滿足。他認(rèn)為“作為一個(gè)革命者,一個(gè)革命的文藝家,永遠(yuǎn)不能滿足自己的成績,正是我們應(yīng)有的革命家的本色。”1981年,在王汶石六十歲的時(shí)候,他寫了一首詩,充分表達(dá)了作家的這種心聲。詩曰:“歲逢辛酉滿花甲/半世風(fēng)云何須夸/天白未了雛年志/猶爭一唱醒萬家。”我想,一切有作為的作家藝術(shù)家,都將會(huì)從王汶石的這種永無止境的追求中,汲取力量,奮發(fā)進(jìn)取!
五、一句贈(zèng)言。在1982年2月《延河》召開的青年業(yè)余作者座談會(huì)上,王汶石語重心長地向青年作者贈(zèng)言:“要讀書”。他強(qiáng)調(diào)要“有計(jì)劃地系統(tǒng)讀書。”“如果空有大志而不去刻苦讀書,我們終究還會(huì)是一個(gè)志大才疏的庸人。”作家用自己終生不倦讀書的感受指出:“要使自己變得聰明,有知識(shí),就得讀書。”讀什么?他說,讀馬列、毛主席著作;讀點(diǎn)世界史、中國史;讀點(diǎn)哲學(xu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還要讀古今中外的一些名著;也要讀文藝史。他體會(huì)到,書讀多了,詩讀多了,“寫起小說來也有點(diǎn)詩味”,也會(huì)使小說有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作為不同的人,讀書也要有重點(diǎn),有選擇。他說:“比如,我為了對(duì)俄國作家契訶夫有個(gè)較明晰的了解,就把國內(nèi)已翻譯過來的契訶夫的全部小說,劇本、手扎,評(píng)傳、回憶錄統(tǒng)統(tǒng)找來,集中攻讀,而且其中許多作品,讀過好多遍;同時(shí),還找來一切與契訶夫有關(guān)系的作家藝術(shù)家的著作,如俄國著名演員和導(dǎo)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文學(xué)家丹欽科等人的著作以及有關(guān)高爾基與契訶夫的文字來讀。這樣,我就覺得似乎有點(diǎn)認(rèn)識(shí)契訶夫了,就像熟悉學(xué)校的老師那樣熟悉他了”。至于王汶石如何讀契訶夫的感受,在《文集》的文論,日記中曾反復(fù)描述過多次。我想這不僅是講述了讀書的有效方法,而且針對(duì)當(dāng)前文壇上一些蒼白的作品,只有故事,而無文化的小說的種種弊端,王汶石的贈(zèng)言與忠告,是何等的切中時(shí)弊,發(fā)人深省啊!
1999年,汶石老走的時(shí)候,由于我不在西安,未能為他送行,成為我終生的遺憾,在《王汶石文集》出版之時(shí),我寫下以上粗淺的感受,就作為對(duì)汶石老的一種追思與懷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