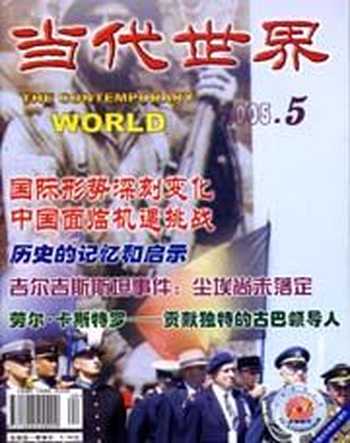歷史的記憶和啟示
李長久
20世紀上半期,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有60多個國家80%的人口被卷入這場戰爭,死亡人數達6700萬,各種經濟損失超過4萬億美元。在二戰期間,被日本軍隊屠殺和作戰犧牲的中國軍民達2000萬人、1500萬人受傷、4200萬人無家可歸;按1973年的匯率計算,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高達5000億美元。
物換星移,二戰結束已經60年,但回憶起來,戰爭的硝煙仍令人心有余悸。今年4月10日,德國政要、各界人士和集中營幸存者共1200多人,在位于德國東部歷史名城魏瑪郊區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遺址廣場上舉行儀式,紀念納粹集中營解放60周年。德國總理施羅德在紀念大會上再次指出:“對納粹主義和其發動的戰爭、種族屠殺及其他暴行的記憶,已經成為我們民族自身認同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我們的一種道義責任。”
歷史的記憶是不該忘卻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對歷史的理性反省,促使德國總理施羅德聲明,德國必須銘記納粹犯下的罪行,不讓悲劇重演。施羅德強調我們不能改變歷史,但可以從我們(德國) “歷史中最羞恥的一頁中學到很多東西。”
歷史是一面鏡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留下的主要啟示:
一、以史為鑒,避免戰爭
1914-1918年,兩大帝國主義集團為重新瓜分世界、爭奪勢力范圍和世界霸權進行了人類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戰敗國德國、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從“一戰”中吸取教訓,時隔20年,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遍及歐洲、亞洲、非洲,以及大西洋、太平洋和地中海。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歐洲戰場結束,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反法西斯國家的勝利而宣告結束。
二戰結束以來,德國政府和主要領導人一直嚴肅對待歷史。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雙膝跪在波蘭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表示“歉疚和懺悔”。
2005年4月10日,德國總理施羅德在講話中說:“過去的歷史我們已無法挽回,但我們能夠從那段歷史中,從我們國家刻骨銘心的那段恥辱中吸取教訓。德國決不向試圖忘卻或不承認那段歷史的任何企圖讓步。”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辛格指出:“德國(歷史教育)可借鑒的東西最多。這里制定了嚴格的法律,禁止極端主義傾向、納粹標志、反猶言論以及任何否認納粹大屠殺的企圖。學校普遍進行納粹大屠殺教育,歷史這一課已經成為德國民族意識的一個組成部分。”
2005年4月13日,德國總理施羅德在柏林與到訪的韓國總統盧武鉉聯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德國的經驗表明,以“審慎和自省”的方式正確對待本國歷史,不僅“不會失去朋友,反而將會贏得朋友”。德國能夠正視本國歷史問題,不僅彌合了與受害國家的心理鴻溝,而且與其他歐洲國家一道,努力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分析德國和日本在對待那場戰爭的不同態度時指出,兩個國家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日本人沒有認罪。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年周前夕,日本出臺重新審定的教科書,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美化侵略、為日本戰犯翻案,引起受害國家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也受到一些媒體的批評。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站發表的評論指出:在二戰結束60年后,日本有關其戰爭歷史的說法仍然激怒了曾被日本占領并遭受日軍暴行、殘殺和細菌戰試驗的亞洲各國。評論指出,為了更加巧妙地掩蓋這個問題,它完全無視證明日本實行占領時犯下滔天罪行的歷史。
韓國廣播電臺2005年4月11日在其中文網站發表題為《日本應正視周邊國家的憂慮》的評論指出,最近東北亞地區掀起了巨大波瀾,原因在于日本明目張膽地歪曲史實,加劇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議,使周邊國家懷疑日本企圖回歸軍國主義。評論希望日本好自為之,切勿重蹈覆轍。日本眾議院就修憲問題發布了最終報告,報告堅持了“和平憲法”第九條規定的“不戰”原則。2005年4月17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日方愿深刻吸取歷史教訓,走和平發展道路。
二、和平共處,協調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到10年,亞洲29個國家的300多位代表聚集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亞非會議,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亞非國家發起和舉辦的國際會議。這次會議達成了處理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其主旨是反帝、反殖、反對強權;堅持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強調團結合作、和平發展。萬隆會議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奠定了主要的思想基礎,是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起點和先導。
二戰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相繼獲得了獨立,但經濟發展仍很不協調、不平衡,廣大發展中國家繼續處在不利地位。據世界銀行統計,2003年,低收入國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數的36.8%,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僅占世界GDP的3%;而高收入國家人口僅占世界人口的15.5%,GDP卻占世界GDP的80.5%。以人均GDP相比,處于貧富兩端、各占世界
20%的富人為窮人相比,1965年,富人為窮人的30倍,1990年擴大到60倍,2000年擴大到70倍以上。窮國獲得世界貿易收入的3%,而富國卻獲得世界貿易利潤的75%。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科技實力相差懸殊,加上制造品和初級產品的“剪刀差”,導致南北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窮人越來越多,即使避免了世界性戰爭,局部地區戰亂仍此起彼伏,并威脅國際社會的安定。只有各國經貿交往公平、互利互惠,各國經濟才能協調發展。
三、聯合國:任重道遠
二戰結束不久,聯合國憲章自1945年10月24日開始生效,宣告聯合國正式成立。聯合國的成立是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根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肩負著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任務。
半個多世紀以來,聯合國成員國已從51個擴大到191個。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和推進非殖民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74年5月1日,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通過的《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中提出:國際社會要“為建立一種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而努力,這種秩序將建立在所有國家的公正、主權平等、互相依賴、共同利益與合作的基礎上,而不管他們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如何,這種秩序將糾正不平等和現存的非正義,并使發達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有可能消除,保證目前一代和將來世世代代在和平與正義中穩步地加速經濟和社會發展”。同年12月12日聯大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強調:“需要加強國際合作以求發展。”
2000年9月6日至8日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通過的《千年宣言》提出:“應確保全球化成為有利于全世界所有人民的積極力量”,各成員國領導人莊嚴重申,決心“通過聯合國努力實現全人類謀求和平、合作與發展的普遍愿望。”但是,聯合國提出的發展戰略、行動綱領和確定的目標基本上都沒有實現。
2005年3月21日,安南秘書長公布的聯合國改革報告,過于強調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和擴大而忽視發展問題,引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注。馬來西亞常駐聯合國代表伊薩代表不結盟運動在聯大會議上發言中指出,不結盟運動對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應是聯大審議的“核心”,但這一要求并沒有在安南的改革報告中得到充分反映。作為77國集團的代表、牙買加常駐聯合國代表內爾指出,現實問題不是讓富國做出新承諾,而是如何落實已經做出的承諾,例如增加國際援助,削減窮國債務和促進資源轉移。阿爾及利亞常駐聯合國代表巴利指出:“聯合國生病了”,需要對癥下藥,“但安南秘書長的報告,以任何標準判斷既不是對癥下藥,也不是眾所期待的靈丹妙藥。”
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涉及各方切身利益,需要各成員國通過廣泛協商達成一致。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強調,從維護聯合國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中方不贊成安理會改革設定時限,更不贊成以強行表決的方式處理尚缺乏廣泛共識的不成熟方案。美國國務卿賴斯的高級顧問赫利說:“希望不要人為地設定期限,要在形成廣泛一致意見的情況下使改革取得進展。”俄羅斯代表也說:“為避免聯合國發生分裂,有必要繼續努力形成廣泛的一致意見。”
絕大多數國家希望,經過深思熟慮、協商一致達成的方案,對聯合國進行改革,才能使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加強合作、促進發展、縮小貧富差距和共同繁榮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做出新的貢獻。
(本文責任編輯:季仰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