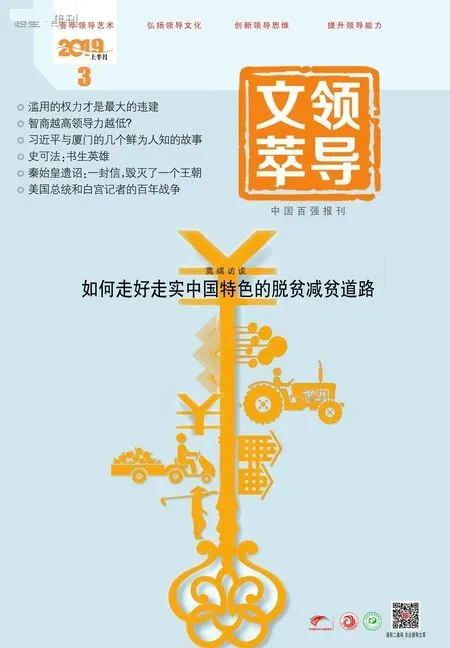西方政府社會管理的實踐及啟示
和經緯 田永賢
西方發達國家在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對社會事務的管理經歷了漫長和復雜的過程。從早期的古典自由主義到凱恩斯主義,再到新古典主義的興起,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在社會事務管理中的作用不一而足,經過了幾次重大的調整。從總體上來看,這些國家在社會事務的管理上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有側重點地進行管理。通過對影響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事項的管理,發達國家實現了其宏觀經濟發展的有序和平穩,在經濟增長和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的同時有效地解決了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社會公平和公正、貧富差距懸殊等問題,并且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與良性互動。這些努力很好地化解了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矛盾,并為其持續發展提供了長久和穩定的動力。
在我國,一直以來并沒有一個準確、全面的“社會管理”概念,對其界定應該充分參考國外的經驗。基于對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事務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的考察,我們認為:第一,發達國家的社會管理主要意指政府力量對獨立于政治、經濟領域之外的那部分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一方面,這種管理提供成其為國家所必需的基本秩序;另一方面,現代政府社會管理的主要方向是為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一個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第二,與公共服務的差別在于:發達國家的社會管理相比較而言帶有更重的“規制”(regulation)色彩。這在發達國家整體“服務型政府”的背景下構成了其剛性但又不可或缺的職能。第三,這里所說的社會管理職能主要由政府來行使,但是越來越多的私營部門和社會團體也開始進入部分社會管理過程。
從實踐上看,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社會管理的具體領域各不相同,各國情況差異明顯,但是綜合梳理發達國家的政府管理實踐,還是可以歸納出這樣一些共同的主要社會管理領域:社會公共安全管理、生態環境管理、就業管理、食品藥品管理、人口管理、社會保障體系管理、社會組織管理、公共交通管理等。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在這些領域的社會管理中實踐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主要的經驗有以下幾點:
第一,較為合理的組織設計。由于發達國家大多有較長的自治傳統,因而在“中央—地方”和“聯邦—州—地方”之間基本不存在嚴格統屬的條塊關系,而是在各自的法定職責范圍內各司其職。發達國家政府在處理社會管理職能的組織設計上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如美國政府的社會管理在聯邦層次上是通過50多個獨立的管制機構煟椋睿洌澹穡澹睿洌澹睿 regulatory agencies犂詞迪值模這50多個社會管理機構的內部設置和下屬分支機構的設置就充分考慮到了管理領域的實際情況和資源預算約束,幾乎沒有統一的組織設計模式。如美國環保局(EPA)在全國設有10個大區,一個區負責若干個州,每個區都根據本區的實際情況制定政策和標準,這種適中的管理幅度既照顧到了各個區域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又不至于出現管理重心過低而帶來的繁重管理任務。
發達國家社會管理機構的設計考慮到了組織整合和權責一致問題。如針對環境管理領域存在的多頭管理、權責不明等問題,1970年成立的美國聯邦環境保護局就對社會的環境管理領域進行了整合,將分散在不同部門的環境管理權由該局統一行使,對環境行使全面管理。
當然,社會管理也是一個牽涉面極廣的領域,由于各種原因,管理機構設置很難歸整到一個部門。對此,美國政府按照管理對象的性質特征,借用組織間流程再造的思想,對幾個管理部門之間的管轄程序和前后銜接做出了比較清晰的設計,如肉制品的生產銷售就涉及到幾個部門。其中,聯邦食品安全和檢查署(FSIS)負責檢查食品制品的加工、操作和包裝;美國農業局(USDA)負責生產廠家衛生、設備、操作的技術標準制定,等等。相關管理部門之間都有法定的或管理實踐中約定俗成的協同規范,很少出現多頭管理、管理真空、扯皮或者“爭著管”等現象,管理效率較高。
第二,分權化的管理取向。權力下放,作為推動民主政治建設、加強經濟發展的一項策略,已成為各國行政改革的主導理念和實踐方向之一,也是發達國家政府社會管理的一個顯著趨勢。隨著理論界對政府間關系(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研究的深入,這一步伐走得更快。在實踐中,基本上以20世紀80年代為坐標,西方主要國家都開始了放權運動。澳大利亞聯邦政府60年代開始曾經追求中央集權的社會管理模式,70年代惠特拉姆政府擴大了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但是其后暴露出許多弊端,后又趨向適度分權,霍克政府時期下放了許多權力,完成“社區參與體制”,這一分權化模式在以后的基廷政府和霍華德政府一直被沿用。
西班牙政府1981年就頒布了自治區條例,對中央與自治區的權限做了明確的劃分,擴大了地方的社會管理權。在這個過程中,發達國家的政府比較注意在向地方下放社會管理權的同時,用中央和地方政府間協議的方式對放權后雙方的職責權限做出明確規定。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也加快了分權化的步伐,明確了國家和地方公共團體的職能分擔,居民身邊的公共事務盡量交由地方處理。而即使在高度中央集權的法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也明確規定市鎮、省、大區和中央政府的職責范圍,取消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監管,授予地方民選機構較大的權力,將地方社會事務的管理權更多地賦予地方民選官員手中。在分權化浪潮下,地方政府在社會管理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權,更有可能對地區內的利益格局進行調整。尤其是在放松管制理念的指導下,地方的經濟社會更具活力,政府的管理績效得到提高。
第三,重視制度建設,完善政府的社會管理運作體制、建立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和合理的利益協調機制。近些年來,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合理的社會分層構建合理的社會結構,使得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各盡所能、各得其所。通過協商、談判、對話等途徑,各階層掌握了其利益訴求的主動權,利益關系能夠不斷得到協調。為了減少社會領域的各種摩擦,西方發達國家試圖建立一個沒有身份歧視,每個社會階層之間相互開放,階層關系融洽,社會流動暢通的開放社會,達到社會的公平和公正。經過長期的發展和完善,西方發達國家在社會管理的各個領域都建立了健全和行之有效的管理體制。如在公共衛生領域,美國建成了包括聯邦——州——地方三級的完善的公共衛生管理體系,聯邦政府的人類服務與衛生部(HHS)承擔主要職責,設計實施了一個廣泛的監視疾病爆發的網絡,將所有醫療機構在因特網上聯網,建立提供疾病信息的網上資料庫,同時向所有醫療保健人員提供培訓和信息,使他們能夠識別有可能是疾病爆發的跡象和癥狀,另外建立了美國應急行動中心電子網絡疾病檢測報告預警系統、大都市癥狀檢測系統、全國公共衛生實驗室快速診斷應急網絡系統等,以確保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作出及時的反應。
第四,社會管理的市場化。20世紀80年代以后,以英國撒切爾政府為首、新西蘭迅速跟進,發達國家大多進行了社會管理的市場化改革,這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民營化。發達國家的民營化最早開始于自然壟斷行業,如郵政、電信、鐵路等部門,而后擴展到一般公共服務。新近的民營化最終進入到了社會管理這一主要以規制為管理方式的政府活動領域,發達國家政府謹慎地將諸如監獄管理、就業指導、消防服務等職能授權給私營部門和第三部門來行使。
社會管理市場化同時也包括在社會管理中注入市場運作的意識。早在里根時代開始,美國政府就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規章都要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的標準,并開始大規模地放松甚至廢除政府管制。英國梅杰政府在1992年發起的“市場檢驗”運動,就是要求地方政府將政府的更多管理活動推向市場,接受市場的檢驗。在社會管理市場化的趨勢下,幾乎達成這樣的共識——在政府與市場之間選擇更多的市場、更少的政府,即使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也是明智的選擇。
第五,較強的社會自主管理能力。發達國家社會管理的一個成功之處就在于運用社會力量進行自主管理。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都有很強的公民社會傳統,社會自治自理能力極強,是名副其實的“大社會”。行業自律組織、社會中介組織、社區乃至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組織都承擔著數量可觀的社會管理職能。
政府與私人以外的第三部門一直是西方社會中重要的一支力量,它們是連接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橋梁,第三部門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它愿意參與政府部分社會管理的功能輸出過程。一些非贏利的第三部門組織以互助友愛為宗旨,一些行業自律組織本身也有社會管理的職能,這些無疑更有利于保持其參與部分政府社會管理過程的持續動力。西方國家深厚的公民社會傳統為第三部門的發展壯大直至參與社會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第六,重視社會監測體系及危機預警系統的構建。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朱力教授指出,敏感的社會預警機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這個監測預警機制要能夠及時發現不和諧因素,并能為政府和民間提供充分的社會運行信息。在實踐中,發達國家建設社會指標體系及社會系統核算的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借鑒。事實上,在西方發達國家,危機管理并不僅僅限于公共安全和公共衛生等特定領域,在幾乎全部的政府社會管理領域,都有危機管理的機制。突發的氣象或生態變化、人口的異常流動、突發的大規模人口流動等等都被定義為公共危機。發達國家處理社會危機主要有制度設計和群眾動員兩方面的經驗。在制度設計上,著重是危機報警、危機處理啟動、危機處理、善后等幾個階段的銜接,各政府部門的角色和職責也被明確界定,而群眾動員方面則主要是危機信息通報和群眾組織問題。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