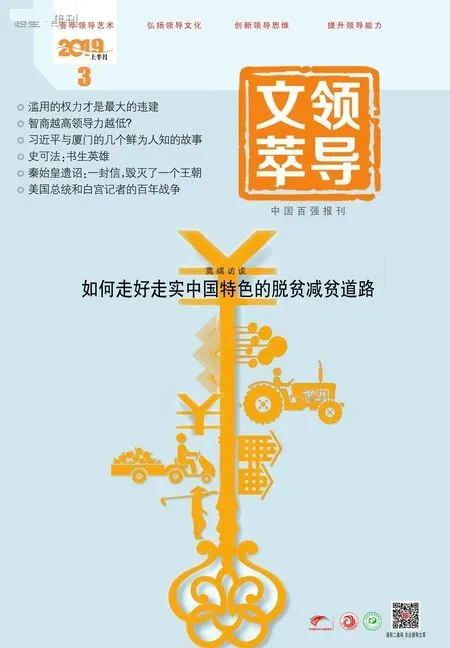官員自殺傳言的社會背景
朱國棟 黃 泓
2月18日10時30分左右,安徽省蚌埠市統計局局長劉敏從自己的辦公地點——蚌埠市政府院內的辦公樓跳下,自殺身亡。
自2003年8月江西上饒市原市委書記余小平自殺以后,被媒體報道的自殺的官員有四川雅安原公安局長、江蘇省射陽廉政辦公室主任、湖南省衡東縣教育局長、原吉林省公路建設局局長等。而2005年以來,先后又有河南省新鄭市市長、甘肅涇川縣縣長自殺事件被報道。
“官員自殺”已經成為一種不容忽視的社會現象。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丁淦林認為,“官員自殺”引起廣泛關注,是出于官員身份的特殊性和政府本身的公共性。
“精神焦慮癥”
劉敏跳樓后,當地公安部門立即控制了現場,并將統計局的工作人員叫到一起,進行了詳細詢問與調查。
2005年2月20日,也就是劉敏自殺的兩天之后,蚌埠市公安局公布了調查結果:劉敏墜樓身亡的原因系“精神焦慮癥”。蚌埠市公安局的這一說法也得到了劉敏周圍一些同事和親友的證實。
安徽一家媒體駐蚌埠的記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2005年初當地電視臺的一個宣傳節目中,“劉局長給人的感覺就是沒有精神,講話完全照本宣科。”
一位和劉敏在政府機關大院共事10多年的干部,也認為劉敏最近有點不大對勁,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有一次我在蚌埠街頭遇到劉局長,感覺他氣色很差,當時我跟他打了個招呼,他居然愣在那里,過了一會兒居然問我是誰。”
劉敏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蚌埠市物價系統工作,從普通干事做到物價局副局長,曾先后多次獲得過全國、全省級別的榮譽。作為蚌埠市政壇的知名人物,劉敏墜樓身亡之后,關于劉敏為什么會得“精神焦慮癥”,民間形成了多種說法。
流傳最多的說法是“腐敗說”——劉敏可能涉嫌腐敗,當地紀委對他已介入調查,造成他精神上的抑郁不振。但這種說法很快遭到反駁。
蚌埠市委宣傳部新聞辦副主任祁學信表示,這種說法是“無稽之談”。蚌埠市紀委則拒絕接受采訪。
“老實做人寬厚處世英名永存,勤懇敬業忠于職守風范長駐”,這是劉敏追悼會的挽聯,而訃告對劉敏的評價是:“劉敏同志忠于黨,忠于人民,工作認真負責,恪盡職守,勤勉廉潔,團結同志,為我市經濟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官方對劉敏的蓋棺定論也否定了“腐敗說”。
另外一種說法則把劉敏的精神焦慮癥與其在統計局的工作聯系起來。就在劉敏自殺身亡前夕,蚌埠市的經濟數據創造了奇跡。
據蚌埠市提供的公開資料,2003年,蚌埠市地區生產總值增長6.4%。而在蚌埠市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制定了“3461”計劃,該計劃的第一個目標就是“2003年至2007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左右,到2007年突破300億元”。6.4%的增長數字顯然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而2005年1月,蚌埠公布的蚌埠市2004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數據飆升到了16.5%,預計達到260.99億元。另外,該市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在2004年增長了32.5%,是全國平均速度的三倍以上,農林牧漁業增加值增長為35%,而全國的第一產業發展速度近年來一直在5%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劉敏自殺之前,蚌埠民間就流傳著“統計局長難當”的說法。劉敏的前任任期也不長。
對于把劉敏自殺與當地經濟數據激增聯系起來,蚌埠市委宣傳部新聞辦副主任祁學信也以“無稽之談”給予回應。
關于“腐敗”的集體無意識
劉敏的焦慮癥,究竟是因為腐敗還是因為虛高的數字,或是其他原因,都無法得到證實。
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記者隨機采訪的幾個人中,他們對官員自殺的第一反應,通常是認為與腐敗有關。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張濤甫是安徽人,對于統計局長由于“數字虛高”而引起焦慮從而自殺的說法,他表示不太可信——在官場浸淫了這么多年的人,一般情況下應該可以承受這種壓力。他從而判斷,自殺可能因為腐敗。
在上海市司法局新聞辦工作的馮鉉,也與張濤甫持近似觀點。
近年來,官員自殺事件被頻頻報道,香港《文匯報》曾引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邵道生提供的一個數據是:2003年上半年,中國有1252名黨員干部自殺。
官員自殺,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涉及腐敗——已經被審查或自知難逃被審查的命運。比如余小平,江西省紀委的結論是:“身為黨員領導干部,道德品質敗壞,生活作風糜爛,最終自絕于黨和人民,所作所為性質惡劣,影響極壞。”
也有官員的死最后被定論為因病自殺。比如,四川雅安市公安局原局長李海自殺,結論是“因為病痛折磨,對戰勝疾病、搞好工作缺乏信心,心理素質脆弱”。江蘇省射陽縣廉政辦公室主任王勇自殺,被公安部門鑒定為“患抑郁病癥”。
但是不管官方結論如何,輿論總是難免把官員自殺與腐敗相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邵道生就公開對媒體表示:“我的看法,對位高權重的官員自殺,不能混同于普通人的自殺,恐怕他們的自殺與整個社會反腐敗的‘大氣候有關。”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丁淦林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分析說,在腐敗成為一種默認值時,官員一出事,對官員的道德懷疑幾乎成為公眾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他認為,知情權是信息社會中人們最基本的渴求,官員的死之所以遭到集體無意識懷疑,很大程度上是籠罩在“官員之死”中的神秘色彩被人為地模糊化所致。
在江西上饒原市委書記余小平自殺事件發生一年之后,“自殺報告”才姍姍來遲,官方對四川雅安市公安局原局長李海自殺原因的解釋也被質疑:一個干了20余年的老公安,經歷過的風風雨雨不可能少,為什么到了新地方才一個月就“心理素質脆弱”。
“對官員之死的懷疑,如果還有別的原因,那就是中國傳統宣傳模式中的慣性所至。”丁淦林說,中國傳統的宣傳模式中,輕言自殺是被人唾棄的,尤其是共產黨員,他們不怕死,更不輕言死,輕易結束生命至少是對黨的事業不夠忠誠。現在,在“腐敗”一詞為大多數人熟知的今天,媒體以及公眾把這個詞加載在他們得不到充分信息的“官員自殺”事件上,不可避免。
“官員之死”與“普通人之死”
在全國反腐敗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官員自殺引起的“興趣點”往往也集中在這些官員的行政級別,以及這些官員之死身后的腐敗故事。
公眾鮮有以人本的心態、以對待普通人的態度來理解官員之死。2003年,香港特區警務處助理處長張之琛跳樓自殺,很多媒體從臨床心理學方面解釋了原因。反觀對內地官員自殺的報道,不能不引人深思。
同樣是官員自殺,為什么關注點不一樣?公眾的反映也不一樣?上海交通大學政治學專業教師謝岳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分析了原因。他說,當前,不少官員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道德意識蛻變,官德坍塌。公眾對官員自殺的疑問,集中反映了對官員的道德形象的疑問。而香港公務員自殺沒有引起公眾的疑慮,相反從心理學方面得到了純人本化的解釋,一方面說明了香港公務員在市民心目中的道德形象令人滿意,另一方面說明官員得到了公眾的認可和理解。
在生活節奏日益加快的今天,焦慮癥的病歷至少并不是件令人吃驚的事情,可面對官員之死,公眾卻眾口一詞說“腐敗”,這絕對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謝岳說,只有等官員的道德形象在公眾心目中得到充分正視,官員的自殺才會被作為一個平常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