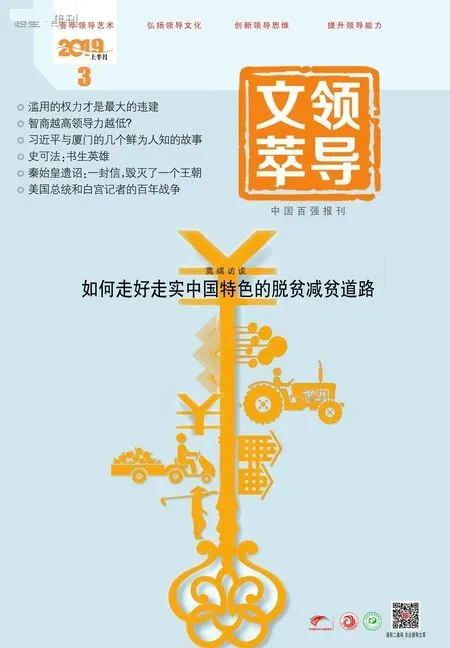蘇式軍事體系不行?
戴 旭
如果說1991年的海灣戰爭像是一場國際玩笑,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已經讓人笑不出來。
兩場戰爭的結果和過程都極像一場缺少刺激的、不公正的拳擊賽:還是那個重量級拳王和那個勢單力薄的孺子,還是當年的場地、當年的結果——一個回合比賽結束。不同的是,前者是亂拳擊倒對手,而后者卻是一拳擊斃對手。甚至連“觀眾”的心態都是一樣的:先是滿懷好奇和期待,最后大失所望一哄而散。
盡管如此,我們卻無法真正地忘掉它。
俄羅斯軍事家斯里普琴科在《超越核戰爭》一書中評價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說:“伊拉克非常認真地準備了一場過去的戰爭。”
到了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世界看到伊拉克準備的是一場什么戰爭呢?
日漸顯露的差距
凝視伊拉克戰爭的廢墟,筆者的眼前浮現出一幕幕似曾相識的場景:敘利亞貝卡谷地、利比亞首都、南聯盟、阿富汗……
人們不難發現,這些昔日的戰地和廢墟有著更加驚人相似的地方:都是蘇聯的盟友或涉足之地,都是主要采用蘇式武器系統和軍事思想,都在美國新軍事理論和信息化空中打擊的掃蕩下,或支離破碎或灰飛煙滅。
為什么?
兩次海灣戰爭讓我們看到同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伊拉克是一個陸海空三軍全面“蘇”化的國家。從“飛毛腿”地對地導彈、薩姆系列防空導彈、蘇式或米格戰機、武裝直升機、各種雷達系統,到主戰坦克、火炮、輕武器,絕大多數是蘇(俄)制,不僅數量龐大,比較先進,而且成系列引進,不僅引進裝備,也引進體制和思想。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04年4月16日有一篇報道說“在伊拉克戰爭中,薩達姆領導的伊軍幾乎沒有進行過什么像樣的抵抗便潰不成軍,這讓俄羅斯備感震驚。現在,俄羅斯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反思俄的軍事體制,據說相關的改革也將提上日程。”
當美國準備大打伊拉克戰爭的時候,俄羅斯的一些軍事專家曾警告說,美國軍隊會在巷戰中遭受重創。然而,20多天的戰事進展證明,美國迅速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俄前國防部官員維塔利·什雷科夫指出,可以說,伊拉克軍隊就是按照俄羅斯軍隊的模式建立起來的,沒想到在這場戰爭中會潰敗得這么快。
俄羅斯的軍事指揮家們在震驚的同時,也開始對自身傳統的軍事體制進行反思。包括什雷科夫在內的俄羅斯軍事專家和政府官員們都認為,蘇聯解體十幾年來,俄羅斯社會唯一沒有改革的就是軍事體制。俄羅斯120萬人軍隊的組織結構、武器裝備以及軍事理論等仍然是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
俄羅斯意識到,在當今世界,除美國外,沒有第二個國家或地區具有進行這種信息化戰爭的全面綜合能力。而它的落后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代差”的地步。這種“代差”不是一個早晨醒來突然發現的,當然也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而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美蘇軍事賽跑的結果。
問題出在“信息差”上
二戰時,應該說美蘇雙方的武器系統是在一個水平線上。朝鮮戰爭中,蘇聯的米格—15的性能甚至超過了美制的F—84和F—86。正是這種性能上的優勢,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當時中朝空軍在技術和訓練上的不足。
20世紀60年代,蘇制的米格—21曾是越南戰場上美國F—4“鬼怪”戰斗機的強有力的對手,而蘇制薩姆—2曾是美國B—52的噩夢。
上世紀70年代的中東戰爭依然是美蘇武器系統和作戰思想的較量。雖然蘇式軍事體系的機械呆板初露端倪,但薩姆—6導彈的表現卻震驚了世界,以至于當時世界軍火商的廣告詞這樣說:“薩姆,薩姆,飛機的克星!”
20世紀80年代,蘇聯在和美國的全面對峙中已漸露疲態。美國挾電子革命的強勢,使主戰武器全面升級換代,同時建成功能強大的指揮自動化系統,而蘇聯卻心有余力不足,只能在部分武器平臺上作頑強的追趕。發生在貝卡谷地的戰斗被稱為“空襲革命”。以色列依靠電子優勢,6分鐘之內就全殲了曾在第4次中東戰爭中大出風頭的19個薩姆—6導彈連。世界在震驚之余,也不由得感到,昔日強大的蘇聯軍事帝國已不復存在。
今天,俄羅斯引以自豪的武器平臺中,如蘇—27、蘇—30、米格—29戰機和T—90坦克、大型水面戰艦等,無一不是機械性能優良,而電子系統落后。而且這還只是個別的平臺。如果從整個C4ISR系統的角度看,俄羅斯的差距更大。未來戰爭是體系對體系的對抗。在體系的優勢面前,平臺的優勢幾乎無法體現。科索沃戰爭中,南聯盟空軍司令駕駛并不落后的米格—29上天,還沒有發現敵機,即被擊碎在空中。
俄羅斯由于實力的削弱、國防軍工科研體系的瓦解,短期內已難以形成應對信息化常規戰爭的整體能力。這也是美國在此次戰爭期間對俄羅斯如此藐視的根本原因。美軍敢于毫無顧忌地攻擊俄外交車隊,反映出的就是這樣一種美國心態。
俄美軍事技術與戰爭理念的這種差距在兩場類似的戰爭中表現得最直接也最明顯。一場是由美國在阿富汗進行的,一場是由俄羅斯在本國內的車臣進行的,都是反恐作戰,戰場均為中亞地區的山地,對手都是游擊武裝。但是,美國只進行了61天,22個人傷亡就解決了對手,而俄羅斯從1999年8月一2002年5月,已死亡2500人,負傷6000人,特種部隊還有230多名官兵陣亡。前后兩次車臣戰爭,俄軍傷亡10萬人以上,而至今仍未徹底解決車臣恐怖分子。
美軍擁有及時、準確、全面的戰場感知能力、信息獲取能力與信息交換能力,從而實現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和偵察與作戰平臺一體化。美軍從傳感器發現目標到作戰平臺實施精確打擊的時間由海灣戰爭的幾天,到科索沃戰爭的幾小時,再到阿富汗戰爭的10分鐘,初步形成“發現即摧毀”的信息化作戰模式。如2001年11月間,美軍一架“捕食者”無人偵察機發現一支車隊,在夜幕掩護下撤離喀布爾,立即通過衛星傳送到美國中央指揮中心。五角大樓立即下達攻擊命令。3架F—15戰斗機在“捕食者”引導下,很快飛到目標上空,即刻投下3枚各重1.13噸的制導炸彈。同時,無人偵察機也向地面停車場上的車輛發射了“海爾法”反坦克導彈,并命中目標,從而成為世界上第一架無人攻擊機。后經證實,包括本·拉登的助手阿提夫在內的近100名塔利班人員在此次空襲中喪命。
在車臣戰爭中,俄軍由于缺乏現代化的偵察與通信手段,無法及時發現車臣匪幫,即使發現也不能將情報即時傳輸到作戰部隊,從而貽誤戰機。和美軍追殺阿提夫的一幕恰成對照,在車臣戰爭中也有這樣一個鏡頭:俄軍一支空降分隊在山區陷入車匪重圍之中。由于聯絡中斷,指揮部無法查明該分隊的具體位置,致使90名官兵苦戰3晝夜而得不到支援,最終全部犧牲。
車臣戰爭與阿富汗戰爭最大的區別在于,俄軍打的是機械化戰爭,而美軍打的是一場已具雛形的信息化戰爭。俄軍使用的武器裝備是各種常規作戰平臺,主力是以10萬人的陸軍為主的作戰集團,采用大規模的步坦協同或空地協同作戰及分割包圍式的戰役合圍,幾乎是二戰時期機械化戰爭的翻版。而美軍則是以導彈對子彈,以衛星對準星。
亟待彌補的代差
曾以《大趨勢》聞名世界的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說:在新的戰爭形式正在崛起之時,舊的戰爭形式還不可能完全消失,就像信息時代雖然正在到來,工業時代還沒有消失一樣。至今還有大約20個國家擁有對本地區影響很大的工業時代的軍事力量。至少在未來的沖突中,有些國家仍派步兵前往作戰,為國捐軀。只要那些貧困落后、憤怒不滿的國家的軍火庫里還充斥著低技術水平、低精確度的武器、愚笨型而非智能型的坦克和大炮,那么,所有工業時代的作戰方式和武器,包括挖戰壕、建地堡、人海戰術、肉搏戰等,都將毫無疑問地被繼續開發利用下去。
但隨著世界從工業時代跨入一個新的世界,這種傳統的戰爭和反戰爭的知識已十分危險地過時了。
自蘇聯解體后俄軍進行了10年的大范圍改革,這10年也是美軍軍事急劇變革和躍升的時期。軍事上的差距,其實是經濟和社會差距的縮影。可以預期,在整體實力落后的情況下,俄與美的軍事差距可能進一步拉大,甚至會落在歐洲和日本的后面。
俄羅斯尚且如此,那些以蘇(俄)式武器體系裝備和信奉蘇(俄)式軍事戰略指導思想的國家,其軍事危機感可想而知。一些軍事專家評論說,伊拉克戰爭之后,世界又將掀起一場新的整軍運動。作為和伊拉克軍事狀況非常類似的敘利亞、埃及、越南、古巴、朝鮮、印度等蘇式軍事體系影響深厚的國家面對伊拉克的廢墟,應該徹底地警醒了。
蘇式軍事體系的核心是以地面力量地面作戰為基本思維的出發點。受蘇聯大陸軍主義的影響,這些國家不約而同地在軍隊編成中保留著龐大的陸軍。然而,此次伊拉克戰爭,美國陸軍回避對抗,無仗可打;伊拉克陸軍不敢對抗,不戰自潰。一攻一防,陸軍的表現為其在未來信息化戰爭中的作用作了準確的定位。痛苦的、脫胎換骨的改造或重建是這些國家軍隊唯一的出路。
目前,由于美國在軍事力量領域中的這種不對稱軍力,其鷹派政客已產生了一種近似狂妄的技術和戰爭迷信。美國學者將美國比作一輛正在向山下沖去的、剎車失靈的戰車。伊拉克戰爭已成歷史,但2003年的春天讓整個地球的人們都感到一種世紀的寒意。比利時首相最近說,美國已經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超級大國。因為美國的危險,世界也危險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