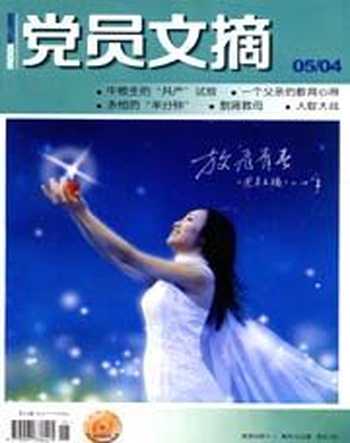牛根生的“共產”試驗
邊 杰

2005年伊始,在呼和浩特市郊區的一棟有1000多平方米的氣派的別墅里,來自全國各地的記者紛紛前來探訪,這間別墅的主人為什么要做出那么“前無古人”的舉動。
別墅的主人叫牛根生,現年49歲、氣色紅潤、身體不錯的他有著“億萬富翁”的名號,他創立的“蒙牛”品牌全國知名,一年有數十億元的銷售收入,其公司也在香港成功上市。然而,2004年底,牛根生卻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捐出他在蒙牛的股份。
“散財”
2003年12月底的一天,牛根生在和一干人討論完蒙牛上市的事情后,突然把律師叫到一邊,告訴律師自己要把蒙牛的股份捐獻出來,原則是“不能繼承,下代人不能享用”,讓律師去做一個方案出來。律師聽后非常激動,說:“這哪能,怎么能做這種事情?是在開玩笑吧?”
牛根生的妻子知道這個消息后,也和律師一樣感到不可理解:“當時挺震驚的。以前窮,什么也沒有,好不容易到現在了,卻什么都不給孩子留,全捐出來了。”
這個消息也很快在牛根生的周圍擴散開來……
“我有一個特點,過去我作出什么決定,雖然大家當時不理解,但后來證明是正確的。所謂生帶不來死帶不走,這我看得很清楚。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任何人都少不了這一步。你看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這些偉大的人物,都是支配過幾萬億、幾十萬億財富的,但是這些人去世的時候一分錢也沒拿走。”牛根生向那些不理解自己動機的人解釋。
最不好做的是家人的工作,一般人在情理上都一下子難以接受。牛根生跟妻子講,不能留給子女太多財富,那會“壞了他們”,“我活著的時候他們的生活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我離開了人世,他生活有問題了,是他自己的事情”。最終,家人都同意放棄股份的繼承,一家人分別在法律文書上簽了字,同意捐獻出牛根生持有的全部蒙牛股份,成立“老牛基金會”。
牛根生對“老牛基金會”的安排是:第一步,在他有生之年,其在蒙牛的股權分紅的51%放入基金會,49%留作家庭生活所需,至于他在蒙牛持有的近10%的股份,誰接任董事長,就轉交給誰;第二步,在他天年之后,其所擁有的蒙牛股份全部捐給“老牛基金會”,家人只可領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平均工資的月生活費。
2004年12月,“老牛基金會”在呼和浩特注冊。成員除牛根生之外,還有政府官員、蒙牛中層領導等共60多人。目前主要資金是牛根生2003年股紅的51%,大概有300多萬元人民幣。
對于牛根生這種“散財”行為,人們試圖從他以前的行為中找到答案,這其中流傳比較廣的故事有:在伊利任職期間,公司給錢讓他買一部好車,但他卻買了五輛,讓部下一人一輛;他還多次把自己的年薪分給部下,他曾將自己的108萬元年薪分給了大家,而他在蒙牛的分紅也大部分用作獎勵員工和經銷商;2002年初,蒙牛很多上層領導都坐上了“奔馳”車,而牛根生卻只坐“奧迪”;地方政府以貢獻突出的名義獎給他一輛100多萬元的“凌志”車,他馬上轉手送給了副董事長……
牛根生也愿意提到自己的這些“散財”故事。他說自己堅守“財散人聚,財聚人散”的哲學:“舍得,舍得,舍了就有得。如果你有一個億放在家里,遲早會被人偷,但如果放在朋友家里,一人一塊錢,根本丟不了。”1999年他從伊利出來創業時,在一無奶源二無工廠三無市場的情況下,“沒有過去的散財,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時間里聚集到三四百名有15年以上經驗的乳業專門人才,取得現在的成績。”牛根生據此來印證自己“散財”的善報。
“共產”理想
中國經濟這些年的快速發展,成就了很多人,牛根生就是其中的一個傳奇。牛根生小時候因為家里窮被賣到了一戶牛姓人家,當2004年6月蒙牛乳業在香港上市的時候,牛根生身價1.35億美元,《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把他排在第107位。不過,牛根生說那是“紙上財富”,因為股票目前并不能套現,而且股價也隨時在變化中。
牛根生目前的收入除了每年五六十萬元的年薪外,還有四五百萬元的分紅。牛根生一家現在住的別墅是貸款買的,實際上也是作為摩根等股東的會所,召開股東大會的時候,這里就成了客房。
這位“億萬富翁”對自己生活的要求很低。牛根生吃飯很簡單,常常是面條、饅頭湊合了事,晚上常打打乒乓球,冬日的早上,則在小區內的河里滑一會兒冰。
牛根生生活的種種細節似乎向外人表明,這是一個對物質要求不高的人。不過,即使牛根生這般,也飽受“仇富”輿論的壓力。除此之外,就像大多數名聲在外的富人一樣,牛根生也有財富安全的壓力。
“我既做過窮人,也當過六個月的紙上富翁,我感覺還不如回到窮人。這兩天我發現老婆孩子都比以前快樂,同學、朋友之間交往也真實了。以前老感覺和別人的交往都是虛假的。家庭成員再也不用承擔紙上富翁的壓力了,如果有人綁架,知道現在我沒有錢,也就沒有綁架的價值了。”牛根生坦言無錢一身輕的快樂。
但“散財”不僅僅是為此,“老牛基金會”寄托著牛根生更大的夢想。他說自己的捐贈是一種“共產主義”,“共產是我的理想,跟大家分享成績、成果和收益的時候是最快樂的。這樣也可以讓企業活得更長,一百年后大家還能想起我老牛——蒙牛的創始人”。
牛根生的設計是,把“老牛基金會”所積累的基金用于獎勵對蒙牛發展有貢獻的人員,同時也作為未來董事長的一個支配權,牛根生希望基金會能成為蒙牛成為百年老店的一個助力劑。在牛根生百年之后,“老牛基金會”將自動更名為“牛根生基金會”。
出于社會輿論、財富安全和企業的長久之道等諸因素考慮,牛根生作出了“共產”的安排——這其中隱藏著一個商人的近憂遠慮。
這情形讓人想起180多年前的一個英國人羅伯特·歐文,他當時的身份和牛根生一樣,是一家2000多人的大紗廠的股東兼總經理。歐文企圖發現一種方法,既有利于工人又有利于企業主,他采取了縮短工時、提高工資、改善住宿條件等辦法,果然有效,工人的福利改善了,股東也獲得了更高的回報。當然,歐文的理想并不在一個企業身上,他夢想著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1825年,歐文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新哈姆尼買下三萬英畝土地,建設起“共產主義公社”。接著他又在紐約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納州其他地方,建立了18個公社。但在當時的社會壓力下,三年后,羅伯特·歐文的共產理想徹底破滅了。
和歐文一樣的是,牛根生也為員工修建了漂亮的小區,員工的待遇和股東的回報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歐文不一樣的是,牛根生“共產”的目的并不是想改造一個社會,只是希望建立一種能使自己的名字和一個品牌不朽的制度。但對于這家只有六年歷史的企業來說,未來要面臨市場變化、人才更替、政策環境變化等諸多因素,牛根生的“共產”試驗能實現嗎?
(摘自《中國企業家》 本刊有刪節 攝影:史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