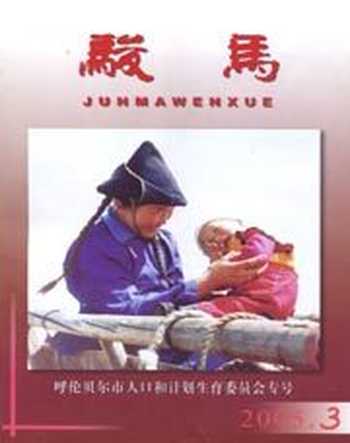馬背上的計劃生育助理員
冬 至
現(xiàn)已退休的敖德巴拉女士在號稱“天下第一難”的計劃生育工作崗位上一干就是十多年,作為計劃生育助理員,她走遍了3500多平方公里的鄂溫克旗錫尼河?xùn)|蘇木,將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獻(xiàn)給了這片滋養(yǎng)著她的草原。由于她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業(yè)績。她先后被評為旗、市、自治區(qū)級先進(jìn)工作者;1995年被評為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勞動模范;1997年被中華全國總工會授予“五一”勞動獎?wù)拢?998年獲得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授予的“全國計劃生育優(yōu)秀工作者”稱號。
當(dāng)我第一次見到敖德巴拉時,我?guī)缀醪桓蚁嘈潘褪俏衣犝f的那個被稱為“草原女英雄”的優(yōu)秀計劃生育工作者。她個子不高,像草原上的所有牧民一樣淳樸,一點也沒有想象中的所謂“女強人”的感覺。通過鄂溫克旗人口計生局的同志介紹才得知,她雖然從小生活在鄂溫克草原,她的戶口上民族一欄填寫的也是鄂溫克族,但她其實是一個上海人。
敖德巴拉的不平常的經(jīng)歷還要從上世紀(jì)六十年代說起。1959年,新中國正處在一個特定的困難時期。當(dāng)時上海、江蘇等地幾十個育嬰院里,好多孤兒因為缺乏食品而營養(yǎng)不良,正在遭受著疾病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脅,急需人們伸出援助之手。剛出生不久的敖德巴拉,就是這三千孤兒中的一員。為了這些孩子能夠健康地成長,康克清大姐在北京專門找到了時任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黨委書記兼人民委員會主席的烏蘭夫同志,還請示了周總理,商談將三千孤兒轉(zhuǎn)到內(nèi)蒙古來,交由當(dāng)?shù)啬撩駬狃B(yǎng)。這樣既增加了牧區(qū)人口,又增進(jìn)了民族感情。烏蘭夫同志馬上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工作方案。經(jīng)過緊張準(zhǔn)備,1960年初內(nèi)蒙古開始了孤兒的接收和安置工作。
1960年初,生于1959年11月的敖德巴拉和其他三百名小伙伴來到了呼倫貝爾大草原,暫時被安置在呼倫貝爾盟人民醫(yī)院育嬰院,當(dāng)時她只有三個月大,尚在襁褓之中。在這里,孩子們得到了阿姨們母親般的照顧,也正是在這里,負(fù)責(zé)照顧她的蒙古族阿姨給她取了敖德巴拉這個名字。“敖德巴拉”的漢語意為“菊花”。這個名字寄托了阿姨熱切的希望,希望她和所有的孩子都能像草原上盛開的花兒一樣茁壯地成長,在草原上扎下堅實的根。
1961年7月,三歲大的敖德巴拉和其他十一個孩子被送到了鄂溫克族自治旗,安排由當(dāng)?shù)啬撩袷震B(yǎng)。當(dāng)時任汗烏拉嘎查黨支部書記的鄂溫克族牧民高力根和他的妻子南斯勒瑪領(lǐng)養(yǎng)了敖德巴拉。敖德巴拉從此有了自己的家。那時,高力根和南斯勒瑪剛剛結(jié)婚十一個月,他們以草原般遼闊的胸懷接納了敖德巴拉,像愛護(hù)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hù)這個嬌小可愛的女兒。在他們心中,敖德巴拉就是他們的親生女兒。
寬廣博大的鄂溫克草原是那樣的寬厚和包容,這里可以孕育和滋養(yǎng)生命,但任何生命都要經(jīng)受草原的錘煉,只有能經(jīng)受住草原考驗的人,草原才算真正接納了他。敖德巴拉在草原上像其他牧民的孩子一樣成長起來了,她和他們一起蹣跚學(xué)步,學(xué)會叫爸爸媽媽,學(xué)會幫助母親干各種家務(wù)活兒,學(xué)會放牧牛羊。在她5歲那年,她不慎碰傷了右小腿;當(dāng)時草原上醫(yī)療條件有限,她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傷處變得紅腫,而且開始化膿。女兒的腿讓父親高力根變得憂愁起來,他帶著女兒四處尋醫(yī)問藥。在哈爾濱市醫(yī)院高力根得到了一個讓他震驚的結(jié)果:敖德巴拉得了骨結(jié)核。女兒的病簡直是當(dāng)頭一棒,高力根夫婦被殘酷的現(xiàn)實給弄懵了。他們怎么也不敢相信,活潑可愛的女兒怎么會得這種病呢?因為他們知道,以當(dāng)時的醫(yī)療水平,這種病很難根治。醫(yī)生說,治這種病必須截肢,否則無法治愈。高力根當(dāng)然不能同意。他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他絕對不能讓自己的女兒變成殘疾人,他要她像其他孩子一樣歡快地在草原上奔跑,他要她騎著馬和他一同放牧家里的牛羊。
接下來的幾年,高力根一家開始了漫長的治病之路,他們賣掉了家里值錢的東西,甚至包括他心愛的雕花的馬鞍。他們?nèi)チ松虾!⒈本⑻旖颍麄冏吡艘患矣忠患裔t(yī)院,他們嘗試了西藥、蒙藥、中藥,但敖德巴拉的傷口仍然不斷地流膿。整整七年過去了,他們一直在與疾病頑強地斗爭著。敖德巴拉已經(jīng)長到十三歲了。也許是他們一家人的虔誠和頑強感動了上天,敖德巴拉的骨結(jié)核病竟然奇跡般地痊愈了。他們一家人心里豁然開朗,感覺陽光又明媚起來,草原上的牧草似乎也比以前更綠了。稚嫩的心最明白,這是爸爸媽媽精心照顧的結(jié)果,她記住了爸爸媽媽海一樣的恩情。
童年這段苦難的經(jīng)歷是敖德巴拉很少提及的,一想起那些往事,她心里都會很難受。可正是由于這段治病的經(jīng)歷,她和父母通過情感的臍帶連接起來,她同父母的感情更深了,也更加淳厚。直到今天,父母有什么話仍然喜歡悄悄地跟她說,她是父母最貼心的人。
像高力根和南斯勒瑪夫婦這樣疼愛女兒的人也的確非常少,當(dāng)他們有了一個工作指標(biāo)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敖德巴拉,因為敖德巴拉就是他們最親最親的女兒。當(dāng)時敖德巴拉已經(jīng)長大成人,從此走上了工作崗位。她先是在汗烏拉嘎查的小學(xué)里當(dāng)老師。由于學(xué)校里教師少,她要教語文、數(shù)學(xué)、政治等好幾門課程,對于她來說這很辛苦,卻也鍛煉了她各方面的能力。1981年她又被調(diào)到錫尼河?xùn)|蘇木政府工作。她先是做打字員,后來又做過婦聯(lián)干事、政府秘書、黨委秘書、文教衛(wèi)生助理等工作。用她自己的話說,我都快忘了我都做過哪些工作了。實在太多了。
由于敖德巴拉在工作中表現(xiàn)非常突出,1987年,她光榮地當(dāng)上了蘇木政府計劃生育助理員。在敖德巴拉心里始終這樣想,她要加倍努力地工作,用最好的成績回報養(yǎng)育她的鄂溫克族父母,回報這片賜予她力量和智慧的神圣草原。
計劃生育助理員的工作不干不知道,真正做起來讓敖德巴拉深深體味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計劃生育工作是一份不被大多數(shù)人理解的工作。當(dāng)她宣傳計劃生育政策時就有人問她,你是一個來自上海的漢族人,咱們這里都是少數(shù)民族牧民,你能做好這種工作嗎?敖德巴拉堅毅地回答他們:雖然我是來自上海的漢族人,但我從小生長在鄂溫克牧民家庭,和你們一樣是草原的孩子,是真正的牧民。我一定會按照國家的法律和法規(guī)辦事,真心實意地為牧民服務(wù),我想我一定能把這份工作干好。
敖德巴拉是這樣說的,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在鄂溫克草原上,世代生活著鄂溫克、蒙古、達(dá)斡爾、滿、錫伯、俄羅斯、漢等各民族同胞。長期以來,各民族合睦相處,這里是一個各民族組成的大家庭。但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也給這里遺留下來很多的生育方面的陳俗陋習(xí)和落后的觀念。“生死都是薩滿的旨意,孩子是上天送來的財富,決不能違抗。”這樣的思想在牧民的心里仍然存在著。人們頭腦中的觀念其實是最難改變的。這就需要計劃生育工作者與他們進(jìn)行交談,幫助他們轉(zhuǎn)變觀念,介紹國家的有關(guān)政策,將計劃生育同生產(chǎn)生活緊密地結(jié)合起來。在工作中,敖德巴拉首先遇到的就是語言問題,為了與各民族姐妹能夠進(jìn)行心與心的溝通,她努力學(xué)習(xí)多個民族的多種語言,這才能方便交流,只要有了交流,工作就好開展了。當(dāng)她能夠流利地說鄂溫克語、達(dá)斡爾語、蒙語和漢語時,她感覺真是如虎添翼。不知她與牧民姐妹們說了多少話,到了后來,少數(shù)民族姐妹由躲著她變?yōu)樵敢獍研睦镌捀嬖V她。她成了已婚婦女的知心人。敖德巴拉給她們講計劃生育的法律法規(guī),講計劃生育的好處。當(dāng)她們需要她的時候,她會竭盡所能地幫助她們。姐妹們做手術(shù)時,她會親自送他們?nèi)メt(yī)院,做完手術(shù)她還會繼續(xù)留在病床前護(hù)理照顧她們,直到她們身體恢復(fù)。
敖德巴拉剛做計劃生育工作時,東蘇木牧民中不登記生育、超生、婚外生育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她非常著急。于是,只要有群眾聚集的場合,像“五四”“元旦”等節(jié)日,她就會利用這些難得的機會向牧民宣講優(yōu)生優(yōu)育的知識和計劃生育的有關(guān)政策。她常對牧民說,一個民族的繁榮興旺,不在于數(shù)量的多少,關(guān)鍵在于人口素質(zhì),先天素質(zhì)的提高取決于優(yōu)生,后天素質(zhì)的提高則主要取決于優(yōu)育。敖德巴拉嘴里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少生而且要優(yōu)生優(yōu)育。剛開始她一說這些話,大家都紛紛躲開,不愿聽她絮叨,可時間長了,人們漸漸地從她的話里聽出了道理來,慢慢地也就理解了優(yōu)生優(yōu)育的觀念。
鄂溫克旗錫尼河?xùn)|蘇木面積很大,而且牧戶居住得非常分散,由于工作需要,敖德巴拉常常要下鄉(xiāng)深入到牧民家里。那時在草原上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騎馬,敖德巴拉就這樣騎著馬走遍了東蘇木的每一塊草場。十幾年下來,她成了當(dāng)?shù)氐幕畹貓D,每家每戶的冬營地和夏營地她都了如指掌,怎么走她都記得清清楚楚。騎馬這在現(xiàn)代人看起來非常浪漫的交通方式,在草原上實際上是非常艱苦的,男人騎個半天也會累得人腰酸背疼,更不用說一位婦女一騎就是十天半個月了。
1993年的冬天,為了趕著完成計劃生育工作的年終報表,敖德巴拉又要冒著嚴(yán)寒趕到布日都嘎查。當(dāng)她從馬棚中牽出馬時,她的丈夫特格喜巴雅爾連忙跑過來幫她把馬肚帶勒緊。他對敖德巴拉說,可能要變天了,等過一兩天,天氣好些的時候再去吧。敖德巴拉說,不行啊,報表得趕快報上去,天氣再壞也得走啊。
草原上的天氣說變就變,剛才還是晴空萬里,一會兒太陽就被厚厚的云層遮住了,嗖嗖的西北風(fēng)卷著漫天的雪花向草原襲來。這是一場來勢迅猛的暴風(fēng)雪。正走在半路上的敖德巴拉在暴風(fēng)雪中奮力地掙扎著,她和那匹跟隨她多年的老馬像海洋中一葉隨波漂蕩的小船,在暴風(fēng)雪的巨浪中時隱時現(xiàn)。路已經(jīng)被雪完全蓋住了,根本不知道路在哪里,天色也漸漸地暗了下來。風(fēng)刮在臉上像刀割,敖德巴拉只好在馬上趴下來,將頭埋在馬鬃里。這時她真的有些絕望了,她有些后悔沒有聽丈夫的話,但這時已經(jīng)沒有辦法了,她只能憑感覺繼續(xù)在風(fēng)雪中前行。
敖德巴拉的馬還真是匹好馬,它竟然馱著敖德巴拉找到了一個蒙古包。當(dāng)時已經(jīng)晚上十一點鐘了,敖德巴拉已經(jīng)被凍得哆哆嗦嗦,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匹馬也快耗盡體力,站都站不穩(wěn)了。人們常說“老馬識途”,看來這句話的確是對的,要不是它,敖德巴拉很可能再也回不了家。這個蒙古包是牧民達(dá)力斯的,當(dāng)他們看到敖德巴拉時被嚇壞了。他們趕緊將她扶到氈包中暖和,一家人一陣忙活,又是熬奶茶,又是熱布里亞特包子。敖德巴拉在包里喝著熱乎乎的奶茶慢慢地暖和過來了,身體有了知覺。這時她才發(fā)現(xiàn)耳朵和頭皮都被凍壞了,一陣陣地發(fā)麻。
直到第二天中午,暴風(fēng)雪才停止,太陽出來后草原上一片潔白,晃得人眼睛生疼。敖德巴拉見外面天氣好轉(zhuǎn)了,又想上路了,因為工作是耽擱不得的。主人再三地勸她,還要走六十里才能到布日都嘎查,下次再去吧。可倔強的敖德巴拉還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工作,她騎著馬,在已沒有路的草原深處艱難跋涉,硬是一戶一戶地摸索著尋找,最終完成了報表工作。當(dāng)一周后她回到家里,丈夫看到耳朵和頭已經(jīng)被凍傷的她,心疼得不得了,對她說,難道你干工作還要把這條命搭上嗎?敖德巴拉卻對丈夫笑笑說,沒關(guān)系,只要是為咱們牧民老百姓們做事,受點苦不算什么。其實敖德巴拉受的苦又何止這些,有些她同別人說了,更多的她都藏在心里,不愿向別人提及。
經(jīng)過不辭辛苦的下鄉(xiāng)調(diào)查,敖德巴拉的大腦里已經(jīng)形成了一份錫尼河?xùn)|蘇木的人口檔案,誰家有幾口人,妻子是誰,家里有幾個孩子,她都記得一清二楚。而這些資料的獲得,都是通過她十幾年如一日騎馬深入牧戶得來的,每年她都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這樣度過。
其實吃苦受累敖德巴拉還不怕,她最怕的就是自己的工作不被人理解,被人誤解和不被認(rèn)同的滋味是最難受的。當(dāng)?shù)赜幸晃幻兄Z日布的老人,他一直希望能抱上個孫子,每次兒媳有了身孕,他都會拿起心愛的薩滿手鼓圍著氈包一圈圈地轉(zhuǎn),邊轉(zhuǎn)嘴里邊念念有詞地祈求上蒼賜予他一個白白胖胖的孫子,可是沒有像他期望的那樣,兒媳接連兩胎生的都是女兒,這讓諾日布老爹悶悶不樂,整天無精打采的。一天,敖德巴拉來到了諾日布老爹家,還沒有開口,老人就沒好氣地對敖德巴拉說,你又來干啥,還是不讓我抱孫子是吧?敖德巴拉一點也沒有生氣,笑著對老人說,我這次正是為您抱孫子的事來的,以前你的孫女年齡還小,按政策不能生第三胎,現(xiàn)在符合生育間隔,我是專門給您家送第三胎指標(biāo)來的。聽敖德巴拉這么一說,老人反倒有些糊涂了。經(jīng)過她耐心的解釋,老人終于明白了國家的有關(guān)政策,開心地笑了起來。
在汗烏拉嘎查有一位很讓敖德巴拉頭疼的蒙古族婦女,她的名字叫巴達(dá)瑪罕達(dá),已經(jīng)有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可又悄悄地懷上了第三胎;她性格倔強,軟硬不吃。為了勸說她采取補救措施,敖德巴拉已經(jīng)在四十里的路上跑了很多個來回,盡管她磨破了嘴皮子,說得嗓子冒了煙,但就是沒有一點效果。有一次敖德巴拉又到了她家,她竟然放開了她家的那條大黑狗嚇唬敖德巴拉。騎在馬上的敖德巴拉連忙躲閃,可馬還是受了驚嚇,把敖德巴拉摔了下來。敖德巴拉的頭和胳膊都摔破了,腳也崴了。敖德巴拉一瘸一拐地走進(jìn)了巴達(dá)瑪罕達(dá)的氈包里,索性在她家里住了下來。接下來的幾天,敖德巴拉一邊幫著她擠牛奶、做飯、添草,一邊跟她嘮嗑,耐心地勸說。人心都是肉長的,幾天相處下來,敖德巴拉的真情實意深深地感動了女主人。幾天后巴達(dá)瑪罕達(dá)拉著敖德巴拉陪她到蘇木采取了補救措施。
十多年來,敖德巴拉一邊工作,一邊承擔(dān)著家庭的重?fù)?dān)。家里的一切都要她操持,兩個孩子需要她照料,年邁的父母她也盡心盡力地贍養(yǎng)。雖然她很清貧,家里的牛羊并不多,但她卻在這平凡的生活中體味到了家庭的溫暖,也正是因為這個幸福家庭對她的支持,她的工作才取得了這么好的成績。
從敖德巴拉來到草原算起,四十多年過去了,對于這片古老的草原來說,這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對于一個人來說,人生的路程已經(jīng)走了很遠(yuǎn)很遠(yuǎn)。來自上海那座繁華都市的敖德巴拉已經(jīng)成為草原上一名優(yōu)秀的計劃生育干部,這也許都是命運的安排,冥冥中似乎有一雙手將她和草原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再也無法分割開來。
敖德巴拉也曾想過回上海看一看,但那只是一個夢,一個不知何時才能實現(xiàn)的夢。當(dāng)她得知當(dāng)年的上海孤兒有機會回上海尋親訪友時,她激動得一宿都沒有睡好。敖德巴拉和伙伴們終于如愿以償?shù)鼗氐搅松虾r,他們的心情是非常復(fù)雜的。四十多年后,他們又回到了故鄉(xiāng),而此時的上海已經(jīng)成為一座繁華的國際大都市。當(dāng)他們登上東方明珠塔俯瞰時,當(dāng)他們在外灘觀光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自己出生的地方。在上海市民政局的安排下,他們參觀了當(dāng)年他們住過的上海市孤兒院舊址,對于故鄉(xiāng)的眷戀也油然而生。此次上海之行,他們還與當(dāng)年的上海知青和社會各界人士進(jìn)行了親切地交談。當(dāng)上海的朋友們得知敖德巴拉還是“五一”勞動獎?wù)芦@得者時,大家紛紛投來欽佩的目光。雖然上海是那么的好,但在敖德巴拉心里,她覺得自已并不屬于這里。當(dāng)她在回家的路上時,家離她越來越近,而上海離她越來越遠(yuǎn),遠(yuǎn)到她在睡夢中也不會夢到那些狹窄的弄堂,只會夢到自己小時候騎在馬背上,在草原上和父親一起放牧牛羊。
靜靜的伊敏河水潺潺地流過鄂溫克草原,緩緩流進(jìn)牧民的心窩。敖德巴拉回到了她熟悉的草原,她踏踏實實地站在山包上,看著草原舒緩的輪廓,看著陣陣輕風(fēng)消失在視野以外的地方。她內(nèi)心的感覺告訴她,她永遠(yuǎn)屬于鄂溫克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