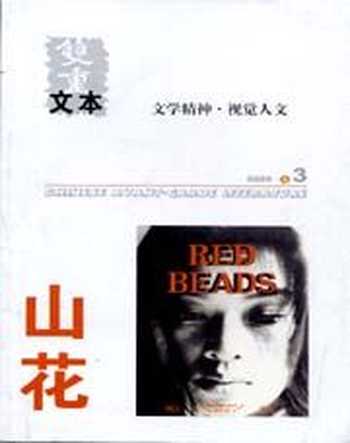小說之我見
劉自立
喬伊斯是造字能手。他的《尤利西斯》中造字頗多,他的《芬尼根守靈》中造字更甚。何以要造字,想來是他文字的所指功能在其小說創(chuàng)造中乏善可陳;再細想,是他的造字說當中,有一種顯然的能指系統(tǒng)在悄悄的發(fā)生變化;是一種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的變化。《尤利西斯》是一部準現(xiàn)實主義小說,自不必多論,但是他的現(xiàn)實主義是在一種異樣的狀態(tài)中存在的,是對于現(xiàn)實主義的反撥,這是他的特點;這個悖論的出現(xiàn),是因為老喬的現(xiàn)實主義和別人的不一樣,就小說的宗旨來看,他的文本實驗是優(yōu)先于他的觀念陳述的,比如說,他的愛國主義,反反猶太主義和他的自然主義觀念等。如果說,他的意識流是在補充他的現(xiàn)實主義,那么,他的布魯姆們的出現(xiàn),就不那么具有實驗性和文本現(xiàn)代化的含義了,因為,如果巴爾扎克也過“布魯姆節(jié)”的話,老喬的存在之意義就會因此貶低不少;正是因為老喬的文本,是在一個比說故事更復雜的階位上來塑造他的布魯姆們的,是在將他的人物放在一個總體的語言指向的超級文本之中的,所以,他的小說的觀念化的意義,就自然地讓位于一種更加超然的指向之上,從而超越于任何觀念。雖然,這一點是不那么明顯的。
我們在閱讀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的時候,會發(fā)現(xiàn)老納的思維線索,是按照老喬的準現(xiàn)實主義的軌跡運行的。他的總結(jié)當然非常精彩。但是他的總結(jié)似乎還是停留在老喬的傳統(tǒng)敘說當中,并且認為他的許多所謂的意識流的用字是沒有必要的和極為晦澀的。
但是,其實正是他的這些所謂的晦澀和歧義,帶來了意識流文字的特殊魅力。
于是,小說的解構(gòu)循著兩個方向發(fā)展。一個方向是,用意識流的寫作手法,增加現(xiàn)實主義的表現(xiàn)效果,使得小說人物在現(xiàn)實主義的大框架中更加完善起來和勤盯接近自然;第二個方向是,由文本的和文字的歧義和多義性,造成小說人物的虛無化和虛擬化,從而造就一個更為哲理化的小說時空,給一代代的讀者,留下只能接近而無可抵達的整體衰變狀態(tài),使得小說的涵義設定趨于無限,像哲學和現(xiàn)代邏輯的設定一樣,只是將人物和情節(jié)作為傳達文本的手段,考驗人們對待事物的判斷能力和陳述能力,而不輕易對陳述的真理性加以確定,像炮制上帝造物般的人類關(guān)懷之謎。用邏輯的術(shù)語來說,就是文本的指向,只是表達一種所謂的“傾向性指向”,這個傾向性指向,是指人們將哲學/文學當中的概念和推斷/人物和情節(jié)(語言),假設為未知的前提之下的一種思維。即便這種未知在某種前提條件下已經(jīng)有解,但卻是一種有限的有解。也就是說,是在將人們的最終的肯定性陳述和非肯定性陳述,都排除在外的情形之下作出的決定。這樣,我們的老喬的文字處理功能也就變得更為復雜和深刻了。這也許更接近這位偉大作家的初衷吧!
有意思的是,在我們?yōu)g覽另一種描述世界的文本的時候,一個重要的邏輯學家告知,Quark,這個物理學上的專用名詞,是在老喬的小說當中被首次發(fā)現(xiàn)的。該詞當時出現(xiàn)在他的小說里,其意是:小東西和小矮人。然而,夸克本身在物理學中的故事,同樣是非常有意思的。難道我們不可以來簡單地敘說一下她的涵義嗎?
是的,我們的問題應該也是這樣的。“夸克真的存在嗎?”
這當然是一個物理學的問題。但這也是一個哲學的問題和邏輯學的問題。再而言之,她也是一個文學的問題。
比如說,“布魯姆真的存在嗎?”
這兩個基本點問題的答案當然是似是而非的。而這個似是而非,正好是我們所追求的藝術(shù)效果和理性定勢。
在另一個方面,“場”的出現(xiàn),是人們論說夸克存在與否的另一種方式。“是只存在一個唯一的場?還是存在許多個場?”這是德國哲學家施太格繆勒的提問。
有意思的是,在我所知道的北京的文人墨客里,談論“場”的神秘主義者是不在少數(shù)的。他們還往往愛講“在冥冥之中”云云。都顯示對于語言之外的一種預示的敏感。
而“場”這個概念,造就了進入文學領(lǐng)域的另類視野,為小說文本留下巨大的、沉默的、頗具潛力的空間。于是我們看到,我們的角色,即作家和小說人物之間,產(chǎn)生了他們共同占有的“場”。這個場的出現(xiàn),是以兩者之間的可以互相了解和可以互為陌生之狀態(tài)為其存在前提的。這意味著“場”的獨立存在的異類性質(zhì),意味著對于建立統(tǒng)一場論(在文學領(lǐng)域中)的最大背棄。
我們的文學的夸克們的時代的和社會心理的真實狀態(tài)如何?我們能否一攬子解決他們在文本活動中的全部目的性和非目的性?他們的關(guān)系是否是一種衰變?是不是在他們的“質(zhì)子心理”(請允許我也造一個漢字或者說漢詞?)中,也存在著一種可以描述和可以論證的“場”,抑或完全相反。
我們的老喬也好,其他文本也好,是否說明在一個特定時代中產(chǎn)生的話語,和在一切時代產(chǎn)生的話語,都有效于一個共時性場域?我們的或者他們的作家,在都柏林或者在北京的作家,在超地域的所有場合營造的場,是否在時空當中都被論證為有效的?我想,老喬應該是歐洲人常說的那種“懷疑論者”,而不是決定論者。這當然是一個玩笑。小說是在一個有限的時間里發(fā)生的事情,抑或?qū)r間的追溯。無論是普魯斯特的漫長的逝水流年,還是老喬的一天二十四小時;時間,在我們的未知和先知看來的時間當中,也許只有有限的意義被讀者看到。我們在論證老喬的一天/時間設定論的場面中,也許不必將他的說法之意義看得過于嚴重,我們寧肯將他的意義游戲化而將重點轉(zhuǎn)入他的文字。
宇宙之大,粒子之小,都是不可理喻的怪誕的情節(jié)。
我們在現(xiàn)代化小說當中所看到的那種語言指向,應該是和哲學的懷疑論相互呼應的。宇宙演化的動人的情節(jié);歷史演化的動人的情節(jié);人類在特定的某個時代和地域中演化的同樣動人的情節(jié),如果或許可以做一個類比的話,我們還是將宇宙演化的情節(jié)看得更為動人。此一情節(jié)的復制,當然會使得斯皮爾博格之流忘乎所以。因為該情節(jié)的時空間的巨大背景,就已經(jīng)將人類的判斷棄置于后了。人類的一天二十四小時和恐龍的一兩億年的時間觀,一下子就變得無足輕重了。
而在對待歷史上,不是早就有人說過,其魅力大大超過小說微不足道的效果嗎!除非有人像老喬和博爾赫斯那樣對小說進行更新。一如納博科夫所說,由于老喬的出現(xiàn),隨后出現(xiàn)了一批小詩人,等等。
這個推理可以邏輯地延續(xù)下去。而我們在欣賞尤利西斯的時候,往往是在文字的一種非指向性,或者說,是在一種文字的非固定指向性當中,去理解他的用意的。這當然是件有趣的事情。于是,我們回到了我們常常說到的小說的時間性考量上。一部小說的時間性魅力,是在小說的一時性/共時性的特點上被巧妙地規(guī)定的。夸克的衰變像人的一生一樣,是在無意義的最終結(jié)果上努力抗爭的一種意義!這種雙重的意義,無外乎趨向兩種表達方式。
一種方式是,我們將小說的寫作,看成是有結(jié)局的,固定的,目的論的產(chǎn)物,這是導致小說純粹觀念化的產(chǎn)物;另一種是,我們的古往今來的喜怒哀樂,被一種無形的命運之手所操縱,最終走向無可挽回的悲劇結(jié)局,像可悲的布魯姆對于茉莉的故事的結(jié)局;也像我們?nèi)祟惖拿\或者說恐龍的命運。這就是我們在二十世紀這個怪誕的世紀,“噗”地一聲,就歸于毀滅的那種結(jié)局。
我們的和他們的,尤其是他們的所有文字作品,在這個時間段上表現(xiàn)的,就是這樣一種敘述和論證。俄們的絕對的烏托邦的幻滅,更加深了我們的印象》我們無聊地欣賞這樣的一種結(jié)局,多半是有過一點小小的興奮而已。一道數(shù)學的難題被解決了,但是,我們馬上就會懷疑數(shù)學本身的抽象能力。
一個可以延伸的點,實在是在或者不可以延伸的點上展開的。敘述,就是一種不可能性的可能性,是—種完完全全的對于我們?nèi)祟愖陨淼奶魬?zhàn)。無論我們是在閱讀老喬的一時/共時性歷程,是在重復都柏林人的二十四小時,抑或是在人類的全部時間上存在,其結(jié)果都是—樣的。就像一個中國詩人所說的,一個人的血,回流入全人類的血管。
其實,老喬的時間觀,在他的文本表達中,是一種藝術(shù)處理藝術(shù)詮釋的手段,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他的至關(guān)重要的細節(jié)由此創(chuàng)生;而時間和空間的互為前提,則是現(xiàn)代物理和現(xiàn)代哲學的基本世界觀。
小說的語言,是表達小說世界的媒介,這一點,是以刨、說語言的界定方式,幾乎沒有人來懷疑。我們;度在巴赫金的言論中就發(fā)現(xiàn)過這樣的論證。換句話說,小說的目的,是通過小說的語言來塑造人物和情節(jié);小說的語言是一種在人們了解的小說內(nèi)容以后被拋棄的語言;這一點,是我們對待舊小說的基本估計。而在老喬那里,這個固定的看法開始動搖,繼而顛覆。小說語言的本體論目的,像在物理學和哲學領(lǐng)域里的目的論的虛妄一樣,被老喬動搖繼而顛覆了。(這里,請原諒我借用了也許已經(jīng)過時的哲學術(shù)語)。
沒有人想到,甚至是納博科夫這樣的大智者,也將老喬看成是一個行文邏輯清晰的文人。而在我的眼睛里,那個門,是gate,而不是door。我看中老納的言論中,將宇宙放人袋鼠的口袋的說法。
剝離這樣的對于語言,對于小說語言的一般看法和一般用法,是否還有可供小說使用的另外—種或者多種語言和對語言的質(zhì)疑甚至顛覆呢?這本是和語言的哲學思索聯(lián)系在一起的。如果說,哲學語言當中的劃界,已經(jīng)將語言分成可以進入陳述和不可以進入陳述,并且在區(qū)分其有無意義方面,回復了對于形而上學和形而下的難度甚大的反思的話,那么,這樣的討論,何以被小說語言所阻止和忽略呢?換句話說,小說語言的這種零度寫作,是和語言哲學的現(xiàn)代思考無可分離的。
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傳統(tǒng)敘述的一般慣例呢?重復而言,老喬小說的用語,何以在詞匯的游戲上(也有其顯然的游戲規(guī)則)如此不遺余力呢?
他是在為一種我們可以關(guān)照的一般社會和哲學理念寫作嗎?顯然不只如此。
一如前述,一時性/共時性寫作的特點,在他那里,完全訴諸于語言本身;而訴諸于語言本身的原因,是因為他看見了door,而不是gate!(是的,door的敞開,也許是為了讓獨角獸和復制的恐龍搖擺而人!)
敘述,是在非敘述的敘述中敘述的;就好像我們看見了伏羲的狗頭人身一樣!(注意,德里達是將赫爾墨斯和我們的伏羲相提并論的。)
固然,喬伊斯的小說賴以生存的活力所在,是一種“雙重關(guān)照”,一是他的一時性時代背景和地域人文化;再是他的共時性關(guān)照,即對于我們?nèi)祟惿鐣餐乃季S模式和思維能力的考問。后者更是他的用心所在。他的小說和后來的不多見的幾位現(xiàn)代小說大師和后現(xiàn)代大師的小說,在將小說的傳統(tǒng)敘述和非傳統(tǒng)敘述有機結(jié)合方面,功績卓著,幾無后繼。換而言之,他們是一批可以將小說和詩歌功官拼用的奇才和怪才。于是,在這樣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詩歌的語言和小說的語言的混合物,是無法將其分離的一種特殊的優(yōu)化語言。是任何一種單純的詩歌語言和單純的小說語言無法取代的語言。而這種語言的出現(xiàn),初看,對于小說內(nèi)容的表達(和象征)更為有效化;細看,這樣的語言其實是在對我們的和他們的所有的語言的一種自我否定。而且,越是否定,肯定的內(nèi)涵就越是豐富。這是非常耐人尋味的二律悖反。這種文明和老喬的所謂的自然化描寫合二為一,都在證明這樣的一種一致性和傾向性。
哲學的和物理學的懷疑,和小說的懷疑——在語言的功能和定位定性上——殊途同歸。如果說詩歌可以直達對于語言的挑戰(zhàn),可以直達語言的似是而非和相對主義之本質(zhì),并且在詩學領(lǐng)域當中和哲學的基本問題合攏的話,那么,老喬們的小說語言,在這方面是和他們異類同歸,或者說是同類同歸的。所謂的詩化小說,應該是更接近語言本質(zhì)的文本試驗;她有更進步和更完善的表現(xiàn),因為這樣的語言已經(jīng)看到了語言的局限和她的宿命,而絕非相反。而在一般的寫作狀態(tài)中,我們往往是將寫作的語言和所謂的現(xiàn)實對應起來,并考查她們的對應的程度。現(xiàn)在,事情在相反的維度上慢慢展開,日益輝煌起來了。
從小說的結(jié)構(gòu)看,故事的懸念是明顯存在的,它的細節(jié)也是明顯存在的。簡而言之,小說的情節(jié)其實已司空見慣:布魯姆的妻子茉莉和鮑伊嵐有染;而布魯姆沒有任何抗爭,他只是想人非非地希望他看得上的斯蒂芬可以取代之;而茉莉,則在和她的情人有過那種感受以后,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將她的情感重心轉(zhuǎn)移到他的老公身上;她,還是愛著她的老布的——這就是故事的梗概——也是納博科夫的見解。
就像我們看到的關(guān)于宇宙起源的論述一樣,宇宙的發(fā)生,是在一次所謂的大爆炸當中;而生命,則是在一個美國人制造的關(guān)于氨基酸的試驗中被重新制造出來的。其制造的關(guān)鍵,也是引入電與火的類似“爆炸”。換言之,宇宙和生命的形成,是由一個我們不可理喻的質(zhì)量巨大的點,作為其起點的。這樣的構(gòu)想,和我們的文學結(jié)構(gòu)的分析也許是有著形似,也許還有一點神似。當列維·施特勞斯在他的熱帶森林里,考證人類結(jié)構(gòu)的同一性的時候,問題的提法是,我們的存在,是按照一種固定的,同一的模式,由點及面地發(fā)展起來的。歷史和小說的結(jié)構(gòu)同樣決定了他們的整合;而現(xiàn)在,問題的提法似乎顛倒而成,結(jié)構(gòu)的形成,是我們看到和發(fā)現(xiàn)了那些從古希臘以來就有先哲提到的原子;當然,這個原子,其實也是一種思想的傾向性和一種后天的邏輯判定。
這樣一來,我們看待小說文本的時候,像喬伊斯一樣,形成文本結(jié)構(gòu)和小說人物情節(jié)的那些原子究為何物,成為問題的核心,那是些什么東東呢?是我們現(xiàn)在說的詞匯,是陳述的句子;而這些詞匯和句子的組成,或許是可以按照我們發(fā)明的各種深奧的邏輯判斷來運營的;但是,自從美國人蒯因提出的,分析的和綜合的判斷,會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困境的論點被揭示以后,對于詞匯/定義這個原子的懷疑,就成為我們對待一切陳述的懷疑的起點;而藝術(shù)的魅力,在詩的意義上規(guī)定了小說的意義和無意義。因為我們的閱讀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不是為了苛求意義,寧可說,是為了尋找一種和我們體驗到的生活的無意義的對稱,從而產(chǎn)生的無意義的意義,等等。小說的深層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朝向非同一性的、多義性語言結(jié)構(gòu)和情感結(jié)構(gòu)發(fā)展,甚至涵蓋其情節(jié)。這是現(xiàn)代小說文本的奧秘和奧妙所在。如此看來,布魯姆的故事的真正涵義,是在結(jié)構(gòu)這個人物的同時,對這個人物進行一番有趣的解構(gòu)。正像老納的分析一樣,我們在每一段故事敘述中,都會發(fā)現(xiàn)詞匯的多義性游戲附著在人物和情節(jié)的身上而自成體系,且導向另類的詩意欣賞功能之出現(xiàn)。我們不知道某一個音素,是否比某—種語形,某一種曲式,抑或一般的情節(jié)的懸念和人物的性格,更加富于詩意。因為在一個簡單的如博爾赫斯的語言和肖邦的語言中,我們還是發(fā)現(xiàn)了極為復雜的語盲傳達和受眾的驚喜!這正是因為那些我們看似簡單的句子,是我們完全沒有理解和感覺的句子。就像原子,粒子和質(zhì)子。
那些被老喬變化和悖用的詞匯/定義,那些他自創(chuàng)的詞匯/定義,一概顯示了他的極為新穎的小說觀和世界觀。喪失了所有這些特征,理解他的難度就會增大,就會陷入真正的誤解和無解之中。只是,他們的文字的象聲性特質(zhì)(缺少一個象形特征),使得老喬的這種努力極為有限;因為他不可能知曉我們漢字的在聲與形方面的魔術(shù)般的變化,否則,《尤利西斯》,就更加是一部可以理解的,知其用意的,人類可以讀懂的天書了。
幾年前在天津,由金堤先生召集的喬伊斯國際研討會上,我記得愛爾蘭的喬學大師,曾經(jīng)對老喬自撰的一種表現(xiàn)愛爾蘭教堂的鐘聲的詞匯,進行了繪聲繪色的模擬。是否有人知道,我們的詩文中關(guān)于鐘聲的詞匯,是在一種對于鐘的形象化的模擬中帶進了鐘聲的聲音的?比如鐘鼎,鼎,就是一副古代的中國畫。字為畫,畫為字,是老外們難以想象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西方出現(xiàn)了反邏輯主義者,他們將觸覺仲向東方和東方文字。因為,中國字,是一種帶有先驗存在特征的語言,更加接近所謂的本體(如果我們還可以運用這個為邏輯學者討厭的詞匯)。而在一切由邏輯定位的西方文字中,這樣的反邏輯思維的,形聲兼俱的文字和詩意的存在,是在他們的視線之外的。
簡單地說,語言的象聲化,是西方語言的特征。為了附和這樣的描述風格,老喬的造字癮大為膨脹而顯得大才馳騁,和者為寡。而他的造字說,大多數(shù)是在附和大自然的一種或者多種聲音。因為,在除了詩人龐德之外,西方文學家對于語言的理解甚至創(chuàng)造,實在是只能在聲音方面做一些創(chuàng)新而已。他們是絕對想象不到類似我們的漢字的象形功能,會在寫作當中彰顯出多多少少的藝術(shù)性的。而按照所謂的能指和所指的區(qū)分,西方文字的象聲性原理,規(guī)定了其文字在能指方面的無理,陛狀態(tài)。我們知道,玫瑰的能指是無意義的,因為它可以在發(fā)聲上完全有別于現(xiàn)在的發(fā)音。
而漢字的起源,至少在造形的特征上,一般是可以按照所謂的本體論界說去尋根溯源的,如我們的水字,山字,等等,是源起于其象形的特征的。
于是,現(xiàn)在,我們來看看老喬的字謎游戲吧!
在他的多少按照老納的說法有些邪惡的文字處理系統(tǒng)中,人類的,尤其是籠罩在他們的西方文明的陰影當中的人們的吃喝拉撒睡的象聲用語,成為他的文字游戲的卓越的,可以說是最為卓越的表現(xiàn)和表達。我們有幸讀到許多這類文字(當然也可以稱為關(guān)鍵詞吧!我們的引語來自王佐良先生的選注。)
Snotgreen
Crush,trak。Crik,crik
Swilling,wolfing gobfuls of sloppy food,
Shovelled gurglin soup down his gullet,
Something galoptious,
Reek of plug,spilt beer,me's beery piss,
也許,我們現(xiàn)在可以引用一下關(guān)于老納談論老喬的文字游戲的申慧輝先生的譯文:
“金牙,‘金嘴巴自然是指四世紀君士坦丁堡的高級主教約翰,”
“鼻涕綠色的海水和斯蒂芬的臟手帕以及缽中的綠膽汁聯(lián)系到—起;還有膽汁缽和剃須缽以及海水,苦澀的淚水和咸咸的粘液,所有這一切都在一個瞬間熔為—個形象。”
“利奧波爾德。麥金托什他的真實姓名是希金斯。”
“他把自己的名字藏了起來,就是那個好聽的維廉,藏到劇本里。”
“布魯姆看到了自己的創(chuàng)造者。”
“誰是麥金托什?”
等等。(還是讓英文專家來進一步解說這樣的詩意節(jié)奏吧!)
看過上述詩意文字后,我們開始進人另一個論點。
由多義性詞語涵蓋的多義性敘說,在老喬晦澀的文本中非常順暢地行進著。這樣的復調(diào)敘述帶來的詩意,在本文的邏輯關(guān)系當中是可以成立的;而在邏輯之外的非小說的,離機文本中(請原諒我造出另一個不太貼切的詞匯!),也是可以單獨成立的,那是一種對于小說敘述的背離和反叛嗎?
進入復調(diào)敘述,是近現(xiàn)代小說擁有的一種敘述張力。這種張力帶來的邏輯關(guān)系,是在對于邏輯的顛覆中隱隱約約地存在著的。因為按照前述所謂夸克的論證,這個或者那個文本,作為客觀/主觀的存在,只是一種存在的“傾向”而已,小說的最終指向是無可言說的。詞語的指向在這里,已經(jīng)開始脫離小說的基本結(jié)構(gòu)而走向另一個看得見的或者是根本看不見的世界。
用直線的指向敘說小說的功能,在這里,已經(jīng)像介子的侵入那樣衰變了;是在小說的一種看得見的或者看不見的能量的再消失和再組合中,發(fā)生了質(zhì)地的變化。如果我們在布魯姆的身上看見了他的后希臘神話的因子和影子,那么,我們在預期后人看待他的時候,布魯姆主義的現(xiàn)實,已經(jīng)在朝向后神話的神話的存在而發(fā)展了。于是,作為老喬的復調(diào)人格,和作為尤利西斯的復調(diào)文本,在一個可以預期的未來,早已經(jīng)成為神話的神話了。至于到底是讓虛構(gòu)代替現(xiàn)實,還是讓現(xiàn)實代替虛構(gòu),這個問題,在具有超越性的時空存在里,就被神話本身給解構(gòu)掉了。留下的痕跡是存在的;既有的小說是存在的;我們的讀者還是在原有的軌跡當中面對文本;但是,是由我們和老喬來虛擬這個世界,還是上帝會一次次地蒞臨,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的文字游戲的高下,是在老喬這伙人類天才的掌控之下,還是由上帝的使者,運用電腦的虛擬語言來加以掌控,這,也是一個問題。
我們好像成了某一高級生物的玩物。我們是他們手上的一滴淚,他們是否會將其抹去呢?我們的小說在這個意義上能否完全轉(zhuǎn)化成為詩和上帝的寓言?而寓言在我們這個時代,能否擺脫繼續(xù)被人們所忘懷的命運?小說作者的出現(xiàn),無論他是博爾赫斯還是納博科夫,是艾柯還是卡爾維諾,都只能在同樣的維度上,來完成他們的對于文本和詞語的未完成交響樂。因為作者的傾向和書中交代的情節(jié),在時間的超越方面,是一個無法完成又已經(jīng)完成的對位。所有的文本,是在邏輯的意義上爭論意義和無意義;而在反對邏輯和智商的普魯斯特那里,該問題以另一種面目出現(xiàn);他們是在爭論如何從邏輯和人類的有限度的理性,返回自由意志的問題;這是一個被羅素大為忽視的柏格森式的提問。因為,我們的和他們的文本,是在預期超越時間的空間里,做出預期的概率的。如若不然,那么,古代的尤利西斯和現(xiàn)代的尤利西斯的區(qū)別,就沒有任何必要了。而這,也是現(xiàn)代化小說文本之魅力所在。
希望尤利西斯不會成為我們手上的一滴淚,被輕易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