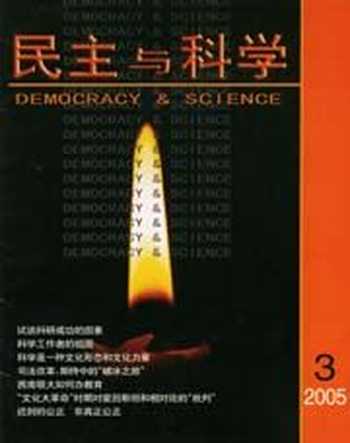“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
楊建鄴
從1968年到1976年,在中國大陸曾發生了一起我國科學史和20世紀科學史上一樁令人痛心的事件,那就是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進行一次極其荒謬的“批判”。這次“批判”,其水平之低下和手段之惡劣,可以說讓人瞠目結舌;如果說它是一場“批判”,倒不如說是一場想滅絕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大陰謀,而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只不過是實現這陰謀的一個可以利用的幌子,因為在所謂“批判”中根本沒有任何一點點值得認真對待的東西,有的只是無賴和強盜似的胡攪蠻纏和血口噴人罷了。
這個批判運動是由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下屬的“中國科學院‘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首先發起的,而這個“學習班”于1968年3月成立。在成立之時,這個“學習班”依照《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的精神宣稱:“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的嚴重錯誤就是目前阻礙科學前進最大絆腳石之一”,他們將“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相對論,革相對論的命”。這個“學習班”我們下面簡稱為“批相班”。
“批相班”于1968年6月炮制出第一篇“文章”,這篇所謂的“文章”,幾平毫無科學見解。他們聲稱要“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治,從而鞏固無產階級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對資產階級的專政”;他們大言不慚地吹噓,“這將是歷史上第一次在無產階綠專政條件下,在徹底進行社會主義的形勢下開展起來的科學大革命”。還說“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學革命都無法與之比擬的無產階級科學革命,即將出現在世界東方遼闊的地平線上”。
但這次偉大得“任何一次自然科學革命都無法與之比擬”的科學革命到底有哪些基本物理思想有了突破呢?是什么新的思想在孕育、催發科學將發生革命呢?絕對沒有!從“批相班”提出的幾條“論點”來看,實在荒唐得可笑,人們只會感到中國大地上忽然冒出了許許多多的魏蘭德的陰魂,他們根本不懂相對論,卻想把相對論和愛因斯坦的精神置于死地。
例如他們批判說:“相對論是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的相對主義。”他們甚至找到一個“有力的證據”:如果按照相對論所說,同時性是相對的,那么珍寶島事件中,我們說蘇聯開第一槍,蘇聯說我們開第一槍,究竟誰開第一槍豈不無法作出客觀的判斷了?這哪里是什么“批判”,純粹是胡說八道。但是誰要是不贊成他們的“批判”,誰就會大禍臨頭,就會被扣上“賣國賊”、“反革命”的大帽子。當時,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實在看不下去,指黃“批判”者們說:中國和蘇聯都在地球上,同在一個參照系里,從相對論推不出上述的結論。竺可楨先生不是研究物理學的,但是他能一眼看穿這些“批判”是什么貨色。
還有吏荒謬絕倫的“批判”,他們說,光速不變原理“深刻反映了西方資產階級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終極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生產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學是人類科學極限這種反動的政治觀點”。這可真正是極其荒唐的“批判”!
在進行了如此這般的“批判”之后,如像當時所有的“豪言壯語”一樣,他們立即宣告:“資產階級學者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一個個嶄新的科學理論,必須迅速發展起來,自然科學發展真正的新紀元一定會首先在我國到來!”
的確是“做夢都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位大學教師在大學課堂上講“力”時,介紹了常見的一些相互作用力以后,一位“大學生”立即像“批相班”的人一樣嚴厲地“批判”了這位教師:“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力,你為什么不講!?”教師莫名其妙。“大學生”說:“毛澤東思想威力!這是任何一種無法與之相比較的力!”
由此不難想像,這種比半個世紀前魏蘭德、勒納等人批判相對論還要荒誕的“批判”,會給中國科學帶來什么樣的“資產階級學者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一個個嶄新的科學理論”!到了1970年4月,當時是政府高級官員的陳伯達,甚至號召中小學生也來批判相對論,說:“中小學生思想活躍,眼光敏銳,興趣廣泛,很有生氣。”這簡直是拿科學開最低級的玩笑;試想,這樣的“群眾批判運動”會是什么樣的批判?
當時的上海理科大批判組還極盡造謠誣蔑和人身攻擊的能事,他們在1970年發表的文章“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寫道:“帝國主義需要相對論這樣的‘科學需要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他一生三易國籍,四換主子,有奶便是娘,見錢就是下跪。有一點卻始終不渝,那就是自覺地充當資產階級惡毒攻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喉舌。”這樣的文章,居然登上了全國最高級政治雜志。
在一本由上海理科大批判組寫的《愛因斯坦》的初稿中,他們完全不顧事實、信口雌黃地寫道:“愛因斯坦一生,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有不滿現實的一面,是為副;又有反對革命的一面,是為主。”“他高喊,科學家應該聯合起來,對政治問題不應當采取沉默態度,應當跪在資產階級面前,乞求自由、民主、平等。”
通過引用的這極小一部分的資料,就足以看出,在“四人幫”專制時期時,是如何嚴重地阻礙和破壞科學的進步。1930年,愛因斯坦就說過:
在我看來,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質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一條千古不移的定律。
愛因斯坦發現的這條“千古不移的定律”,無論對于歷史和現實都有重大的意義。
科學自身的特質,就離不開自由,就與專制是勢不兩立的,任何專制者都一定會遲早拿科學和科學家開刀。納粹時期如此,麥卡錫時期如此,“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是如此。納粹時期,專制者把科學分為“德國的”和“猶太人的”的兩種;麥卡錫時期把科學家分為對美國“忠誠”與“不忠誠”兩種;“文化大革命”時期則把科學和科學家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種,這統統是為了不可告人目的而顛倒是非、指鹿為馬,是對科學的污蔑和詆毀。自然科學從來不屬于任何特定的階級,它屬于全人類,自然科學中的學術權威也同樣如此。
1971年11月,正當“批判”的惡浪一陣高似一陣之時,周恩來在接見意大利前總理、社會黨領袖南尼時特意指出:“猶太民族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馬克思是猶太人,愛因斯坦也是猶太人。”這句現在聽來極其平凡的話,在當時對“批相班”幕后指使人可謂當頭棒喝。還有許多正直的科學家如竺可楨副院長、周培源教授,對這種倒行逆施作了機智的斗爭。例如1971年夏天,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周培源就公開發表了反對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意見。商務印書館還利用機會,巧妙地將許良英、李寶恒等人翻譯的《愛因斯坦文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于1974年和1975年相繼付排,并于1976年1月將第一卷印出,第二卷于1977年3月出版;第三卷則在1979年10月出版。
“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結束后,中國終于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人們終于有了封面為淡綠色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到1994年已經是第4次印刷了。1979年愛因斯坦誕辰100周年的時候,中國科學界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會,還出版了《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國外最好的幾本愛因斯坦傳記的中譯本,也先后在國內出版;至于國人自己編寫的愛因斯坦傳記就數不清有多少了。1999年,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斥巨資啟動了一個更大的工程,出版《愛因斯坦全集》。
愛因斯坦著作的陸續出版,是我們“最大限度地追蹤愛因斯坦的思想、生活及科學活動,從中領略到科學和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深遠影響”的最好機會。同時,這也是我們紀念愛因斯坦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