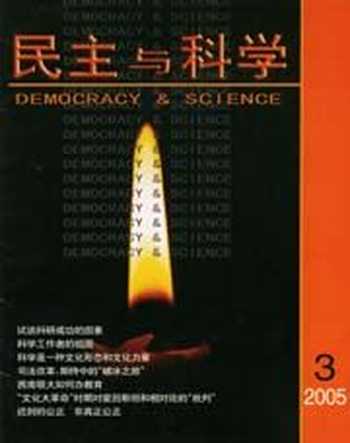群體非理性及其后的“記愧”
井 濤
那一年,我呆在布魯塞爾,乘EUROSTAR到巴黎不過兩個多小時的車程。正好有幾天的假期,于是決定去看看自己心儀已久的巴黎。作為自助游的必要功課之一,出發前我照例收集相關介紹資料,把以往形成的對目的地的種種印象清晰化、完整化。在心里已然勾勒出了諸多的畫面,到實地無非是驗證,哪些和我的想象是一致的,哪些比我想得更美好一點,哪些需要我去寬容和理解。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下,我隨手翻閱林達的《帶一本書到巴黎》,起初完全是把它作為一本旅行手冊來看,作者手繪的彩頁插圖很精美。翻過幾頁后,我的閱讀不再散漫,我深深地被其優美的文字、深邃的思想、廣博而翔實的素材所吸引。一口氣讀完全書后,腦子里閃現出的竟然是群體非理性及其控制這樣嚴肅的問題。以后的數日旅行中,欣賞著眼前祥和而美麗的景致,腦子里還是會不時地想,在革命或是改良的社會大背景下,如何理解那些屢有發生的群體非理性行為?誰會從中受益?誰又一直在付出代價?
躁動的群體非理性
在著名的協和廣場上,作者關注到了廣場焦點的方尖碑和邊界在視覺審美上的失衡。這很讓人奇怪,到了18世紀,法國的建筑師對廣場的設計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為什么在巴黎最要緊的盧浮宮前面的協和廣場是如此的不完美?
原先廣場的設計是很完美的,居于中心的是國王路易十五的巨大雕塑,其下還有象征著“仁慈、富裕、勤奮、節制、正義;勤學、智慧和詩情”八項美德的八尊雕像。這些復雜而雍容的設計作為廣場的重心點完全符合視覺審美的平衡要求。
但是在廣場建成26年后,法國大革命爆發了,巴黎人在攻下巴士底獄以后,“熱血噴漲,又不想回家,又不知干什么好。這個時候,最適合的消耗精力的事情,就是去搗毀什么類似路易十五廣場之類的大型象征。于是,路易十五雕像和其他雕像被砸毀”。據說在雕像被推倒的時候,一個圍觀的婦女被砸死了。今天,人們只能在巴黎歷史博物館看到殘留下的路易十五的一只青銅手臂。
和任何一場革命一樣,巴黎的革命也想著要有自己、的藝術,于是又在路易十五倒下的位置上豎起了一尊自由女神,還有三色旗,象征著“自由、平等和博愛”,這個口號響徹了法國大革命,直至今天仍在一些時空中余音尤存。但是在成立了“巴黎公社”后,立法會議被廢除了。這個“革命狂飆唯一的剎車裝置”被搗毀后,就幾乎沒有約束了。激動的民眾歡呼著讓這尊女神像在兩年內見證了一千多個生命被當眾絞死的場面。
這是一個噩夢,醒來后的人們還是有點茫然。在革命熱情逐漸衰退,巴黎人開始恢復起碼的藝術感覺以及對公共構筑物的藝術審查,重構廣場重建方案。一切尚在爭議中,“復辟”又開始了。這個廣場成了巴黎的傷口,國家又在血雨腥風和動蕩飄搖中了。廣場失去了中心主體,連個名字都沒了,只是一塊空地。太多的起義革命以及之后的反動復辟,一切都在躁動不安中。就在這時候,埃及國王送來了國禮一盧克索方尖碑。于是,它被豎了起來。在經歷了太多沖突、太多鮮血之后的廣場,仍然叫“協和”。
不論是以什么名義,不論是在何時、何地,個體或群體的非理性,或者說瘋狂帶來的后果是災難性的,文明沒有得以傳承反而遭到粗暴地踐踏。那些永遠留存的鮮明印記,讓人們對那些為此付出-的代價想忘也忘不了。
理性的妥協
在群情激動的情勢下提妥協,會被指責為投降和懦弱。但是平心而論,妥協是需要非凡的冷靜和超常的智慧。布什總統在第二任就職演講中仍然提到“在美國的自由傳統中,有費城制憲時的妥協先例”。在《帶一本書到巴黎》中,作者詳述了這個奠定美國憲政基礎的妥協。
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前后相差不過十來年,兩國幾乎在同一時間制憲。美國制憲是關起門來的,由精通法律酌人參與。門外,是安靜地等待中的美國。制憲參與者們清醒地意識到,這是制度的內在變革,而不是形式上的轟轟烈烈。
制憲的參與者是民眾推選出來的代表,他們深切地理解到民眾是就此把一切都托付給了他們。期間有激烈的辯論,但必須有退讓和妥協。在開會辯論議題之前,由牧師帶領他們頌念“請放棄唯我正確”的禱告詞。
到最后簽字的時候,沒有弓個代表的要求是全部達到的,但是他們都覺得只能有所妥協。那些在會場之內曾經以最激烈的言辭爭辯卻被迫妥協的代表,回去之后不是忿忿不平地發動一場新的革命,而是努力向民眾解釋勸說,使憲法得以實施。從此,美國人“安安頓頓地,在有生命的尊嚴和自由的前提下,追求個人幸福的日子”。
而法國則完全不是這種平淡無奇的樣子。法國總是充滿激情的,制憲會議始終處在漩渦中。暴力政變和暴力鎮壓交替進行。常見的場面是“祖國處于危險之中”,“巴黎上空再次響起革命的警鐘,起義人民紛紛聚集”。
并不是說理性一定意味著妥協,但是社會整體結構復雜,要容納多層次、不同群體的利益,所以一定需要妥協。而作出這種妥協需要勇氣,更需要理性。
有趣的是,對照中國盼隋況,好像是在體制內的人往往更容易接受理性的妥協觀點,而體制外的人則多主張激進的革命。以外交為主線,反映中國簽署《巴黎和約》過程的影片《我的1919》,似乎印證了我的這個看法。看著影片中鏡頭前掠過的巴黎種種場景,我竟然產生出一種恍惚的時空交錯感。其實;沒有區別,對所有的民族都是一樣的,躍躍欲試中的激進,被鼓舞的民眾可能總是歡呼雷動的,甚至是殺聲震天的。盡管期間,總是會有鮮血染紅他們襤縷的衣襟。
非理性后的“記愧”
更多的時候,很多的人是缺乏清醒意識的,在莫名其妙間似乎有點身不由己地做著各種事情。所以,在非理性過后,似乎應該覺得慚愧。錢鐘書在為楊絳的《干校六記》校定本(1991年)寫的序言中說,“記勞”,“記閑”,記這,記那,不過是社會運動這個大背景的小點綴,大故事的小穿插。六記之外還應該再加上一記,那就是“記愧”。
普通人需要“記愧”,杰出的人物也需要“記愧”。這慚愧之情或者是因為沒有擦亮眼睛,或者是因為怯懦。我想或許還有意志不堅定,或者事態發展屬于自己始料未及,無法控制,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帶一本書到巴黎》中提到的若干事例,讓我唏噓不已。
在法國大革命中,攻占巴士底獄是一個重大的事件。那是許久以來對舊制度累積起來的宿仇。發生了武力沖突,革命者用炮轟,最后守軍彈盡援絕,監獄被攻打下來了,近百人為此付出生命。大門打開了,里面只有七個罪犯!民眾在熱血沸騰,槍口滾燙冒著輕煙。不知道有人在感到興奮和刺激之余是否想過,其實不轟倒巴士底獄的高墻,也可以救出那七名囚犯?而且,更富有悲喜劇色彩的是,那七個被釋放的囚犯中其中一人已經完全適應監獄生活,被解放后反覺得茫然,又請求繼續被關押,直至死亡。那些轟轟烈烈地投入到攻打巴士底獄的行動中的人們,那些動輒就攜帶“短刀斧頭涌上街頭”的人們,回首不知作何感想?
到巴黎的游客們常購買的屬于巴黎式浪漫的一種紀念品是工藝晶斷頭臺或者是斷頭臺形狀的耳環。這種工藝化的處理使人們全然看不出其原形的殘酷了。當初,為了使死刑的行刑方式更加人道,蓋勒廷博士設計出了斷頭臺。他開始四處游說,試圖說服大家接受他關于死囚關懷的主張,但是他的努力不僅不被接受還遭到嘲笑。幾年后,他的發明被廣泛使用了。但是我想,他不僅不感到欣慰,反倒應該是覺得慚愧無比,或者確切地說非常后悔吧。他的發明被推廣的原因是,在大革命中,人們動轍被處死刑,劊子手沒有時間磨斧頭!蓋勒廷所設計的斬首機器自動化程度高,殺人的速度非常快,在這一點上非常符合“革命的需求”!
法國大革命的領袖之一丹東宣稱“我們必須使我們的敵人膽戰心驚”。在大革命行動中的九月大屠殺中,一名記錄者寫到,自己走過一個地方“一腳就踏入了齊膝的血污中”,那個地方是個監獄,在五小時內,殺死了220個人。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無論歷史學家們多么努力,都無法確定死亡的人數。無從得知那些發動民眾運動的人面對此等事實是否有稍許的悔意?
或許有意無意間,他們是忘記了。慚愧常使人健忘,事實上,人們對于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愿記起,因此,這些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凈。或許這愧意原本就是不應該記得的吧。因為慚愧會使人畏縮、遲疑,耽誤了急劇的生存競爭,所謂的人之“七情”中就沒有慚愧這一說。或許忘卻也好,可以輕松地活著,好有情致去欣賞巴黎色彩豐富、流動繁忙的街景?
這篇短文寫到結尾了,我還是無法對自己開頭就提出的問題自信地給出答案。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今,群體非理性行為都時有發生。可以說,沒有誰是從中受益的,即使有的人會有一時的顯赫和榮耀,但是他們自己或者他們的親人都很有可能被送上斷頭臺。這在拉法耶特的故事中最能體會到了。可以說,所有的人,個體也好,群體也罷,都一直在為此付出代價。理性的人們所能做的或許只是設計出一個好的規則,能夠對不同人的不同訴求有包容性和回應,讓個體的興奮、激情、抑或沖動,不過多地影響到他人,或許這也是法律的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