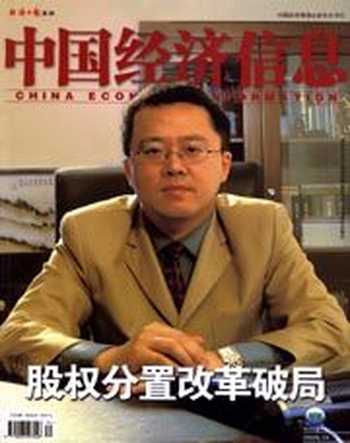中國企業 海外并購福禍相依
楊曉妍
1979年,北京市友誼商業服務公司同日本東京九一商事株式會社合資在東京開辦了”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中國對外開放以來第一家海外合資企業,標志著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開始。時下,中國海洋石油公司提出了以185億美元收購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除此之外,至少有上百個大型海外并購項目在醞釀、談判之中。一個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時代就這樣潮水般的涌來。
近日,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向美國優尼科公司發出要約,出資約185億美元,以全現金方式并購優尼科公司,這是迄今為止涉及金額最多的一次中國企業收購海外企業行動。海爾集團近來也宣布出資12.8億美元,參與競購美國家電生產商美泰公司。包括去年底聯想集團境外收購在內的一系列巨額收購戰,標志著中國企業正在大步走向世界。
海外路線是捷徑還是無奈
通過并購實現企業快速發展已經成了企業制勝的法寶。對于雄心勃勃的中國企業來說,這是實現國際化目標的最迅捷的方式。通過海外并購,不但可以打破國外企業的技術、專利、管理經驗和營銷網絡的壟斷地位,還可以把并購來的技術、專利以及自我更新換代的專利、技術與本土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及巨大市場空間結合起來,發揮出整合后的競爭優勢,從而提高與同行業強手競爭的能力。
從市場的角度來看,按照GDP8%的增長比例,中國企業的海外業務即使從零開始,在20年之內就將超過國內業務,為此,相當部分中國企業必須成為全球營運的企業。再則,國際化是雙向的,作為WTO的成員,國內已然是國際市場的一部分,若不能夠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企業無疑是坐以待斃。
從資源的角度看,由于中國的礦產、能源、木材等戰略性的資源總量有限,難以滿足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需要,通過國際并購的方式在全球范圍內尋找資源儲備、支撐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海外并購是企業在實踐著“走出去”的國家發展戰略。中海油志在并購尤尼科就是企業界典型的代表。
中國市場在全球市場份額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例,跨國公司普遍提升了中國市場在全球布局中的戰略地位。而隨著跨國公司把更多的制造和部分研發業務放到中國,國內企業依靠廉價勞動力產生的成本優勢日漸削弱,在核心技術、管理能力、資金實力、規模效益等方面的劣勢卻日益明顯。在此情形下,中國企業如果僅僅局限在國內,單一市場不足以支撐他們進一步長大,也難以進一步抗衡跨國企業。
并購IBM之前,聯想在國內市場占有近30%的市場份額,但他們在國際市場的銷售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在解析聯想為何收購IBMPC事業時,柳傳志不免感嘆:“不冒險怎么辦,窩在中國這個地方也是不行的,不突破慢慢就只有萎縮。”
并購路上變數太多
海外并購充滿太多的未知變數,當TCL公司宣布收購法國湯姆遜公司的電視機和DVD機生產部門時,分析師和投資者紛紛稱贊這是中國公司在全球崛起的一個里程碑。TCL移動在和阿爾卡特宣布合并相關業務的公告中也宣稱,合資公司擁有市場互補、強大的品牌力量、制造上的協同效應、更加豐富的產品線、世界領先的共同的聯合研發實力等并購優勢。
把歐洲的技術和營銷知識同中國低成本的制造業結合起來,創造全世界最大的電視機生產商,這聽起來似乎非常理想。但是,這種想象還沒有來得及一一驗證,就被并購帶來的巨大虧損所淹沒。業界最新看到的是,曾經在中國市場上迅速崛起的TCL移動以極快的速度滑落,今年一季度他們交出了一份虧損3.86億港元的季報。香港中國光大研究的分析師珍妮弗·蘇說:“以前,我們對這種并購相當樂觀。”但是現在,她說:“他們錯誤地判斷了對所收購的企業扭虧為盈的能力……我們大家都錯了。”
遺憾的是,很多企業家只注意到了企業自我發展的不易,卻忽視了并購式拓展只是從一個難題轉換到了另外一個難題的事實,就像千斤重擔從一個肩上換到了另外一個肩上,同樣考驗中國企業的實力和智慧。而且因為收購是一種大投入、大運作的經營方式,風險更加集聚,稍有不慎,就可能導致企業多年的積累毀于一旦。
并購企業“死穴”在哪
并購研究專家從大量的企業并購案例中發現一條重要的規律:收購是否成功主要是看收購方能夠給被收購企業帶來什么,而不是從被收購企業獲得什么。正是這條規律點中了中國企業的死穴。
聯想并購IBM的PC業務之后,把企業總部移到了美國,CEO也換成了原IBM主管電腦業務的副總裁沃德,高層團隊中來自原IBM的人員占據了近一半的數量和關鍵的職位,這固然有利于穩定原IBM的員工和客戶,但也有人難過地反問:如果一切都是IBM原來的樣子,那么本來虧損的IBMPC業務又憑什么扭轉?
TCL和阿爾卡特的組合也是如此。兩家公司在組成合資企業之后,僅僅是增加了數百人的研發和銷售團隊,人員開銷和管理費用成倍翻番,這成為導致合資的T&&A業務虧損上升的直接誘因。
與此同時,在近期炒得沸沸揚揚的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公司事件中,中海油的報價比競爭對手雪佛龍公司多出近20億美元,雪佛龍坦言收購后將裁員以壓縮成本,而中海油卻慷慨承諾不影響美國本土員工的就業。因此,有觀點指出這些優惠條件是否值得,將來是否會成為中海油難甩的包袱。
不管怎樣,所有的事實都反映了一個本質原因,那就是作為收購方的中國企業無法給并購后的新企業帶來能夠產生競爭力的“中國因素”。而事實上,這些失敗的企業并不是被中國企業打敗,而是受挫于第3方企業,比如阿爾卡特、西門子是敗在諾基亞、摩托羅拉、三星的手下。IBM敗在康柏、戴爾的手下,在此前提下,中國企業不敢以勝利者的姿態去接收,為此,他們必須接受被并購企業提出的要求:人員不能裁,工資不能減,管理制度不能改,整體的管理甚至還要受被并購方所控制。
并購企業走出去的策略
TCL的坎坷、聯想的前景不明和海爾新并購的延緩,已讓我們開始為中海油的選擇感到一絲憂慮。這不是杞人憂天——一方面,國際經驗已真切顯示,并購之路既非捷徑,更非坦途;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在跨國并購中表現出來的稚嫩,讓人深刻感受到我們還沒有底氣十足。不能叫停剛剛起步的跨國并購,也不能挫傷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信心,但如何走出一條獨特的跨國企業發展之路,需要中國企業家的“雄才大略”,但更需要一系列的反思。
麥肯錫上海分公司咨詢師JonathanWoetzel稱:一個品牌的內涵遠遠不是單憑技術就可以闡釋的,它是一個企業一切因素的總和。審視目前條件下我國企業的狀況,雖然技術上沒有較多的優勢可言,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建立自己的品牌。而且,品牌正是我們與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競爭的依托。
中國企業必須尋找靈活的的方式進入國際市場,并且要注意經營模式的動態調整。受東道國各種投資法規的約束,許多企業在進入之初選擇合資的方式,這也是基于對各種風險防范的考慮。隨著條件的變化,這種方式可以適當地進行調整和優化。
企業的價值活動可以分為基本增值活動和輔助性增值活動。其中基本增值活動又分為上游環節和下游環節。如果跨國公司的優勢在于價值鏈的上游環節,則應當采用全球性戰略,如果優勢在下游環節,則應當采取地區性的產品策略。
跨國公司關鍵是要保持在戰略環節上的比較優勢,并不需要在所有的環節上都保持比較優勢,很多非戰略環節可以外包出去,盡量利用市場合作降低成本與風險。
中國企業在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跨國直接投資時,應當辨別、分析利用何種價值鏈上的比較優勢。中國企業在進行跨國直接投資時,可以適當地追求在價值鏈的上游環節有所建樹,然后隨著企業實力的發展壯大,在技術、資本條件比較成熟的條件下,逐步實現向下游環節的突破。
張瑞敏把企業國際化簡潔為“三步走”:“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可以肯定的說:走出去——方向是正確的;走進去——成長是艱難的;走上去——霸業是輝煌的。海外并購不是企業國際化的唯一方式,也不一定是最佳的方式。適合企業自身發展的才是最優的方式。
背景鏈接?
△2005年6月,明基無需支付任何現金便獲得了整個西門子手機業務,相反,西門子卻將為此次出售支付價值2.5億歐元的現金和技術服務。通過此次收購,明基一舉成為全球第四大手機品牌,還完全獲得了西門子在手機領域擁有的1000多項專利。
△2004年12月,聯想以支付給IBM6.5億美元現金加6億美元股票的代價,接受了IBMPC業務的全部業務,以及IBMPC所帶來的5億美元凈負債。此舉使得聯想成為僅次于DELL、HP的第三大品牌。同時,聯想還獲得了IBM在個人電腦領域的全部知識產權。
△2004年7月,TCL與法國湯姆遜合資組建TTECORPORATION(簡稱TTE),成為全球最大彩電企業,TCL集團旗下的TCL國際控股和湯姆遜分別持有TTE67%和33%的股權。2004年8月,TCL與阿爾卡特組建手機合資公司TCL持股55%,阿爾卡特占余下45%股份。TCL通訊將投入5500萬歐元,阿爾卡特將投入4500萬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