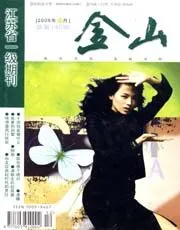京峴山拾夢
王申春
最早知道宗澤的名字,還是“文革”后期上小學時,在一本無頭缺尾、紙張泛黃的宋詩選集上,有一首他的《早發》詩:“傘幄垂垂馬踏沙,水長山遠路多花。眼中形勢胸中策,緩步徐行靜不嘩。”短短二十八個字,樸素平實,描繪了一支軍容嚴整、軍紀嚴明的隊伍踏沙前行,從容不迫的情景,同時彰顯了愛國將領收復失地、胸有成竹的堅定決心,令少年的我心馳神往,敬佩不已。后來投筆從戎,從書中了解到許多關于宗澤的故事,知道他忠勇愛國,知道他足智多謀,更知道他啟用提拔了年青的岳飛,使之走上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之路……種種信息,盡管東鱗西爪,但對宗澤其人的敬重和崇拜與時俱增。
今年春夏之交,由南京調鎮江工作。習慣性先查閱研讀當地地圖,無意中發現城市的東郊,在一座叫京峴山的山腳下,赫然標著“宗澤墓”三個字,附近還有一條以宗澤命名的馬路。霎時,積淀心中多年的崇敬之情再度涌動,同時也生出幾許疑問,只知道宗澤死在抗金最前線的河南開封,怎么歸葬在江南之地呢?不愿等待,恨不得生出雙翅,即刻飛往京峴山。
為了使這次喜出望外的拜訪更具歷史內涵,我仔細閱讀了《宋史·宗澤列傳》。宗澤字汝霖,婺州(今浙江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侵中原,涂炭生靈,攻陷首都汴京(今開封),隨手擄走徽、欽二帝。宗澤奮不顧身投入抗金斗爭。金兵退出開封城后,經愛國名將李綱力薦,宗澤以六十九歲高齡臨危受命,出任開封府最高行政長官。
短短幾個月,宗澤率部擊退金兵十余次進攻,獨撐大局,聲威大震,“臨戎盡瘁賴有公,收拾中原惟一手”。因而,“金人聞其名,常尊憚之”,呼其“宗爺爺”。
天上下起蒙蒙細雨,像為我的這次歷史性的探訪營造幾分悲壯的氛圍。在寬闊平坦的宗澤路上,我向路人打聽墓址,有人一臉茫然,搖首不知;有人指東望西,似是而非。我不敢責怪他們。本來嘛,身處太平盛世,一心奔向小康,還有多少人愿意念叨那些遙遠的陳年舊事呢?耐著性子邊走邊問,跑了不少冤枉路,折騰了近一個小時,才在一條正在拓寬的公路旁,找到了墓地。
京峴山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峻拔,這個當年秦始皇命三千囚徒拚死開鑿以泄東南王氣的名山,猶如一條盤行屈曲的游龍靜臥在長江南岸。宗澤墓坐落在山腳下,坐南朝北,四周綠樹成陰,蒼翠欲滴。墓道前矗立一座三門四柱的青石牌坊,中央兩根立柱的正面鐫刻著一副描藍對聯:“大宋瀕危撐一柱,英雄垂死尚三呼。”牌坊像一位忠誠勤勉的歷史解說員,反復呤誦著這兩行帶血攜淚的詩句,不厭其煩地向世人述說著老英雄最后的故事。
為早日北渡黃河、收復失地,宗澤一邊“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杰”,自謂渡河克復指日可待;一邊前后二十四次上疏已逃往南方的宋高宗,提出渡河復國的具體計劃,并請皇上還京督戰。貪生怕死的宋高宗,既畏敵如虎,聞金色變,又怕父、兄一旦返回,自己將失去剛剛坐上的龍位。一伙奸臣緊緊圍繞在宋高宗身邊,竭力迎合軟腿皇上“一保性命,二保皇位”的既定方針,對宗澤等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竭盡壓制、排斥、打擊之能事。宗澤眼睜睜看著打過黃河去的收復之計化為泡影,憂憤成疾,飲恨而亡。死前長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部下問他還有什么囑托,他“無一語及家事”,而是揮舞空拳,三呼“過河”。“堪嗟事半業未成,三軍慟哭星墜營。”噩耗傳來,開封軍民哭聲震天。他的靈柩由兒子宗穎和愛將岳飛護送南下,與早年在鎮江病逝的夫人合葬在郁郁蔥蔥的京峴山下。
穿過牌坊,馬上就要見到仰慕已久的英雄之冢了,我的心劇烈地跳動。沿著四五十米長的墓道疾步匆匆,拾級而上,我仿佛完成了一次歷時三十萬個日日夜夜的時空穿越。墓道邊野花盛開,星星點點,與遮天蔽日的冬青松柏上下呼應,虔誠地呵護著人跡罕至,略顯寂寥冷清的墓園。一塊白云石碑,上刻“宋宗忠簡公諱澤之墓”。碑后巍然隆起一座高大的墓冢,素石圍砌,芳草覆頂。我在碑前脫帽肅立,然后緩步徐行,繞墓包一周,靜默懷想。
雖然滄桑歲月八百年,歷史長河已經拐了無數道彎,那一幕幕或激昂慷慨,或屈辱流淚的活劇早已化為史書上一粒粒刻板制式的五號字;雖然昔日揮戈殺敵,振臂疾呼的熱血身軀,早已化為累累白骨,融入蒼茫大地,但是,那樣一種精神、一種氣節、一種神韻、一種風范,卻真真切切地在人世間留存下來。不是嗎?無數英雄豪杰的歸葬之地,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青山綠水之間,猶如聳立起一尊尊不朽的坐標,好似舞動起一面面奪目的旗幟,時時刻刻在昭示呼喚著什么。它一下子拉近了今人與先者的心靈間距,它讓你可以盡情傾訴心中的仰慕和崇敬,它讓一個個晚生后輩圓了崇尚英雄、傳承英氣的美夢。
(作者單位:駐鎮73860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