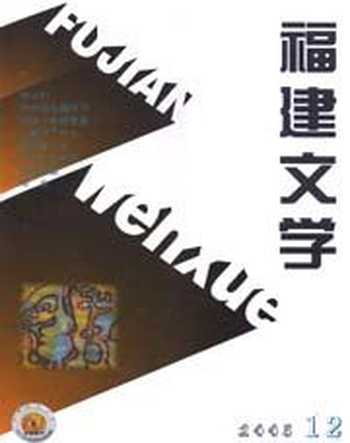何處得秋霜
盧六周
偶然攬鏡,不再顧盼自雄。額上顯明有力的橫紋,儼然是吳道子的“莼菜苗”,心想那是抬頭紋,可低頭也還是那樣。而最令人怵目驚心的是,鬢角多了一縷白發,總讓你覺得秋霜已得,人老珠黃。于是心頭一緊,“往事依稀渾似夢,都隨風雨到心頭”。平生一些小恩小怨、小溝小坎、小曲小折,一時波瀾翻覆,釀成不盡的人生酸楚;既而黯然神傷,胸臆難平:“艱難苦恨繁雙鬢,潦倒新停濁酒杯”、“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明知遲暮之悲未免言之太早,奈何“秋士”之心,睹物傷懷,便也不由得自己不把這“后事”提前個二三十年來加以感受,卻每每忘了或者忽略了自己還有大半的青春儲備尚未開掘,便認定“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了。當代中青年的苦悶由是可見,“美麗”的“中青年憂郁癥”亦由此生也。
心既老,秋霜就不僅是發上的事情了,更要命的是一重一重地飄在心坎上,像殘冬的余寒,令人冰涼不堪。于是閑愁像不死的幽魂鬼魅,纏得你呼吸艱難,眉角難舒。看著你一天一天的消沉老成下去,知情的人說:“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不知情的人卻說:“越來越成熟了,越發深沉穩重了。”不知是哪個人喜歡杜撰:“成熟好啊,現在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就喜歡成熟一點的男人。”那口氣仿佛是說:“只要你成熟穩重一點,就大可不必擔心沒有好姑娘尋上門來。”什么邏輯我也搞不大懂,只是發現,連年輕的小伙子也搶著以“老”為尚,真的認定這便是成熟,因此也競扮“成熟”。“老”化趨勢遂成潮流,張口便是“哎呀,不行了,人老了,就看你們的了”,閉口便是“你們這些年輕人啊”,儼然一副飽經滄桑的世紀老人的神態。同輩中的同齡人一旦在你的稱呼之前冠以“小”字,你就非得跟他急,覺得他怎么這么不要臉,企圖把你從他面前給“小”下去;叫個“老X”什么的,你卻樂得“老”一回,覺得臉上榮光。可當自己反過來稱呼他人時,最喜歡的卻往往是對別人“小”字加身,以“小”賣“老”。中國人不是喜歡排資論輩嗎?在這點上,資歷的深淺年紀的長幼往往和別人對你的尊重程度成正比,自然也就有些小伙子愿意加盟“老”字輩了。
我們并不否認,生活的磨難也曾經使一部分年輕人無論在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確確實實地“老”,下去了。“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思想負荷過大,心事重重,整天愁云慘霧,能不“老”嗎?
他們滋生煩憂、引發愁悶的容易度令人難以置信:學習上稍微受挫,工作中稍有不順,生活上稍不稱人意,便終日落落寡歡,感慨多多,甚或要對生活,對自己失去信心,總覺得跟別人相比,自己的命運要坎坷曲折得多,人生要灰色黯淡得多。于是,一些悲天憫人的情緒,一些老年人才有的人生況味,他們也不妨有了起來,以致一夜之間,秋霜盡染,華發早生,不負責任地“老”下去了。頹廢哲學由是生也。生活的小磨難使他們“老”起來的,不是心態上的更加成熟穩健,不是“吃一塹,長一智”,變聰明起來,老到起來,而是心態上日趨老化,成日只懂自悲自嘆,最終因經不起挫折而消沉下去,他們身上缺少的正是一種韌勁。
因此,較之青春早衰的青年后生,我似乎更欣賞那些忘了年庚的“老伙子”們。他們樂觀,但又不乏智慧;青春,卻又不失深沉。盡管幾歷人世滄桑,卻始終不會在歲月的風雨面前激情盡失,干枯了生活的泉眼。
不過,話說回來,人之老也,乃生理規律的題中之義,不可抗拒。倘使非得色厲內荏地大加抗議,并由此導出一幕幕“老來俏”的鬧劇來,那無疑要叫人大為厭惡。梁實秋說:“年屆不惑,再學溜冰踢毽子放風箏,‘偷閑學少年,那自然有如秋行春令,有點勉強;半老徐娘,留著‘劉海,躲在衛生間里穿高跟鞋當作踩高蹺地學走路,那也是慘事。人生的妙趣,即在于相當的認識人生,認識自己,從而做自己能做的事,享受自己能享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