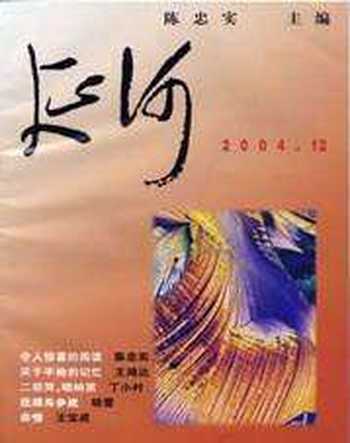去城里看電影
1
坐在自家屋檐下的三子,聚精會神地看著走廊上的幾只麻雀在嘰嘰喳喳地搶食。這時,突然聽見有人喊他,三子,到城里看電影去———
三子的家門口是條砂石馬路,那是通向邵陽城里的,至于到邵陽之后,馬路再通向哪里,三子就不知道了。三子抬起頭一看,是窯山的一群朋友,喊他的是個叫五佗的人。五佗這時又朝三子用力地揮了揮手,然后繼續往前走。
馬路上,陸續地出現了許多窯山里的大人,當然是一幫年輕的男女,他們肯定也是去城里看電影的。窯山里的人,通常消息靈通得多,比如說,城里有什么好電影了,發生了什么武斗事件了,甚至于有什么好的布匹賣,他們不用多久就知道了。三子就是經常從五佗他們那里,知道城里發生的許多事情。
窯山和農村其實是混在一起的,錯落交織,又沒有圍墻,所以,你很難用清清白白的框框劃分開來。三子雖然是農村孩子,但是他經常和窯山的孩子在一起玩耍。三子禁不住誘惑,猶豫地往屋里看了一眼,母親愁眉苦臉,正在給父親熬草藥,屋子里彌漫著刺鼻的藥味。父親在農校教書,被揪了出來,打斷了一條左腿,哼哼嘰嘰地躺在床上已經兩個月了。
三子遲遲疑疑地說,娘,我跟五佗他們去城里看電影……他擔心母親不同意,母親也許會責備他,你父親傷成了這副樣子,你還有心思看電影?
母親在光線黯然的屋子里唔了一聲,三子的心情頓時高興起來,他知道母親同意了。緊接著,三子站起來,飛快地朝馬路上跑去,在后面大喊,五佗,等等我,我來了———嚇得那幾只麻雀噗地一聲飛走了。
三子氣喘吁吁地追趕上五佗他們,滿臉興奮地問,什么電影?
五佗高興地說,《賣花姑娘》,朝鮮片子。
三子看看那些同伴,個個臉上也是興高采烈的,便激動地說,朝鮮片子我還沒有看過呢。
三子是第一次跟著人家去城里看電影。
五佗接著說,誰看過?都沒有看過的。五佗指著那些大人,他們也沒有看過。又擦了擦鼻涕。五佗的鼻涕像是下粉條似的,不斷地流下來,鼻孔下面流出了兩道紅色的淺淺的槽。
馬路上三三兩兩地走著許多人,個個都很興奮。有些大人把煙抽得滋滋響,猛猛地抽上一陣,便用手指頭重重地一彈,煙屁股便在空中飛了出去———這里面有興奮加上抵御寒冷的雙重因素。大家扯開步子,勁鼓鼓地一邊往前走,又一邊議論道,聽說很好看的,那些女演員長得非常乖態,看的人很多,如果能夠買到票就好了。還有人非常有把握地說,聽說在邵陽演三天,應當說票是沒有問題的。還有人跟著說,我聽說沒有誰看完之后不哭的,電影院里充滿了一片哭聲,像死了老娘一樣。馬上就有人提醒說,莫亂說啊。那個人立即就閉上了嘴巴。
三子他們跟在大人們的后面聽。三子突然想起自己身上沒有錢,沒有錢怎么買票?沒有票又怎么能夠進去?他想問五佗帶了錢沒有,如果帶了,便向他借,以后再還。但三子終究沒有問,他想,他們肯定有錢的,到時候再借不遲。
五佗側過臉,問走在身邊的三子說,你會不會哭?
三子說,會哭,你呢?
五佗說,肯定會哭。
走在一起的那些小同伴也說一定會哭的,又說,到了那時候,電影院里一片哭聲,你不哭都忍不住的。
三子加入了看電影的隊伍之后,就完全忘記了斷腿的父親還躺在床上,母親坐在灶邊熬草藥。他一邊奮力地走著,一邊尖著耳朵聽人家說話。他而且想像自己在電影院里嚎啕大哭的情景,影片中的人物對話以及音樂完全聽不清楚了,都被觀眾的一片哭泣聲淹沒了。他還想像坐在身邊的五佗哭起來的時候,鼻涕肯定像永遠也流不完,似長長的粉條一樣,分不清楚哪是眼淚哪是鼻涕了,不時用手揩來揩去的。想起五佗那副邋遢樣子,三子情不自禁地笑起來。
五佗問,你笑什么?
三子連忙搪塞說,沒笑什么。
五佗滿有把握地說,你還笑?到時候,你哭都哭不贏的。
窯山離邵陽四十里路,路途要經過老龍潭,范家山,高崇山,黃陂橋,火車站,雙坡嶺,然后再進入城里。通往邵陽的汽車也是有的,只不過每天下午兩點才有一趟,人們都等不及了。大人們走得很快,恨不得幾腳就走到城里。三子他們生怕跟不上,便聽不到那些有趣的議論了,所以幾乎是小跑。還有一個原因,只有大人們才知道究竟是城里的哪家電影院。不跟上他們,一旦進了城,三子他們就會像一群無頭蒼蠅四處亂竄,找不到地方。
他們出發的時候,大概是上午八點多鐘。天氣不太好,北風呼呼地吹來,雖然沒有下雨,但那風卻很厲害,刮在臉上像刀子一樣生痛。陰沉沉的空中不時地飛揚著被風吹起的紙屑或枯葉或稻草。三子他們的臉上紅紅的,尤其是鼻尖,紅得更是厲害,簡直成了紫色。一半當然是因為激動。
三子戴著父親的一頂破舊的呢帽子,有點大,帽檐軟塌塌的,遮住了眼睛。所以,三子干脆將帽子歪歪地戴著,軟塌塌的帽檐便在腦袋的一側不斷地擺動著,有一種滑稽的效果。寒冷的天氣一點也沒有影響他們的情緒。他們的精神非常飽滿,沒有因為路途遠而產生一絲泄氣。
馬路兩邊的田野,空空蕩蕩的,顯出滿目凄涼。不時地飛起一只寒鳥,哆哆嗦嗦地便很快消失了。農舍飄出的炊煙,弱不禁風,一股股黑黑地吐出來,立即被風吹得無影無蹤了。汽車不時地來去,搖搖晃晃,便掀起漫天的黃色灰塵。所以,等到汽車一過,無論大人或小孩,都要反轉身子,咬牙切齒地朝著汽車屁股大罵,你要死了——
罵上一陣,又心滿意足地大笑起來,然后繼續往前走。
2
三子他們走到邵陽城里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點鐘了。大家的肚子餓了,咕咕地叫起來,可是,誰也沒有提出來先吃點東西,包括那些大人。可見眼下吃東西似乎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大人們的心情似乎更加迫切,目不斜視,馬不停蹄地朝橋頭走,三子聽他們說是紅色電影院。他們顧不得看街上的風景了,三子即使是第一次來城里,也沒有對城里表示出一種驚奇之感,只是感到那街道是水泥的,實在好走多了,又沒有那么多的灰塵。三子緊緊地跟著人家往前走,認為看完電影之后,再慢慢地看街景也不遲。
過了一座大橋,等到他們匆匆地趕到紅色電影院,天啦,簡直人山人海,一片喧嘩之聲。黃色的灰塵似薄霧一般,若有若無地飄蕩在上空。連大街上也站滿了人。根本看不見售票窗口,窗口已經里三層外三層地被人墻包圍了,就連一只狡猾的鳥也插不進去。在外面等著看電影的人,急切切的樣子,埋怨上一場電影怎么還沒有放完,并且不停地看手表。還有一些已經看過的人便站在一邊,好像舍不得離開,滔滔不絕地說起電影怎么怎么好看,說著說著,居然就流淚了。圍在身邊的人也跟著流淚,希望早點看到的心情就更為迫切了。當然,還有一些買到了票的人,坐懷不亂,臉上得意洋洋的,站在一邊耐心地等候著,但隱隱地,那臉上又流露出一種擔憂,這么多的人,到時候怎么擠得進去?
三子緊張地問五佗怎么辦,五佗說,跟著那些大人。可是,那些一起來看電影的大人,一眨眼,就全部不見了人影子,通通地消失在人群之中了,看樣子是都去各顯神通了。
五佗憤憤地罵了一句,這些人……真是像叫化子烤火,只顧往自己的胯里扒。他是罵那些大人,一進了城就丟下他們不管了。又說,我們既然是一起來的,就要一起進去看,然后一起回家。
三子和同伴們都點了點頭,不由緊緊地挨在了一起,他們的確有點看不起那些自私自利的大人。
五佗看了看這個混亂的陣勢,深思熟慮地說,我們只有等到這場電影放完之后,進場的時候再混進去,這么多的人,我就不相信混不進去。
三子聽五佗這么說了,懸在心上的那種擔心才噗地落了下來,這下好了,不要借錢買票了。
三子跟著五佗他們退回到人不多的地帶,憂心忡忡卻又耐心地等待著。那是大街上了,一群一群的人也在等待。有人還悠然地嗑著葵花子,將瓜子殼吐得滿天飛舞。
五佗擦了擦鼻涕,左右看了看幾個同伴,叮囑說,進場時,我們就不要講客氣了,一個跟著一個,不要掉隊了,一起拼命地擠,擠進去就是勝利。
大家又點了點頭。
三子看著這么多的人,像螞蟻一樣,本來是沒有多少信心的,聽五佗這么一說,信心又像炊煙一般地慢慢地升了上來。他不由地緊緊地握著拳頭,暗暗地在給自己鼓勁。他想,五佗他們既然能夠擠得進去,自己也一定可以擠進去。
那個破舊的電影院,被一片黑鴉鴉的人像鐵桶一樣地緊緊地包圍著,說不定會被人們擠垮,如果一旦倒塌了,肯定會砸死砸傷人的。三子不免想起父親被人打斷的那條腿,渾身一陣顫抖。他暗暗地保佑電影院千萬不要倒塌。
這時,人流突然騷動了起來,肯定是散場了,人們像潮水一樣地涌進涌出。那些從電影院里好不容易擠出來的男男女女,臉上還殘存著看電影時流下來的淚水,嘴里卻在尖聲大罵,擠死啊———,你娘手里沒有看過電影啊———。而外面的人卻充耳不聞,齊心協力地往電影院的大門口擠去,臉上充滿著興奮和渴望,眼睛炯炯發光,居然還異口同聲地起哄,嗬嗬嗬———好像在不斷地給自己鼓勁。
五佗見機會終于來到了,果斷地說,跟著我。五佗非常機靈,飛快地貼著一群大人的屁股后面,插進了洶涌的人潮之中。
三子便緊緊地扯著五佗的衣擺,其他的同伴依次地跟在三子的后面,也抓緊著衣擺。他們也情不自禁地興奮地叫喊,似乎需要不停地叫著擠著,就能夠擠進電影院。前進的速度十分的緩慢,有時進一步,又潮水般地退了兩步,那是因為觀眾還沒有完全走出來,便急于往外沖。進出雙方的阻力都相當大,真是人挨人,人擠人。三子覺得像困在了一只巨大的鐵桶里面,憋得要死,呼吸十分困難,前后左右的力量,像鋼鐵一樣殘酷無情地向他單薄的身子壓迫過來,似乎要將他壓成一個肉餅。三子突然產生了一個不好的念頭,我如果擠死了,我父母肯定會傷心死了。
三子這時突然感覺到頭上的帽子被擠掉了,趕緊騰出一只手來摸了摸腦袋,帽子果然不見了,他在肩上背上摸了一下,也沒有發現帽子。蹲下去在地上摸,三子是沒有這個膽量的,搞不好,人就會被踩死。三子不敢再找帽子了,騰出來的那只手又緊緊地抓著五佗的衣擺。但三子還是非常擔心,母親如果知道他的帽子丟失了,會不會罵他?
叫罵聲,吵鬧聲,哭喊聲,尖銳的聲音不絕入耳,簡直要將耳朵震聾了。三子想,我如果是個大力士該有多好啊,只需輕輕地一擠,便會將周圍的人通通擠開,讓五佗他們跟在后面,輕輕松松地向電影院的大門走去。或者說,是一個會飛翔的人也是很可以的啊,只需向上縱身一躍,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向門口飛去。可是,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個可憐的小孩,任憑人家擠來擠去。
三子心里其實有了一絲后悔,如果早知道是這樣擁擠而混亂的場合,他就不會來了。但是,他卻又無法抵御這個電影的誘惑。三子鼻子里癢癢的,那是灰塵在搗蛋的緣故。三子覺得那些干燥的灰塵沿著鼻孔進入了喉嚨,然后走到肺里去了。
三子他們都緊緊抓著衣擺,像一根牢不可破的鐵鏈。偶爾被人沖斷了,又趕緊死死地扯著,就像扯著一絲希望。人流仍然在艱難地進出,三子他們不屈不撓,終于漸漸地向電影院的大門口靠近了。
大門口有兩道狹窄的鐵欄桿過道,大約六七米長,剛剛只能容一個人走。由于人太擁擠,結實的鐵欄桿也是搖搖晃晃的,似乎會被人擠垮。看來,電影院也早就預料到了這場空前的擁擠,便做好了準備的,將大門半關著,僅僅留下狹窄的縫,讓觀眾們進出。十來個守門員穿著黃色的軍大衣,戴著紅袖筒,年輕而又人高馬大,一臉兇氣,一個個地仔細查票。若是沒有票的,絲毫也不講客氣,像抓小雞一樣,高高地抓起一提,就往一邊丟去,也不怕摔傷了人,而且破口大罵,你再打偷票,老子打你不死?所以,就經常聽到有人哎呀呀尖叫的痛苦聲。
三子他們眼看著就要進入了鐵欄桿過道了,心里激動不已。這時,五佗卻突然不再往前走了。三子剛剛緩過一口氣來,便驚訝地問,五佗,怎么不走了?
五佗絕望地說,看樣子進不去了,人家好兇的。
他們這幫人便停滯不前,后面的人大吼起來,擋路做什么?災狗!
五佗他們急忙往邊上站,站在了鐵欄桿的外面,但是,想出去一時又出不去,人真是太多了,他們只好緊緊地站在一起,被人們擠來擠去的,眼睜睜地看著有票的人擠進去。當然,也看著那些像他們一樣沒有票的人,沮喪地站在一邊。這時,經過三子他們身邊的一個女人,嘴里含著票,嘲笑地說,小屁股也想打偷票混進去?說得他們臉上泛起一陣難言的羞愧。
一直挨了半個多小時吧,該進去的已經進去了,外面才漸漸地松散一點,但這種松散也只是相對而言,其實仍然是比較擁擠的。許多的人,還在等著下一場電影,有些人則抱著僥幸的心理,希望能夠有人退票。還有一些人就擠近大門,遞煙給守門員,媚笑著,千方百計地跟人家套近乎,希望人家會高抬貴手放他一馬。
三子他們便趕緊趁機擠了出來,重新來到了大街上,一個個垂頭喪氣的,似乎已經看不到任何希望了。
五佗突然發現了什么,對三子說,你帽子呢?
三子摸摸壓得緊巴巴的頭發說,擠掉了。
五佗大方地說,沒關系,回去老子給你一頂。
三子怯怯地問五佗,我們……回去吧?
五佗好像沒有聽見三子的話,鐵著臉,仍然不心甘地望著眼前這一片混亂的場面,突然說,我們走。
三子他們以為是回家了,也就跟在后面。誰知五佗并不是往回走,而是繞過了一個很大的彎子,來到了電影院的另一側,他是想從窗子里爬進去。
可是,他們來到電影院的另一側一看,頓時呆住了。天啦,那一排窗子上全部站滿了人,大人小孩都有,但沒有女的。三子數了數,總共有八個窗子,每個窗子上起碼擠了五六個,姿態各異,但一律是彎曲著腰背的,因為窗口不高,不彎腰便看不見銀幕。窗戶上安著很粗的木欄桿,一格一格的,人們的雙手就緊緊地抓著它們,不敢松懈一絲,時時刻刻地充滿著緊張。窗子下面,還站著許多眼里充滿著希望的人,他們巴不得那些站在窗子上的人支持不住了,只好無可奈何地跳下來,他們便可以立即補充上去。
三子緊張地看著擠在窗子上的那些人,十分擔心木欄桿會被人攀斷,因為窗臺非常狹窄,僅僅只能踩腳,何況,又有那么大的力量全部聚集在木欄桿上面,只要一斷,肯定會有人猝不及防地摔下來。
三子正在惶惶地想著,這時,只聽見啊地一聲大叫,有人果真摔下來了。三子居然沒有聽見木欄桿攀斷的聲音。仔細往地上一看,那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跟三子他們的年紀差不多,人很瘦,頭上帶著一頂棉帽子,看樣子是摔斷了腿,他抱著左腿喊天喊地地叫,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三子再往窗子上一看,木欄桿并沒有攀斷,那肯定是這個小孩沒有力氣支撐了,卻又不愿意下來,一不小心,松了勁,于是就摔了下來。站那一排窗子上的人全都聽見了,轉過頭來,驚訝地看了看,然后,又漠不關心地返過頭去,繼續看電影。電影的吸引力顯然要比摔下來痛哭的小孩大得多。
站在離三子不遠的幾個男人,便像百米賽跑一樣,匆忙地朝小孩掉下來的那個窗子跑去,企圖占領那個空閑下來的位置。那幾個大人擠在窗子下,互不相讓,用力地推搡著,兇兇地吵罵,結果,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終于戰勝了對手們,他能夠憑借著身高,死死地抓著窗子上的木欄桿,然后艱難地爬了上去,甚至還回過頭來,朝那幾個沒有競爭力的灰頭灰臉的男人嘲笑了一下。
三子的心臟一下子緊了,不由地打了個寒顫,又想起了可憐的父親的那條斷腿。他和五佗他們一樣,瞪著大眼睛,驚恐地看著那個小孩。
那小孩抱著左腳,痛得哇哇大哭,卻沒有任何人來幫他。從他那乞求的眼光可以看出來,他是多么希望有人來幫幫他。可是,大家的眼睛時而淡漠地看他一眼之后,更多的則是盯著窗子,渴望另一個機會突然降臨。
站在另外一個窗子的男人,肯定被小孩這哭聲鬧煩了,轉過頭來,一臉兇相,大聲地吼道,你哭死啊,吵得我們都聽不清。
小孩顯然嚇壞了,哆嗦了一下,淚眼蒙眬地望著那些站在窗子上的人們,哭聲便收斂了一些。但那種尖細的哭泣聲,在冬天寒冷的大風中,像刀子一樣地鉆心。
三子暗暗地扯了扯五佗,低聲說,我們是不是去幫一下?
五佗猶豫地說,我們又不認得他,怎么幫?
三子說,那我們干脆走,這么多的人怎么看?三子其實不再忍心看著那個小孩了。他覺得再這樣無所作為地看下去,無疑是對那個小孩的一種殘忍。
五佗想了想,無可奈何地說,走吧。
三子這幫人立即穿過了熱鬧的街道,簡直像一群喪家之犬,根本無心看城里的風景了。他們的肚子已經餓癟了,也只能在一家家面館門前站站,聞一聞從里面飄出來的肉湯香氣,口水直往肚子里咽。三子以為五佗他們身上帶了錢的,誰料他們跟他一樣,沒有一分錢,只能看看罷了。然后,又繼續走。那些一起來城里的大人,始終也不見了,他們只好匆匆地往回趕,因為天色的確不早了。
他們在回來的路上,再也沒有來時那股興沖沖的勁頭了,情緒非常低落,不太說話,即使要說,也是憤憤地罵道,沒想到有這么多的人,螞蟻一樣多。他們本來不想走得太快了,但是,寒冷的天氣和空空的肚子,又逼迫著他們不得不走快一些。五佗的鼻涕流得更加厲害了,不時地狠狠擤一下鼻涕,甩了出去,并大聲地惡罵,流流流,流你的娘啊!
三子卻一直沒有說話,他害怕一開口說話,北風就會毫不客氣地灌進肺腑,那就更加的寒冷了。但他的眼前,總是恍恍惚惚地出現那個被摔斷了腿的小孩在不停地哭泣,他那痛苦的樣子,曲卷著的身體,以及無望地叫喊,弄得三子心里酸酸的。
三子有點后悔,要是幫幫他就好了。
我以后再也不來城里看電影了。三子又想。
4
三子回到家里,已是精疲力竭,全身發軟,這時,天已經大黑了。昏暗的燈光下,只見母親坐在灶火旁邊,低低地哭泣,那哭泣聲像寒冷的北風一樣,令三子渾身不停地發抖。母親紅著眼睛看了三子一眼,又繼續抽泣,顯然沒有注意到三子頭上的帽子不見了。
三子想看看父親,便一聲不響地走進父親的屋子里,床鋪上,父親卻不見了,三子驚慌地喊道,娘,爸爸呢?
又……抓走了……
姜貽斌湖南邵陽人,下過鄉、當過礦工、教師、編輯。現居長沙專事寫作。著有長篇小說《左鄰右舍》,小說集《窯祭》《白雨》《黑夜》《女人不回頭》《姜貽斌卷》,散文集《漏不掉的記憶》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