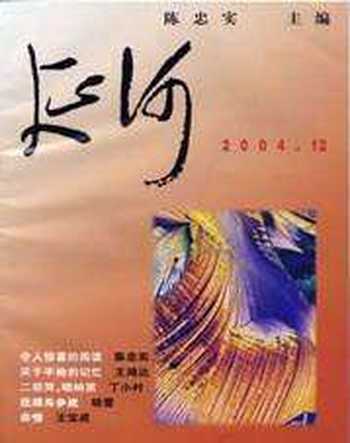陜西多出奇人
艾 涓
已記不清是因為什么原因,我請好友阿明畫了柳青先生漫畫。
記得是在辦公室里,正好有半張宣紙,便將漫畫隨意撕下貼在上面。也是巧合,這天我去向平凹君約稿,他正在寫字。平凹的字難求人人皆知,但我還是拿出這經過加工的有柳青先生漫畫的小紙片,請他題寫幾句相關的話語。大概因為上面有他尊敬的人物,阿明也是他的好朋友吧,平凹顯得很大方,信筆寫了起來,寫滿了這張紙片。字一如既往,隨意而自然,與神形俱佳的漫畫相映成輝。所寫話語更是表達了他的心思:“陜西多出奇人,現代以來,有于右任、柳青、石魯、張藝謀。而于、石、柳我皆未見過,張遇見一面。曉明今作柳像,算我見了先生。”這是平凹所推崇的陜西文學、書畫、影視四個方面的重量級人物。
這四個人物,在各自的領域中都是杰出代表,影響著這些領域的發展。于右任是國民黨的元老,他的標準草書開風氣之先,左右著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關于柳青與《創業史》,著名評論家閻綱有過精彩的評述,他說:“柳青一生熱愛農民,歌頌農民,最后變成農民。他取得農民的資格以后,便以中國農民真正的代表表現中國革命。他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以大量無可置疑的生動細節建造而成一座龐大的殿堂。作為我國社會主義農民運動行將到來和已經到來時各階層農民面貌和心理的忠實表現者,柳青的確是杰出的,《創業史》因此成為史詩性的名著。”這段話從人格魅力、藝術魅力和思想魅力上高度總結了讓中國文學驕傲的柳青先生。石魯,同樣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早在四十年代就以繪畫藝術反映人民戰爭生活,進行革命宣傳。解放后他潛心鉆研中國畫,大膽探索,勇于創新。其作品表現著強烈的時代氣息和獨特的藝術魅力,是長安畫派中的領袖人物。而張藝謀,也是以他的獨特風格馳騁國際影壇,為中國的電影事業發展創下了幾多輝煌。當然,如今的張藝謀,因其導演的電影《英雄》《十面埋伏》受到幾乎是所有娛樂媒體的責難,從《十面埋伏》公映以來,不間斷地有媒體在一邊倒的批評。偶見《西安晚報》上就有半個版的關于他的批評,一篇是《娛樂傳播“運動化”,進步?恐怖?》其中有北京電影學院教授蘇牧說,我是不能原諒張藝謀的。因為我認為,原諒了張藝謀,對中國電影的發展和生存,會更加不利。一篇是《名導朱延平:張藝謀已經“死”了》,朱導毫不客氣地說:“《英雄》和《十面埋伏》走的都是豪華路線,就是純粹的商業片。盡管炒作和拍攝非常成功,畫面精美、制作精良,但已經不能代表張藝謀本身了。這樣的片子只要有錢,任何一個導演拍出來都不會輸給他,只能算是一部不錯的商業片。嚴格意義上講,張藝謀已經‘死了。”
平凹推崇的張藝謀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和嚴峻的挑戰,為他的藝術。我自以為,張藝謀似乎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力,比如在電影的原材料———故事的準備上,就犯了嚴重的失誤。大家還記得讓他名揚天下的那幾部電影,諸如《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活著》等,每一部電影的故事原創都是其作品本身已在讀者中獲得了較高的聲譽,每一部作品都有著耐讀的故事情節。而后來的張藝謀的電影作品的故事,來自哪里,這里面又有多少成分是攙雜了張導的個人情緒呢?我想,這可能是張藝謀遭到全面攻擊的重要原因吧。
由平凹的題字說到現時的張藝謀,似乎跑題了,就此打住。
周明與文懷沙
周明先生是著名的編輯家、散文家和文學活動家;文懷沙先生是當代著名的國學大師、楚辭泰斗。以兩位重量級人物為題作文,是因了我所收藏的幾幅墨寶。
我收藏的“一生只流雙行淚,半為滄桑半美人”字幅,是2004年5月下旬召開的陜西文化資源保護與利用研討會上,周明先生為我書就的。題款:“錄文翁句贈艾涓。”文翁———就是文懷沙先生,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關于愛美和性的精彩評論。九十高齡的文翁,還經常騎自行車出入街頭,有人勸他出門坐車,不要再騎車了。他說,坐車人是不自由的,騎車人精神是自由的。騎車人只要不闖紅燈,可以東南西北自由行駛,坐在汽車里就沒有這份自由了。再譬如,路旁走過一位婀娜美女,坐在汽車里的只能看個瞬間,而騎自行車則可以下車駐足仔細觀之品之,人生賞美是一大樂事,失之則不再來!這是老人的美人情結。關于性,他以性命兩字作解:“性命,有性有命,無性即無命可言。”(大意如此)。這些年來,老先生對美的率性追求,流傳在文壇上的風流韻事,竟遮掩住了他作為國學大師和楚辭泰斗的光輝形象。我倒要說文懷沙先生可算是當代的奇人義士。我品味著老先生的鶴發童顏與風流倜儻,也感慨著耄耋老人竟有如此的炯然精神。這一聯句,恰到好處地印證了我腦海中所存留的文懷沙的形象……
然而,時隔不久,關于這一聯句,又有了新的話題。
10月10日左右,周明先生去寧波參加我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小說家、散文家和翻譯家王魯彥先生逝世60周年紀念活動,恰與文懷沙先生同機前往。我便請周先生求文翁為我題寫“虛室小品”四字。并求證“一生只流雙行淚,半為滄桑半美人。”聯句的寫作背景。很快,12日晚,我接到周明先生電話,一是告知文翁已題寫了“虛室小品”,二是講了“一生”聯句有出入以及聯句的寫作因由。
“一生”聯句的本來面目是“平生只有雙行淚,半為蒼生半美人。”大概是在1941年的某個季節,文懷沙對暨南大學附中的一位女教員十分鐘情,大有非此女不娶之念頭。他辭掉原來的工作,追到暨南大學附中應聘為國文教員。然而,文懷沙的癡情并沒有贏得這一女子的芳心。愛情的失敗,國家遭受外敵的侵入,使他感慨萬分,吟詠出了“平生”聯句。后來,柳亞子先生知道了文懷沙的情事并見到這一聯句,大加贊賞,有聯為證:“未嫁已傾城,君詩如美色。”
在寧波,文翁將“平生”聯書贈周明先生,并對自己的人生大發感慨。在談到和自己有過情感沖撞的女人,他說:“我只記她的愛,不記她的恨;只記她的恩,不記她的怨。”能見出老人的心性來。關于“平生”聯,文翁還講到另一層意思:“美人者,既涵蓋了人間美女,但比美女含意更為廣泛,《詩經》里把‘美人兮‘芳草兮,視為人間美麗的象征,因而你們可以把它看成是美到極致的追求和表達。”這是一個多情多義的文人,有著萬般的柔情,萬般的智慧。
借周明先生之光,我寫了上面這段文字,至此本應結束這篇文章,不意,我讀到了叢維熙先生寫的《文懷沙剪影》,其中有一段文字能見出文翁的另一面。大概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文懷沙被下放勞動期間,陪文懷沙老母前去看望的友人,勸他給江青寫封信,一表示悔改,二表示知恩圖報。文懷沙斷然拒之,并寫成了一首詩表明心跡。其言曰:“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若將每句的第六個字連接起來,就是“龜主江青”。在那個烏云蔽日的年代,有如此的膽識,能見出一個錚錚鐵骨、陽剛之氣甚盛的文懷沙。
因了周明先生,我既得到了文翁的墨寶,還成了這篇文章。依文翁解釋“性命”的方式,“緣分”就是“無緣無分,有緣有分”。周明先生、文翁與我,也算是“有緣”“有分”的。
白燁與郁達夫
郁達夫是寫小說的;白燁是讀小說的。寫小說的郁達夫用自己風格和思想留下了傳世之作,不說別的,一部《沉淪》小說集,就能使我們永遠記住郁達夫。在談論時人很挑剔的知堂老人有一篇專說《沉淪》的短文,我以為入情入理。談到文壇上有人說《沉淪》是不道德的小說時,他列舉美國莫臺耳(Morddell)在《文學上的色情》里論不道德的文學的觀點,認為“《沉淪》是顯然屬于第二種的非意識的不端方的文學,雖然有猥褻的分子而并無不道德的性質。”“他的價值在于非意識的展示自己,藝術的寫出升華的色情,這也就是真摯與普遍的所在。”“而《沉淪》卻是一件藝術的作品。”我推崇知堂老人的這篇文章,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其中的一些說法還能讓讀者對以往的關于郁達夫創作之外的某些放浪形骸行為以及被冠上“浪漫派”“頹廢派”的稱號,會有重新的認識。他說:“生的意志與現實之沖突,是這一切苦悶的基本;人不滿足于現實,而復不肯遁于空虛,仍舊在這堅冷的現實之中,尋求其不可得的快樂與幸福。現代人的悲哀與傳奇時代的不同者即在于此。”今時不同于往時,人們的思想也在發生著變化,也許,在今天的讀者,還會將羨慕的目光投向郁達夫時代的生活方式。我想,這不是他所希望的。
寫郁達夫,我拉出了白燁,是因為“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這兩句詩,十多年前,我曾請著名書法家邱星先生書寫過,也曾讓平凹君寫過。邱星老的書法作品被我轉贈友人;平凹君是寫在冊頁上,不宜示人。2004年的初夏,我與白燁先生有過幾次同案書法表演的機會。期間,我請他書寫了這兩句詩。而這兩句詩,是摘自郁達夫《釣臺題壁》,現錄于此:“不是尊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欣賞這首詩,非本文所能,只說“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其一是講詩人縱酒狂放,生恨生怨遷怒于馬;其二是說有情者自是多情,愛美人卻還要怕累美人。郁達夫的熱愛美人,從他的作品包括日記里我們都能有深刻的體會,無須贅言。白燁才識、膽識具備,與酒有緣;也是多情而愛美之人。寫小說的郁達夫給我們留下動人的詩句;讀小說的白燁饋贈我書寫郁達夫詩句的墨寶。
我一再說白燁先生是讀小說的,讀者萬不可認為他是如同你我般地讀。你我讀小說,可以根據自己的好惡選擇作品,而白燁的自由不多,他是職業讀小說的,絕對不能有好惡之念,他必須將市場上流行的長篇小說整體閱讀。如不這樣,我想每年關于長篇小說的綜述文章他是完不成的。即使能完成,也不能服眾。這些年來,寫小說的人是風起云涌,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老的少的、美的丑的都可大把大把地抓起來,數量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新興的八十年代派,我真不知道白燁怎么會有如此的勇氣,敢攬這檔子事———這可是出力不討好的事啊!文章中提到的,必須說好,稍有不妥,會招白眼的;未提到的,當然是要罵上幾句方能解恨,于白燁只能是忍受了。
白燁先生讀小說,讀出了自己的感受和理性的升華,也讀出了風情萬種。愛美是人之常情,如同讀小說一般,白燁的愛美和為美付出的表現也是很獨特的。既不同于郁達夫,也與我等平常人有異。這些年街上流行的美女作家,十有八九都于白燁有關系,當然不是曖昧關系,讀者千萬不敢理解錯了,我說的關系,是指這些美女們出的書大都是經過白燁的策劃而出籠的。衛慧啊、棉棉啊、等等、等等,她們的成功與白燁身心的付出是分不開的。現在,白燁先生除了諸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等職務外,還被同行譽為文壇上女性作家的“黨代表”。聽說在2002年5月20日由北京文學和北京日報聯合舉辦的“她世紀與當代女性寫作研討會”上,白燁成了萬紅叢中一點綠。
“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這是男人寫的詩句,為男人而寫。我收藏了白燁先生的墨寶,經常拿出來欣賞———為這兩句詩的深刻含義,也為如白燁先生形象一般清爽、俊朗的書寫風格。
艾涓原名劉輝,男,1967年生。1991年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先后出版了詩集《這邊風景》,隨筆集《移動的城市》、《藝文空間》等,系省作協會員。現就職于省政府某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