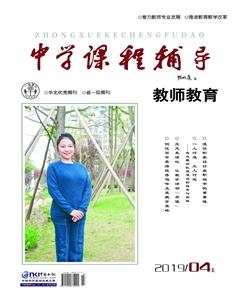讓學(xué)生在生態(tài)德育體系建設(shè)中自信地成長
陳月忠
摘 要::盛澤中學(xué)在生態(tài)德育體系建設(shè)中利用生態(tài)德育的綠色性(主色調(diào):寓意著生命與希望)、人文性(精神支柱:以校園特色文化為內(nèi)涵)、和諧性(具體要求:是穩(wěn)步推進的基本保證)和長遠性(追求目標(biāo):促進每位學(xué)生的全面發(fā)展)去幫助學(xué)生樹立生態(tài)德育的觀念、熏陶學(xué)生的生態(tài)道德情素、提升學(xué)生的生態(tài)道德能力、形成和諧的生態(tài)德育氣氛、給學(xué)生提供展示的生態(tài)德育平臺等方面開展生態(tài)德育活動,進而在這個過程中把學(xué)生自信的學(xué)習(xí)能力培養(yǎng)起來,讓他們自信地規(guī)劃未來、明確自主發(fā)展的目標(biāo)并為之而努力奮斗,提升學(xué)生的核心素養(yǎng),促進學(xué)生的全面發(fā)展。
關(guān)鍵詞:生態(tài)德育體系;活動;自信
中圖分類號:G631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992-7711(2019)07-007-2
自信可以讓學(xué)生進行積極的自我暗示,進而調(diào)動他們的自強之心,最終取得成功。居里夫人曾經(jīng)有過這樣評價:“自信心是人們成長與成才的一種重要的心理品質(zhì)。”如果一個學(xué)生失去了自信,并且沒有堅定的信念,將無法成為棟梁之才。因此,我們的老師應(yīng)該在我們平時的德育工作中注重幫助學(xué)生樹立他們的自信心。自信作為學(xué)生的一種內(nèi)在的基本需要,如果能充分滿足學(xué)生的這種需要,他們就會得到更好發(fā)展。最新的科學(xué)研究成果表明:每個人的自信心受遺傳方面因素的影響比較小,最大的因素則來自于我們所受到的教育和所處的環(huán)境,它們對人的自信心的樹立與提升發(fā)揮著無可替代的功能。盛澤中學(xué)在生態(tài)德育體系的建設(shè)過程中做到從培養(yǎng)學(xué)生自信心入手,充分激發(fā)學(xué)生成功的潛能,發(fā)展學(xué)生核心素養(yǎng)。
盛澤中學(xué)在生態(tài)德育體系建設(shè)過程中以促進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發(fā)展為目標(biāo),以促進學(xué)生的長遠、全面的發(fā)展為原則,盡力體現(xiàn)出生本化、生活化和內(nèi)省化相結(jié)合,最終實現(xiàn)以體驗性為特征的德育形式。它強調(diào)主題活動要呈現(xiàn)出生動活潑的特征,在道德體驗過程中讓學(xué)生形成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優(yōu)秀的道德品質(zhì)。盛澤中學(xué)在生態(tài)德育體系建設(shè)中利用生態(tài)德育的綠色性(主色調(diào):寓意著生命與希望)、人文性(精神支柱:以校園特色文化為內(nèi)涵)、和諧性(具體要求:是穩(wěn)步推進的基本保證)和長遠性(追求目標(biāo):促進每位學(xué)生的全面發(fā)展)去幫助學(xué)生樹立生態(tài)德育的觀念、熏陶學(xué)生的生態(tài)道德情素、提升學(xué)生的生態(tài)道德能力、形成和諧的生態(tài)德育氣氛、給學(xué)生提供展示的生態(tài)德育平臺等方面開展生態(tài)德育活動,進而在這個過程中把學(xué)生自信的學(xué)習(xí)能力培養(yǎng)起來,讓他們自信地規(guī)劃未來、明確自主發(fā)展的目標(biāo)并為之而努力奮斗,提升學(xué)生的核心素養(yǎng),促進學(xué)生的全面發(fā)展。
盛澤中學(xué)的德育生態(tài)德育體系的建設(shè),落實在學(xué)生自主能力的開發(fā)、生態(tài)班級的創(chuàng)建、生態(tài)社團的建設(shè)、主題活動開展等方面,以各種專題案例的形式,積極引導(dǎo)學(xué)生參與各種德育活動的體驗,促進學(xué)生生態(tài)式發(fā)展,增強學(xué)生的感恩之心、進取之心、責(zé)任之心;增進學(xué)生的文明程度、禮貌習(xí)慣和道德水平,以促進學(xué)生的終身發(fā)展為終極目標(biāo)。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健全自主管理體系,培育學(xué)生的自信心
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自信心應(yīng)把培育學(xué)生的責(zé)任能力作為切入口,學(xué)生自主能力的發(fā)展是我們教育的最終要實現(xiàn)的目標(biāo)。盛澤中學(xué)學(xué)生的自主發(fā)展、自主管理的理念主要通過建立和健全學(xué)生自管會的形式來體現(xiàn)。學(xué)生自管會由學(xué)代會選舉產(chǎn)生,是學(xué)生自主管理的重要力量,也作為師生之間的聯(lián)系的重要紐帶。學(xué)生自管會下設(shè)校園環(huán)境衛(wèi)生督查委員會、學(xué)生宿舍衛(wèi)生紀律自管會、學(xué)生紀律仲裁委員會等七個工作部,涵蓋了學(xué)生在校期間的各項活動。學(xué)生自我管理方面表現(xiàn)在學(xué)生日常學(xué)習(xí)生活中的“五讓”:要求讓學(xué)生“明”;制度讓學(xué)生“訂”;干部讓學(xué)生“選”;問題讓學(xué)生“析”;效果讓學(xué)生“查”。把學(xué)生的主體性充分發(fā)揮了出來,自理體現(xiàn)在生活上、自主體現(xiàn)在學(xué)習(xí)上、自律體現(xiàn)行為上,自信體現(xiàn)在思想上,讓學(xué)生真正成為德育的主體,把目標(biāo)定在促進學(xué)生的全面發(fā)展上,把實現(xiàn)過程體現(xiàn)在學(xué)生的自我教育上,發(fā)展學(xué)生的核心素養(yǎng),推動學(xué)生的全面發(fā)展,呈現(xiàn)了盛澤中學(xué)學(xué)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主發(fā)展的良好德育風(fēng)貌。一大批的學(xué)生,通過參與學(xué)生自管會的工作,自信心和責(zé)任能力得到明顯的提升。
二、推進生態(tài)班級創(chuàng)建,養(yǎng)成自覺道德要求
學(xué)生在學(xué)校學(xué)習(xí)的主要場所是班級,班集體建設(shè)也是我們班主任開展德育工作的主陣地。班級的生態(tài)化是生態(tài)德育的前提與保證,盛澤中學(xué)重視生態(tài)班級的建設(shè),每班均有自己的生態(tài)班級建設(shè)方案。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1.遠大的志向:利用班訓(xùn)營造積極向上的班級文化氛圍并確立切實可行的班級奮斗目標(biāo);2.優(yōu)美的環(huán)境:打造生態(tài)、綠色、和諧的能體現(xiàn)班級特色的班容班貌;3.嚴明的紀律:制定班級的各項制度,如班級公約、獎懲制度、值日生制度等,讓班級呈現(xiàn)出活而不亂的良好狀況;4.和諧的關(guān)系:形成良好的師生關(guān)系、生生關(guān)系,成立生活和學(xué)習(xí)的互助小組;5.豐富的活動:定期開展體現(xiàn)班級特色且具有教育意義的主題活動;6.端正的學(xué)風(fēng):班級成員具有良好的學(xué)習(xí)態(tài)度,并重視自身興趣的發(fā)展;7.長足的發(fā)展;注重班干部隊伍的培養(yǎng),加強對學(xué)生進行自主管理、自主學(xué)習(xí)能力養(yǎng)成,實現(xiàn)能力與成績?nèi)姘l(fā)展。
優(yōu)良的班風(fēng)在在班級生態(tài)德育建設(shè)中處于核心地位,它是在全體同學(xué)共同努力下(滿滿的自信心、強烈的進取意識、強大的凝聚力、正確的輿論導(dǎo)向)。一個好的班集體營造出積極向上的文化氛圍,對學(xué)生會產(chǎn)生潛移默化、深遠持久的的影響,陶冶著每個學(xué)生的情操,促進學(xué)生的全面發(fā)展。盛澤中學(xué)從美化班級環(huán)境(包括物質(zhì)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選拔優(yōu)秀班干部(班級生態(tài)德育體系的骨干力量)、正確的輿論氛圍(班級生態(tài)德育體系的精神之根)、濃厚的學(xué)風(fēng)建設(shè)(班級生態(tài)德育體系的關(guān)鍵)、完善的激勵措施(班級生態(tài)德育體系的強大動力)、豐富的課外活動(班級生態(tài)德育體系的有效途徑)、和諧的家校關(guān)系(班級生態(tài)德育體系的溝通橋梁)等方面構(gòu)建生態(tài)班集體,促進和諧友好、奮進爭先的良好班風(fēng)的形成,展示生態(tài)教育的精神風(fēng)貌與獨特優(yōu)勢,讓學(xué)生在這樣的班集體快樂自信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