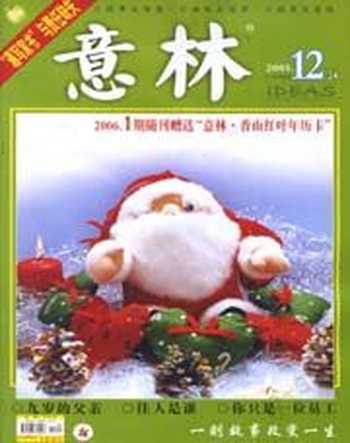身上沒有盔甲的人
張東吾
他孩童般地度過大學生活,他過著簡單自足的生活,他給人以最自由的空間,他以淡泊的心態接近成功。微軟的人都說:“亞勤感性、率真。身上沒有盔甲,不需要戒備。”2005年7月,科大78屆學生聚會,張亞勤博士成為他們的驕傲。張亞勤的人生軌跡,體現了他作為一個成功學者獨特的精彩的養生之道。
張亞勤博士1966年出生于山西太原,12歲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23歲獲得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電氣工程博士學位,后又就讀哈佛大學高級主管商業專業。張亞勤博士于1999年回到中國,加盟當時的微軟中國研究院,致力于數據壓縮、視頻、多媒體及Internet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微軟亞洲研究院經過近五年的發展,目前已經擁有160多位研究人員,另外有250多位訪問學者、博士后以及學生,成為微軟發展的智囊團,而張亞勤也被提升為微軟全球副總裁,負責微軟全球的移動業務。張亞勤6歲就開始自己坐火車。
1978年他告別母親坐了20多個小時的火車來到科大少年班的時候才12歲,是當時年齡最小的大學生。在去學校的路上,別人分辨不出他是小學生,還是大學生。他和其他少年班學生一樣,有最好的老師,吃最好的食堂,還有人幫著洗衣服。思想、工作、生活、起居,都被關照得細微周全。而心靈的豐富與滋養更值得懷念:“眼界完全開闊了,在自由的校風中感覺很舒展。著名的科學家都去演講,美學音樂什么都聽,對交響樂都入迷了。”
小學的年齡上著大學的課程,成天跟比他大十幾歲的同學在一起,張亞勤并沒有像想象中那樣變得少年老成。他活得很性情,完全是孩子心態。“我早晨睡懶覺,中午起來就吃飯,回來睡個午覺。下午又去踢球了。晚飯后七八點鐘才開始學習。玩得太多,挺長時間都沒有上過課,以至于老師找我談話。”
他用孩子的眼睛,孩子的思維想事情:反正考進來了,動力有點消失了,也沒有家里人管,愛干啥干啥唄。也沒有覺得辛苦,也不知道為什么學習,張亞勤就這樣高興地、朦朧地度過了美妙的大學時光。他進入美國讀書,張亞勤與異國文化、同學老師、科研環境都和諧共處。張亞勤把這歸結為“喜歡學習”、“糊里糊涂地什么都不在乎”。
但亞勤真的從來沒有遇到過挫折嗎?5歲的時候,張亞勤的父親就去世了。博士論文都做到了一半,才發現同一個題目別人已經做過了,只好改題目重來。“但我不覺得懊喪,總比全做完了到答辯時才發現好吧?再說,做同一個題目的還是位很有名氣的人。”這種思維方式,成就了張亞勤平和簡約的心態,這種心態像保存在特富龍涂層中一樣,從未被破壞過。
因此,張亞勤活得一直比較簡單而自足。在美國讀書時,“我和女朋友(現在的愛人)兩個人整天出去玩,開個破車到處跑,從華盛頓開到佛羅里達,中間也舍不得住酒店,老吃快餐,挺快樂的。”現在他的辦公室里擺著太太和兒子、女兒的照片,溫暖洋溢。
張亞勤在美國當學生會主席時,天天搞活動,跑前跑后,成天幫別人幫得高高興興。國內企業代表團到華盛頓訪問時,他去接機,是當時著名的“免費司機”。“當時大家關系都很近,一到周末都在一起,特別有大家庭、團隊的感覺。很值得懷念。”與很多中國留學生在國外活得很封閉不同,張亞勤的朋友遍天下。張亞勤平靜清淡的思維,足以提醒我們,他作為一個學者的真實。事實上,他是活得很主動,很盡致的人。
他的性格是多元的,有著龐雜的愛好:交響樂、美學、跑步、游泳、跳舞、去酒吧和朋友神聊。像很多高智商的人一樣,他很重視感覺,也相信感覺。“我是個很情緒化的人,情緒好的時候,有很多靈感。不好的時候,做的事情比誰都差。”要是去旅游,張亞勤基本不會想好去什么地方再出發,而是“把車子到處亂開,邊走邊想。有好玩的地方就停下來。”天賦與炫目的成功經歷,注定了張亞勤心靈的明澈與舒展。張亞勤說話的聲音和外表都給人很溫厚的感覺。
他有著溫和聲音和文雅的外表,有著不同于一般人的細心和平和。一起外出的時候,他會很細心地讓別人先選擇座位;交談的時候,他也總能看似不經意地“檢查”你杯子里的水,然后請助理甚至自己站起身來幫你添。在他的言談中,你感覺不到任何與坎坷、消極相關的字眼。
張亞勤喜歡直白與不回避的方式,但卻幾乎從未在他交往的人中得到過微詞。他非常在意別人的感受,也是愿意與世界和諧相處的人。他的世界里似乎永遠陽光、和諧。他直視著對方的眼睛說話,說到高興處笑得很盡興。遇到談得來的人,就是再忙,也總是任時光在不知不覺間流淌。“我跟這個世界很少沖突,一般都比較和諧。”他語調平靜,沒有疲倦感、隔膜感。在微軟亞洲研究院,張亞勤營造了講究團隊精神、和睦相處的氛圍。
員工說,在這里每個人都很透明,管理和運作的方式也很透明。每個人都是他本來的面目,不是因制度而改變過來的人。張亞勤“管理”研究院這么多“聰明人”的方式是:給人自由的空間,因為每一個人定位是不一樣的,要給他更多的責任。
管理者要有胸懷,包容不同的工作方式,往往一些很聰明的人性格會比較特別一點,管理者必須有一種包容的心態去幫助他們。學者們的個性不同,要賦予他們不同的環境,創造不同的思維空間。在數次員工大會,張亞勤說:“如果5年之后我仍然是這里最資深的人,最有名的人,那就證明研究院的失敗。”
現在,3年前進來的學生們都已能獨當一面了。在張亞勤的記憶內存中,更多的是感性的、“難以忘懷”的鏡頭。“我離開GTE公司到微軟中國研究院時,走的時候公司專門開了個Party,回到自己工作過4年的辦公室,幾十人一個一個地走進來,他們都是我招進來的,我們擁抱告別……情景真的很感動。”工作上的同事,很多人成了他終生的朋友。
每天清晨,充滿朝氣的張亞勤都會很準時地出現在“星巴克”門口。店員們早已習慣了他的作息時間,每天一大杯的“奶特咖啡”在他走進店門的前幾分鐘已經開始制作了。從星巴克出來,打開車門,坐在后排的座位上,翻看剛郵寄過來的《華爾街日報》。到辦公室的時候,恰好是早上九點。帶拐角的長形辦公桌旁放著一個竹籃,里面裝著餅干、薯片之類的零食。墻邊書柜的空格里擺著太太、兒女的照片,溫暖洋溢。了解張亞勤的人都知道,他雖然總處于“最好”的位置上,卻不是執著于第一的人,反而是怎么樣都挺高興。
他自己也承認:“我從來沒有想過做第一。我覺得盡自己的努力,和最好的人為伍最好,做第二,第三也挺好。人應該在內部外部找平衡。”張亞勤總有多維的目標,如果沒有達到這個目標,沒有關系,還有別的。就是現在問他不做院長行不行,他也會說“當然行,哪天我做院長不高興了,可以做大學教授。”回到中國之后,對于張亞勤來說,做技術權威的愿望就像大海中小小的浮標,雖然還在那里,卻已不是絕對焦點。“回國后我最大的感覺是使命感,我能影響的是更多的人。”張亞勤受邀定期到全國各大學演講。
每一次演講他都會想起自己做學生的時候,對講演者虔誠的吸收心態。不過,一旦張亞勤決定在一個新領域超越,那就離實現目標不遠了。張亞勤是一個熱衷于工作但又絕對懂得如何“享受工作”的人。
他說:“我從不會要求自己今天一定要做什么,明天一定要怎么樣。Lifes short(人生短暫),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足夠的Fun(樂趣)。一個成功的人并不僅僅是指事業上有所成就的人,而應當是真正懂得Enjoy(享受)的人。”
我經常聽人說,今天是星期五了,馬上就可以回家,真是太開心了。他們每天工作8小時,換回的就是一天幾個小時的Fun,我覺得這個交易太不合算了。最理想的狀態是24小時都有Fun。”
“我每天盡量爭取兩小時一個人自由思考的時間。這種時候,不希望別人打擾我。”張亞勤知道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處理管理與研究之間的沖突,沒有人比他做得更好了。
(李久紅摘自《北京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