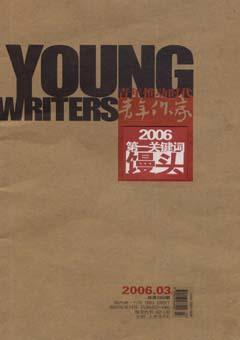“文革”老照片壓抑與狂歡
林和生
兩幀文革老照片的解讀
在我保存的所有照片中,確切屬于“文革”時期的老照片并不多,總計約20幀。最早一幀大約攝于1966年盛夏,哥哥帶著我抱膝坐在草坡上,兩人均身著短袖白襯衣,藍色長褲,我的褲腿挽到膝蓋以上,打著赤腳。遠處圖書館閣樓上隱約可見一幅橫標,由字形猜測,內容大概是“無限忠于毛主席”一類。那一年,我12歲。
仔細觀察這幀影像模糊的照片,并充分調動記憶的存儲,我從中認證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哥哥和我都未佩帶毛澤東像章。這是一個不小的發現,說明1966年的夏天,尚未發明毛澤東像章,或者發明了也未普及。作為對比,我拿起另一幀1968年的老照片(兩兄弟在1968年9月。見小刊14頁),照片主人翁是一對十歲左右的兄弟(我兒子的兩位表舅)。兩人身著拉鏈開領的春秋服,胸前均佩帶了毛澤東像章,哥哥的像章是矩形,弟弟的是五角星形。這個細節說明兩個事實:第一,兩年左右的時間內,毛澤東像章已成所有人崇拜和追逐的紅色時髦;第二,毛澤東像章已發展出多樣化的形式。這個細節讓我回憶起:五角星形的毛澤東像章最初屬于軍隊的特權,后來逐漸解凍進入民間,所以比一般的圓形或矩形像章更珍貴。兩兄弟所佩像章的差別,似乎不經意間反映出他們在家庭中地位的差別。后來證實,當年弟弟的確更為父母所愛。弟弟胸前那枚五角星像章正是這一事實的明證。照片上,兩人的意念似乎都聚焦于胸前的像章。不同之處在于:哥哥神色略顯不快,不知出于性格、還是出于像章的差別。
“圖騰”及狂歡
借用弗洛伊德的術語,毛澤東像章是當年億萬中國人的“圖騰”,它對于當時心靈的作用,不難從這位孩子幸福滿盈的神色得到證實(身著軍裝胸佩像章手拿紅寶書的幸福孩子。見小刊12頁)。然而,另一幅四人全家福文革老照片卻令人費解:兩姐妹手拿(父母的)“紅寶書”,連同父母,每人佩帶一枚巨大的圓形毛澤東像章,全家似乎都以一種“哲人尼采式”的眼神望著虛空中的某點(“文革”全家福。見小刊47頁)。是攝影師技術上的問題?還是圖騰正在解構、壓抑開始形成?這一推測自有理論支撐,并非玄想。弗洛伊德在其名著《圖騰與禁忌》中表達了這樣的洞見:圖騰是崇拜與壓抑兩者不可調和之沖突的結晶,圖騰=崇拜(狂歡)/壓抑。崇拜有多狂熱,壓抑就有多深刻。往往,狂熱的崇拜退潮之后,便會在社會心理的沙灘上留下空洞形式的壓抑。事實上,就在狂熱崇拜的同時,壓抑即已如影隨形。思嘉的回憶短文《一枚破碎的紀念章》生動地詮釋了這一深刻的精神分析原理。該文憶及文革中某次與姐姐爭搶一枚紀念章,一不小心摔成了兩瓣。于是圖騰變幻為壓抑,狂熱演生為夢魘:
當時我們姐倆頓時傻了眼。開始我們互相埋怨對方,但吵過之后,我們都同時感覺到這件事情的處理才是最重要的。首先是要瞞過母親,其次是要把摔碎的紀念章放到一個不為別人看到的地方去。那個年代,摔碎一個紀念章可不是小事,如果隨便亂扔,被人看見了,搞不好會被別人上綱上線,視為反對偉大領袖,嚴重了還可能說你是反革命,那可要吃不了兜著走。為了這個破碎的紀念章,我覺得自己犯下了滔天大錯,我整夜嚇得提心吊膽,在幼小的心靈里充滿了沉重的負罪感。
由這兩姐妹聯想到上面那幀文革老照片中的兩姐妹,我們似乎多少明白了她們(及其父母)令人費解的眼神。
第二天早晨起來,窗外飄著飛飛揚揚的鵝毛大雪,我和姐姐在上學的途中悶悶無語,心里都在想著那枚摔碎的紀念章。我們腳踩著咯吱作響的白雪,我突然想起一個辦法,不如把那枚摔碎的紀念章埋在皚皚的白雪之下,這樣不會被別人看到。我跟姐姐商量之后,姐姐因為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辦法,只好同意了我的辦法。我從作業本上撕下一張紙,精心地把摔碎的紀念章包在里面,然后蹲在地上佯裝系鞋帶,隨即悄悄地把這個紙包塞進了已經沒過腳脖子的白雪里。說真的,當時我這樣做的時候,緊張得心臟幾乎跳出胸口,我左張右望,就像一個作賊的人,那種折磨人的感覺,后來多少年都難以忘記。直到我站起身來,確定了并未有人注意到我時,才如釋重負般地舒了一口氣,仿佛終于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被記錄的主體
今天的人的確難以想象。就連作者本人想起當年,也有不可思議之感:多少年過去了,這件事情一直壓在心里,感到沉甸甸的,現在想起來覺得那時幼稚得可笑。但是,在那樣特定的年代,這的確是一個懵懵懂懂的孩子真實的經歷和感受。現在的孩子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更不會相信,為了不小心摔碎的一枚紀念章,會給人的心里帶來如此沉重的壓力。
這枚摔成兩瓣的紀念章是一個絕妙的隱喻,提供了大多數文革老照片的最佳解讀:大字報,傳單,大批判,“忠字舞”,樣板戲,革命“調演”,最高領袖的接見,盛大集會或游行的“紅海洋”……大量文革老照片見證著原始巫術般的群體崇拜和群眾狂歡,也見證著其后深不可測的壓抑。
壓抑首先體現于群眾狂歡的宣泄對象:被以“鴨兒鳧水式”掛牌斗爭的國防部長彭德懷、身陷囹圄病死獄中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惶惶不可終日的各地各級“走資派”等等。壓抑也體現于群眾性狂歡的“軸心人格”主體,如毛澤東本人在檢閱紅衛兵時臉上偶現的隱憂。壓抑也體現于周恩來那幾幀“面色凝重”的照片,尤其是那幀著名的《沉思中的周恩來》(見小刊34頁),它由意大利攝影師焦爾喬·洛迪攝于1973年,周恩來已在上一年確診為膀胱癌。在這幀歷史性的照片中,周恩來胸前也佩帶著一枚風格簡潔的毛澤東像章。
壓抑還體現于那場全國性群眾狂歡中身份更復雜、心理也更復雜的人物:林彪作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卻表現出對風和陽光的焦慮,今天用心理學的眼光來看,這是典型的神經癥。壓抑也深藏于狂歡者自己的內心,他們在“文攻武斗”中歇斯底里,甚至精神崩潰,在夜間做噩夢。誰都害怕從狂歡者淪為狂歡宣泄的對象。從技術上說,誰都有被告密、被指認為“反革命”的可能。就此而言,正如剛才所說,狂歡有多烈,壓抑(焦慮、恐懼)就有多深,這是解讀大多數文革老照片的“圖像學”,它最終是一種反面的見證。
人性永遠充滿希望
最后,壓抑以一種令人心碎的眼神,從筆者父親的目光中流露無遺。我手頭拿著一幀20世紀80年代初的彩色照片,它在技術上不屬于“文革”時期,然而忠實地記載和傳遞著“文革”時期痛楚的記憶。當然,如果對比“文革”中另一幀類似的老照片,不難發現父親人心碎的眼神中滲出了某種柔和,雖然不易捕捉,但也足以印證人性的堅韌。沒過幾年,父親即辭別人世,然而,僅僅依據這幀照片,我已可以代父親自豪地宣告:他曾經苦熬,而且,熬過來了!
人性永遠充滿希望。“文革”老照片雖然彰顯著狂歡壓抑的二律背反,但也偶爾生機微漾。例如那幀寫“決心書”的“文革”老照片(見小刊16頁),書寫者臉上的笑容已頗有些春意,四位少女的神情亦然,尤其左邊兩位少女,她們的衣著即便在今天看來亦不為過時。右邊兩位少女衣著樸素,而且各佩帶了一枚毛澤東像章,其余三人均未佩帶,這一細節的差異透露出這幀照片的時間信息,那顯然已是“文革”的晚期。據此,對于一些具體日期不詳的“文革”老照片,我們找到一種行之有效的時間判別法,即觀察照片主人翁佩帶毛澤東像章的情況。“文革”后期(大體以林彪事件為分野),佩帶毛澤東像章不再是壓倒一切的狂熱,而蛻變為隨意的個性之舉。壓抑在不知不覺間悄悄解除,人們的面容開始流露日常性質的愉悅神情,與群體崇拜和群眾狂歡時代的歇斯底里形成對比。
圖像見證時代
在今天的圖像時代,相對傳統的文字媒介,人們更傾向于由圖像獲取直接信息。老照片,由于忠實記載著過去時代人們的眼神、表情、衣著、飾物、裝點、建筑、環境等相關信息,因而具有重大文獻價值。
有關“文革”的老照片更是如此。這是因為,“文革”是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罕見的非常時期。“文革”標示政治文化地脈,閃現集體無意識,見證民族生命史。僅就純粹學術領域而言,“文革”研究早已是國內外學界一大熱點。尤其在西方,“文革”研究倍受關注。用今天的眼光看,“文革”創造了諸多吉尼斯世界紀錄:“20世紀群眾參與程度最大的運動”(8億人全部參與)、“20世紀最大規模的集會和接見”(如毛澤東第8次接見250萬紅衛兵),“20世紀最流行的書”(幾年之內50多種文字正式出版500多種版本《毛主席語錄》50余億冊),“20世紀創紀錄停課”(2.3億中小學生停課長達18個月)等等。更重要的是,“文革”見證個體生命的載浮載沉,恍如隔世的痛楚,最后定格在那些泛黃或殘損的老照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