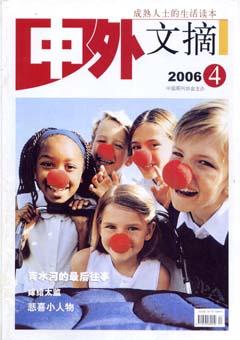故宮博物院搬遷始末
郭瑞璜
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成果之一是中共中央臺辦宣布:開放大陸居民到臺灣旅游。兩岸隔絕半個多世紀,大陸居民赴臺觀光,看什么?有關方面分析,臺北故宮博物院將是首選的旅游景點之一。日本放送協會(NHK)制片人后藤多聞1996年發表的《故宮采訪筆記》,對臺北1故宮博物院的歷史淵源敘述甚詳。現將該文有關部分編譯如下,供參閱。
1985年10月,北京和臺北都舉行了紀念故宮博物院成立60周年大會。日本放送協會由此萌發了一個念頭:攝制一部大型系列片,用完整的故宮博物院璀璨藏品,介紹中華文明史。幾經周折,此項計劃1994年秋才付諸實施。歷時兩年,《故宮——用瑰寶講述中華五千年》拍竣。在采訪、拍攝過程中,后藤多聞探尋了故宮博物院的淵源及其藏品在中華民族、中華五千年歷史上的意義。
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這兩個收藏著世界頂級文物的著名博物院,原來是一個整體,一分為二的背景,是上世紀上半葉這個國家的戰爭悲劇。
1911年10月10日,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末代皇帝溥儀退位,根據清室優待條件,仍暫居紫禁城內。13年后的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廢除大清皇帝稱號,溥儀被逐出皇宮,供歷代皇帝等少數人賞玩的大量珍寶,統歸民國政府所有。總理黃郛主持的內閣會議,決定成立“辦理清室善后委員會”,聘請一批專家學者,清理宮內財產。
91歲的北京故宮博物院顧問畢士元說:“當時我還在大學讀書,去幫助教授們清理故宮財物。那時宮內荒涼不堪,雜草叢生,撥開雜草才能露出路徑。過去平民不能進入紫禁城,只能在戲劇和小說里了解皇帝和后妃們的生活,現在能親眼目睹這里的情景,內心是十分高興的。”
因為社會上流傳著種種盜竊寶物的流言,善后委員會制訂了:“點查清宮物件規則”18條,內容非常縝密,以昭信于社會,并使清點工作有所依據。臺北故宮博物院顧問、90歲的那志良,那時也是大學生。他中學時期的校長、考據家陳垣,是善后委員會成員,便把他找去,和其他學生一起,幫助清點故宮文物。
那志良回憶說,一個人清點,一個人登記,一個人掛號碼牌。上有組長,都是政府各機關派來的,他們未必懂行,但可以當見證人。另外還有專門監視的人,以及一個兵,一個警察。清點時不能吸煙,不能單獨行動,要同進同出,連撒尿都不成,怕有人偷東西。那時正是冬天,北京天氣很冷,毛筆都被凍住了,要不時用嘴呵氣才能化開再寫。
皇宮里到底有多少珍寶,恐怕連皇帝本人也說不清楚。溥儀16歲時,內廷建福宮一帶倉庫頂棚內,發現了大量文物,都是乾隆的收藏品,乾隆去世后封存于此,再未面世。溥儀看到這些寶物后驚嘆:“我到底有多少寶物呢!”
經學者、專家、幫忙的學生們艱苦細致工作,花費了一年多時間,完成了清宮內物品的整理、清查、登記、編號、造冊工作,并選出一批物品公開展覽。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辟為故宮博物院,專事收藏、展覽歷代皇帝收藏的文物,正式對平民開放。從此,清宮內的所有物品,哪怕是家具擺設,都具有了新的歷史意義。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基本上是宋、元、明、清四朝代的皇帝們收集到宮中的珍寶,但它的精神卻是從夏、商、周朝以來一以貫之的。故宮博物院的藏品,應該說是延續幾千年、世代傳承的中華瑰寶,是一個完整的體系。
從古以來,每個王朝的皇帝,都要收藏一些稀世珍寶,以證明其正統性,如周秦時期的九鼎。到了漢代,皇帝已經有專門收藏珍寶的設施,如西漢時期的石渠閣、麒麟閣等。起初皇宮的藏品,大多是玉器、青銅器,魏晉以后,書畫陶瓷精品亦進入皇帝收藏的視野。
隨著王朝交替,戰亂頻仍,宮廷文物有些被破壞了,有些丟失了;有些散落民間又輾轉回歸皇宮的;有些被帝國主義掠奪至今存放在外國博物館的,如大英博物館的《女史箴圖》等。故宮文物流傳的故事,有代表性的可以舉《江行初雪圖》(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運行軌跡為例。《江行初雪圖》是南唐宮廷畫家趙斡的作品,先是歸“風流天子”宋徽宗收藏,后落入金章宗之手,元滅金時流落民間,明初進入皇宮,清初再次傳到民間,清乾隆時期重歸皇宮,遂成為現在故宮博物院的藏品。
在所有皇帝收藏家中,宋徽宗和清乾隆這兩位有鑒賞力的皇帝,對收藏故宮文物功不可沒。宋徽宗是中國古代著名書法家,清乾隆亦擅長書法。他們在位時,廣泛收集古董和書畫,說宋徽宗打下基礎,清乾隆在此基礎上集大成,一點也不為過。
在北京故宮近萬間房屋中,“三希堂”只不過是養心殿一隅的小書齋而已。但因它收藏了三件稀世珍品而名滿天下。清康熙時期,長期流落民間的書圣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被獻給皇帝。乾隆十一年,又有人把王羲之外甥王珣的《伯遠帖》(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獻給乾隆。加上王獻之的《中秋帖》(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本已在宮中,王氏一門三件法帖全部歸于乾隆。這位皇帝喜不自勝,遂在他生活起居的養心殿一隅修建了一個書齋,專門收藏這三件稀世之寶,故名之“三希堂”。
乾隆最中意的書法作品是《快雪時晴帖》,曾在該帖上大寫一個“神”字,還在另外的紙上寫下“神手技點”,表達了喜愛和景仰之情。每到下雪天,乾隆就到三希堂欣賞《快雪時晴帖》,興之所至,畫了一幅山水畫《羲之觀鵝圖》,描繪王羲之觀看鵝在池中游泳,頸部擺動的樣子,從而悟出腕訣竅的故事。
可見,故宮博物院的文物,是在王朝更迭、無數次的戰亂中,以極偶然的機會,被皇帝們和理解中華民族之心的文人們保存下來的瑰寶。
故宮博物院創辦不久,戰爭陰云又籠罩了中國。1931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軍三個月即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1932年,日本又制造了一個以廢帝溥儀為傀儡的“滿洲國”。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公開化,華北、華東將成為繼續侵吞的目標。中國政府決定,將故宮文物裝箱南運,存放在上海租界內,以免毀于戰火。
為了保證易碎品在運輸過程中不致損壞,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請教了北京琉璃廠各大古玩店包裝瓷器的方法。那志良說,裝箱時把十個瓷碗扎在一塊,使它成為一體,然后裝箱,再用軟物塞緊,一箱文物就成了一個整體,即便箱子掉在地上,里邊的文物也不會損壞。
據《故宮七十星霜》一書記載,故宮文物南運計劃傳開后,社會各界是贊成的。因為北京很快就要變成戰場,文物被破壞的危險性是顯而易見的。土地丟失了可以收復,文物一旦遭到破壞就永遠丟失了。也有反對的,理由是擔心故宮
文物一旦失散就很難復合。有些激進人士認為,文物南遷是政府放棄北京的前兆,民心浮動。其中最激烈的是周肇祥。他曾任湖南代省長,當過故宮古物陳列所所長。為了阻止故宮文物南運,他在中南海成立了“北京民眾保護古物協會”,自任會長,發表演說,散發傳單,多次表示要武力阻止故宮文物南運。他還聯絡了一批汽車司機、車夫、搬運工人,拒絕給故宮搬運文物。預定第一批南運的箱子,就是因為等候工人未到而使計劃落空。
當時社會上謠言四起,說只要文物裝車啟運,就要在鐵路中放置炸彈,炸毀列車。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易培基沒法,便拍電報給行政院代院長宋子文,宋給北京市長下令,以“煽動群眾,擾害治安”罪拘捕了周肇祥,并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文物南運才得以進行。
當時20多歲的那志良是故宮博物院最年輕的科長(其他科長都四五十歲了),從頭到尾參與了故宮文物運輸、保管過程。據他介紹,1933年2月6日,天不亮,故宮博物院第一批南運文物箱子,在軍隊嚴密保護下,裝上北京站物別編組的列車,一路向南駛去。到同年5月5日共分5批把13491箱文物,從北京疏散出來。其中,陶瓷、瓷器1058箱,玉器158箱,青銅器55箱,書畫128箱,以及大量文具、印章、漆器、玻璃制品,還有許多圖書、文獻。
這些故宮文物存放在上海租界。1937年元旦,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竣工,才又運到南京,尚未開箱布展,同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開始全面進攻中國,戰火即將蔓延到南京。在這種緊迫形勢下,國民黨政府又決定將故宮文物向國內西南安全地區疏散,即分成二組,運往陜西、湖南、四川等地。那志良是第一組負責人,8月14日動身,把一批文物運到長沙,存放在湖南大學圖書館。11月12日上海淪陷,20日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因為日本飛機飛臨長沙上空,很不安全,12月那志良再次把文物裝船,轉運到四川山中保存。大約一個月后,湖南大學圖書館即遭日本飛機猛烈轟炸,毀壞嚴重。那志良感嘆道:“多虧我們逃得快,否則……”
幾十年后,那志良還記得運輸文物的艱難:“用汽車運,一車裝20箱文物,麻煩極了,有錢也沒有用,找不到車,有了車又沒有汽油,有了汽油路又斷了……”
原定運往寶雞的第三組文物,由于在當地找不到合適的存放地點,卡車繼續南行,翻過秦嶺,經漢中運到成都。最后一批即第三組文物,裝船離開南京,沿長江上行,向重慶進發,是12月8日的事情,五天后日軍即攻入南京。
這些文物分別存放在四川、貴州的深山里,直到二戰結束,才又集中到南京。不久,國共之間爆發內戰,共產黨軍隊勢如破竹,蔣介石政權搖搖欲墜,即挑選出4000多箱約70萬件文物(一說2792箱約65萬件),從1948年12月22日開始,分三次運到臺灣,存放在南投縣霧峰山的北溝倉庫。那志良也隨著文物到了臺灣,再也未能回到北京。
解放軍渡過長江,進入南京,剩下的9000余箱約100萬件文物被運回北京故宮博物院。
1965年11月;位于臺北市郊外陽明山腳下雙溪的臺北故宮博物院落成。這座按照南京中山陵的模式修建的地下一層、地上三層宮殿式建筑,就成為臺灣收藏、展覽故宮博物院文物的處所。
1933年從北京故宮運出的一萬多箱中華瑰寶,歷經艱險跋涉,到達臺灣或又回到北京,行程都在12000公里以上,可謂中國文物的一次25000里長征。在世界大博物館中,像這樣大規模、長距離運輸文物是沒有先例的。它在世界博物館史上應當大書一頁。而且在運輸途中文物卻沒有受損。那志良說,曾發生過幾次翻車事故,但卻沒有死一人,沒有損壞一件文物。
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說:“每想到這個問題,我就感到‘古物有靈。這個‘靈就是民族感情,民族語言和文化,保護著這些文物。這個‘靈一直在我們心中。”
這也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有關人士的共同心聲。
(劉述禮摘自《各界》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