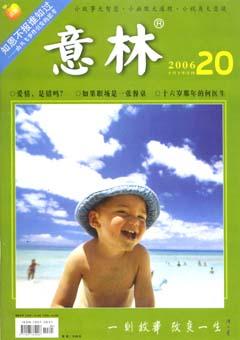個人所承載的含義
劉 昆
一片晨曦,一條小河,一道木橋,一支蘇聯紅軍部隊千里奔襲,追擊德寇來到這里。兩個紅軍指揮員騎著戰馬立在橋頭,共同展開一張巨大的軍事地圖,一寸一寸地用心查看。
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河對岸的森林里,走出來一個扛著長柄斧頭的樵夫,越來越近了,一直走到橋頭的另一端,停下來。
指揮員問他:“你是誰,這里是哪兒?”
樵夫反問:“你們是誰?來這兒做什么?”
“我們是蘇聯紅軍,大校凱蘇里、上校斯捷潘,我們在追擊敵人。”
樵夫答道:“哦,我是波蘭公民涅里克,”他半轉身,手向后一揮,“先生們,請進入波蘭。”
一個情景出現了:漫山遍野的蘇聯紅軍全體立正,向樵夫敬禮。
一個災難深重的國家,不到二百年中三次被列強瓜分,又三次復國;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二戰期間幾乎被法西斯滅絕種族,眼前這個衣衫破舊困苦不堪的人無疑是戰爭鐵蹄下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可是,他心無余悸,鎮定依然。在上萬荷槍實彈的紅軍戰士面前,這個普通的老百姓無疑是微不足道的。微不足道的人張開寬闊的臂膀說:先生們,請進入波蘭!一個砍柴的農民,他竟敢毫不臉紅地把自己作為一個國家的代表嗎?他竟敢毫不臉紅地把自己作為一個民族的象征嗎?你看,你聽,他的手勢多么從容!他的口氣驕傲到何種程度!他揮手說這句話的時候,波蘭已經再次被法西斯德國吞并,版圖意義上的波蘭并不存在。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話聽得有些年頭了,很多時候很多場合聽了就會下意識地鼓掌,而且每每出于某種目的——為了向旁邊的人證明什么吧?拍得生疼,拍得麻木……作為本民族的一分子,我常常心虛地質問,自己除了拍巴掌我還肯做些什么?
為此更加由衷地感激這個小故事,它讓我明白了我心深處還殘留著些許真摯的情感,還沒完全喪失受感動的本能。
更深一層意義的感動,是那些向波蘭敬禮的紅軍官兵,正像一個高尚的人永遠懂得感恩一樣,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們懂得尊重。
(曹西國摘自《合肥晚報》2006年8月29日)